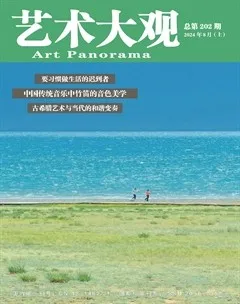诗乐交融的意象表达
摘 要:本文探讨了音乐与其他艺术形式的相互影响及其在现代创作中的具体实践,特别是通过民族室内乐《共坐白云间》来分析跨媒介创作思维的应用。文章详细阐释了作品如何通过塑造文学符号与感官艺术的互动,利用“跨媒介”手法实现感官与音乐形态之间意境的转换。材料延续了诗乐一体的传统,并进一步分析如何运用音乐材料与技法来实现音符与文字之间的跨媒介作用,突出这种创作方法为现代民族音乐的审美观念和创作实践提供的新视角和动力。
关键词:跨媒介;创作思维;诗乐一体;民族室内乐;《共坐白云间》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7357(2024)22-00-03
音乐不仅是艺术家自我表达的重要形式和载体,也是作曲家传达生命体验与感悟的重要手段。2020年,青年作曲家刘鹏创作了民族室内乐作品《共坐白云间》。同年11月,该作品由北京现代乐团与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室内乐团联合在莱比锡当代音乐室内乐团音乐节(Ensemble Festival for Contemporary Music Leipzig)首演。作品的乐谱也被纳入首批“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项目,并将由中国出版集团与德国朔特音乐出版社(SCHOTT MUSIC)联合出版。
该作品通过时间、空间、感官与审美的多维度构图,试图借助寒山的诗意,在全球疫情严峻的背景下,表达对生命万物的敬畏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渴望。以“寒山”为核心象征,作品展现了音响空间的抽象性与丰富的想象力。它不仅融合了东方的写意美学与西方的写实技法,还将音乐的精神内核与人文内涵紧密相连。
一、诗乐传统与“跨媒介”创作特征
(一)“跨媒介”的历史意涵与当代表达
音乐作为一种跨媒介的表达形式,融合了文学、视觉艺术与音响元素,成为表现诗歌意象与文化意境的独特平台。在此背景下,“艺格符换”这一概念在跨媒介创作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源自三世纪阿弗索尼斯的西方修辞学,“艺格符换”最初指用语言精确描绘可视事物,与中国古代诗学中的“赋”相似,后发展为跨艺术领域的关键术语。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者如克里格(Murray Krieger)重新审视这一术语,将其置于诗画关系和更广泛的诗学语境中,强调“艺格符换”是“文学对造型艺术的模仿”,“艺格符换原则”体现了诗歌语言的特殊空间性。
在当代创作实践中,跨媒介手法通过借鉴“艺格符换”原理,有效地结合了诗歌的文学性与音乐的形式表达。此方法不仅是对视觉与情感深度的音乐场景的再现和塑造,也是作曲家将乐外媒介(如诗歌、书法、绘画等)的灵感进行有机转化的一种创新思维。这种跨越艺术界限的创作思维,不仅拓展了其他艺术媒介的表现力,而且极大地丰富了音乐创意的表达可能性,这种“出位之思”在很大程度上也塑造了创作者的艺术走向与风格[1]。
此外,跨媒介的创作逻辑与中国古代的“诗乐一体”传统有着密切的承继关系。中国的“诗乐一体”文化传统始于《诗经》,并贯穿汉乐府诗歌、唐代曲子、宋词、元曲,直至明清的说唱与戏曲艺术。这一传统不仅促进了诗歌与音乐的交融与共同发展,而且在三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促使某些文学体裁与音乐形式分离并各自独立发展,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作品《共坐白云间》选择“诗乐融合”作为艺术及审美的基点,不仅探索了音乐作品中诗意与音乐结构的新互动方式,而且凸显了音乐作为一种声音艺术之外,作为一种表达和转化诗歌深层文化意境的有效媒介的能力。
(二)“意象化”的文辞转换与形象刻画
《共坐白云间》作为一次具体的创作实践,展示了诗歌文字与音乐艺术之间的跨媒介互动,实现了音乐的隐喻、诗词的隐意与聆听时的情感共鸣,将这些元素与听众的主体意识相呼应。作品分为七个部分:Ⅰ.寒山杳杳、Ⅱ.白云自闲、Ⅲ.联谷曲曲、Ⅳ.叠嶂重重、Ⅴ.千草泣露、Ⅵ.孤风吟松、Ⅶ.共坐白云间。这七个部分的创作不仅启发了观者的文学联想,还通过音乐文本深入探讨了音乐的“能指”与“所指”——即音乐形式及其背后的文化和情感意义。每个部分通过独特的音乐结构和词汇,向听众展示了丰富的文化意境和音乐画面,展现了音乐形式的多样性和音响形象的丰富性。作品的每个乐章都体现了丰富的音乐色彩,并通过和声与音响的同构关系,如彩绘玻璃般呈现多样的变化和层次,将音乐形象从诗意延伸至视觉层面。
全曲共145小节,由八种器乐声部组成:竹笛、笙、琵琶、中阮、古筝、扬琴、二胡、中胡。每个声部都占据重要地位,展现各自的音色特点。例如,第1—24小节的“寒山杳杳”部分,通过明确的音色层次和强弱对比,创造出一种远处观山的感受。从第25小节至第37小节的“白云自闲”中,突出了竹笛的清亮音色,笙的声部则不断变化,营造出一种平静的音乐氛围。接下来的“联谷曲曲”部分(第38—66小节)利用各声部的音色优势,描绘了一幅生动的景物画面,音乐动力逐渐变得活泼。“叠嶂重重”(第67—91小节)通过浓郁而紧凑的和声处理,增强了浓雾与树木之间的互动效果,加深了音乐的层次感和复杂性。在这一段中,笙的声部大量运用了花舌技巧和颤音,和弦音的密集变化呈现出山景的晦涩和压抑感,塑造出音乐中的紧张与神秘效果。
在“千草泣露”(第92—106小节)中,音乐变得更加狂躁,通过大量不规则的节奏变化,刻画了风中草地的激烈动态。而“孤风吟松”(第107—114小节)通过各声部间的即兴演奏,呈现出具有发散性的幻想旋律感,再现了风声和鸟鸣,为听众呈现了一幅灵动的音乐画面。作品的最后,“共坐白云间”(第115—145小节),则回归至一种平静而悠闲的状态,音乐色彩模仿白云的浮动,创造出一种身临仙境般的听觉体验。整个作品巧妙运用了各种器乐之间的共性和个性,通过音乐个性化与音响形态的转换,展现了实体与艺术之间的三层结构,包括现实样本、视觉艺术形式,并通过诗意化的语言对原始文本进行再创造,增加了音乐作品的深度和多维度的艺术表现[2]。
二、“跨媒介”创作的美学特征
(一)气息处理与灵动美
音乐布局中对气息的精心处理反映了音乐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通过模拟人的呼吸状态来控制时值长短和空拍,体现了一种类似于绘画中“留白”技法的空间感。特别是在吹奏乐器的演奏中,这种技法通过具体的指示性文字和强调得到了更为显著的表达。例如,在作品的第105小节,竹笛与笙采用动感的剁音和锯气技巧来预示高潮的临近,从而加强了音乐表现的紧迫感。
气息的精确控制建立了音乐表现与听众感受之间的桥梁,增强了音乐的真实感和参与感,并影响了音乐的动力表现。此外,音乐的灵动之美也与泛音列的运用密切相关。泛音列,作为音乐声音的本质组成部分,通过在乐曲中的独特单音表现,展现出各乐器之间的微妙状态差异。这种状态差异引发的声音“时间差”有效地增加了作品的空间延展性,使得音乐表现更加悠长而深远。音乐保持了其诗意的连贯性,音型的远近表现、画质的浓淡对比,以及音乐个性化的鲜明与模糊,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听众的体验和感知,深化了音乐作品的艺术表达和情感传达。
(二)音色组合与意境美
《共坐白云间》的创作初衷侧重于画面的优先表达,整首乐曲的色调设计反映了淡雅且富有中国绘画意境的美学理念。它捕捉并展现了这种意象,通过和声色彩与诗意意境的融合,利用音乐的层次感来呈现水墨画从淡到浓的过渡。音乐在表达上具有延展性,通过和声色彩的运用填补了音乐绘画中的留白,而音乐质感的变化则通过描绘“山”的远近景观对比来体现。乐曲中使用了持续音、单音、长音、波形线条、滑音、颤音等多种线性旋律材料,这些材料在乐曲发展过程中通过各种变形深化了概念性的理解。特别是,“虚按”“重颤”“滑音”“揉弦”“泛音”等技法,不仅满足了技术上的需求,也深刻地描绘了音乐意境中的“虚景”,通过这些处理达到了水墨画中的“淡雅”意境,为作品增添了一层诗意氛围[3]。
在音乐创作中,作曲家的感知力与想象力是展现作品深度和广度的关键。特别是在通感的运用上,作曲家需要具备将和弦与调式中的色彩“看”出来的能力。《共坐白云间》的音乐创作风格个性化地运用了“通感”手法,将音乐与人的感官体验紧密联系。通过诗句中关键词的意境来表现音乐,使聆听者不由自主地跟随身体的感官进行想象和本能反应。神秘主义经验中提到的“嗅觉能听、触觉能看”,这种将各种感觉混合的方式也是佛家与道家常见的讨论。例如,“老聃”能“耳视目听”,古代诗词中常以“耳目内通”来表现通感中的诗意与境界。
三、“跨媒介”的意象营构
(一)文本性的直接“意象”
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美通常建立在鲜活而富有生命力的自然意象之上。近年来,国内民族室内乐创作中涌现出许多富有创新意义的作品。这些作品如何在保持鲜明的现代创作风格的同时,又能展现出朦胧的诗意意象?意象性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有中国古代诗歌才能充分体现这种思维及其语言表达。在这种文化语境下,结合作曲家作品中的象征意义与精神表达,如“寒山”这一词汇,在中国诗歌中极具代表性,象征着冷寂的山谷——不仅是诗人游览咏叹的可见之景,更散发出一种超然的禅意象征。
寒山子,这位唐代著名的诗僧,以“寒山”为栖居之所,他的诗歌和文字中蕴含的寒气与冷意转化为深邃的禅意象征。在作品《共坐白云间》中,作曲家从寒山的诗篇中提炼出关键词,并通过重新组合这些词汇构建了七个意象化的段落,形成了一个连贯的音乐结构。“寒山”作为一个意象符号,虽然外在形态显得单一和稳定,但其内在变化却极其丰富多样:既能提供远眺的宏观视角,也能深入描绘如“草”这样的微观事物,展现出包罗万象的气势。因此,在组织这些意象时,作曲家刻意创造出与意象布局相匹配的音乐动态,旨在提供更立体的听觉体验,并丰富音乐与诗歌之间的关系表达。这种深思熟虑的构思不仅增强了音乐的层次感,也加深了听众对作品意境的理解和感受,使其在全球疫情这一严峻历史背景下,能够更好地体现对生命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尊重与渴望。
(二)音响性的间接“意象”
作品的乐器编制及设计体现了作曲家在音乐文本和音响传达诗意方面的深思熟虑。探讨音乐结构如何转化为具体的诗意表达,揭示了文本与音响如何共同实现诗意的呈现,逐步阐明了音乐如何体现其独特的意境与空间感。这种方法展现了作曲家如何通过精心设计的音乐语言来塑造和加深听众的空间感知与情感体验。
在《共坐白云间》中,听觉体验始于竹笛的微弱音调,引入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氛围。笙的声部与其他乐器相互呼应,竹笛与古筝的音色尤为突出,成功捕捉并表现了寒山的静谧与清凉。这种意境随着音色向高音区过渡而变得更加激昂,最终又逐渐回归寂静。竹笛随后成为主导声部,引领着乐队描绘寒山奇景的不可预测变化,音色从浅入深,使听者产生一种视觉景象由远及近的联觉体验,仿佛视角环绕山间旋转。竹笛的断音带来了一种严峻之感,随后渐渐归于静寂。琵琶与中阮的突入以及其他声部的相互呼应带来音乐的再次集中,并逐渐过渡到持续的长音。二胡的加入与竹笛的断音相配合,结合古筝的低音弦,共同营造出音乐的厚重感。笛声的顿音释放出深沉的箫声,二胡随后模仿鸟鸣,增添了音乐的生动性。中阮与琵琶如对话般的互动,以及古筝的随意泛音,增强了音乐的空灵感。二胡的旋律柔和,古筝的琶音则表现出音乐空间的轻盈。音色之间的交错对话使各声部更显独立,扬琴的音色突显了白云间的清凉感。最终,二胡伴随着古筝的单音,逐渐使山中神秘的风景意境回归于想象,从悠扬的笛声中再次回到山中的寂静。乐曲的结尾,音乐表现出的凄凉与空寂感随着各声部的长音逐渐减弱并远去,增强了作品的空间感。
四、结束语
探究如何通过音乐创作弘扬民族文化自信是每一位中国音乐家的重要任务,而作曲家则需要不断创新和突破来推进这一进程。他们致力于将感官视觉体验与想象力深度融合,从而激发听众在欣赏过程中的通感与想象。《共坐白云间》正是在此背景下探索并实践了“跨媒介”的思维,旨在提炼创作与分析思考之间的共生关系。这种创作思维依赖于作曲家对相同特征的多角度、个性化探索,呈现出强烈的个人视角。因此,媒介转化难以形成统一的理论。作曲家通过自己的民族室内乐作品《共坐白云间》来进行阐释,将个人的创作实践、思考与运用融入其中,作品的各种表现、内涵与意境以及音乐呈现的状态都取决于作曲家的主观创造力。
“跨媒介”的应用不仅是融合西方技术,更是一种有效采用多样音乐文化语汇的策略,揭示了作曲家对音乐意境的深度追求。通过具体的艺术创作实践,作曲家追求“诗乐融合,古今对话”的艺术境界,为现代音乐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刘鹏.一花一世界——陈晓勇《时代万花筒》的音乐分析[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20(03):34-52.
[2]谢嘉幸.音乐的语境——一种音乐解释学视域[J].中国音乐,2005(01):64-75+152.
[3]潘建伟.论艺术的“出位之思”——从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的结论谈起[J].文学评论,2020(05):216-224.
基金项目:四川音乐学院院级科研项目“跨媒介作曲思维的应用实践——以作品《共坐白云间》为例”(项目编号:CYXS2020044)。
作者简介:刘鹏(1986-),男,四川成都人,博士,副教授,从事作曲研究;吴艺璇(1994-),女,江西景德镇人,硕士,从事群众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