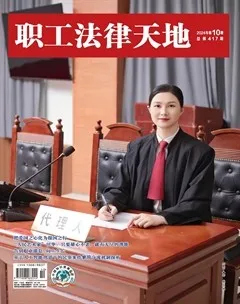探究非法经营罪中的“违反国家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非法经营罪属于一个“口袋罪”。“口袋罪”是学界对于某些构成要件行为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的罪名的俗称,一些罪名因构成要件行为模糊而在司法实践中易被滥用。“口袋罪”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在少数极端情况下,执法部门基于秩序和安全的角度要处罚某种行为时,需要用一些罪名进行规制,但如果无限制地扩张,会出现极少部分冤案。因此,执法部门既要保留本罪又要对本罪进行限缩。本文将选取两个典型案例,探讨限缩“口袋罪”的思路、方法,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与行政法责任界限的角度深入研究如何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
一、非法经营成品油案例分析
(一)非法经营成品油案情
案例一:张某某非法销售柴油案例分析。
2022年11月至2023年1月,张某某未经许可,多次购买柴油储存于自己的汽车修理厂和砂石厂,并通过非法销售柴油牟利,共获利4万余元。后来,张某某再次购买柴油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查获。经安全风险评估,张某某的非法经营行为具有重大的安全隐患,可能导致严重事故发生。云南省昌宁县人民法院判处张某某犯危险作业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并禁止其在缓刑期间从事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等活动。同时,相关部门没收其违法所得。
案例二:李某某擅自从事危险物品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案例分析。
2021年9月16日至12月23日,李某某未经批准,使用改装后的厢式货车,先后三次从宁夏固原市西吉县某加油站购买92号汽油共1130L。之后,他将汽油储存于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黄河路居民区旁一个彩钢房内,并销售给过往车辆。2022年1月8日,李某某被景泰县公安局查获,被扣押轻型厢式货车一辆、储油罐两个、92号汽油538.05L、加油机一台以及违法所得钱款2030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某某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未经依法批准,擅自从事危险物品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其行为已构成危险作业罪。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李某某自愿认罪认罚。根据李某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景泰县人民法院对该案当庭宣判,李某某表示服从一审判决。
通过法院对上述两起案件的裁判,可以发现法院认为张某某、李某某等人非法经营柴油、汽油的行为只能定为危险作业罪,而未构成非法经营罪。但是,案例一是自2023年1月1日柴油被列为危险化学品以来,昌宁县人民法院判处的首例危险作业罪案件,在这之前此类此行为都被定为非法经营罪。法院认为,根据2004年商务部出台的《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规定,柴油为成品油,而行为人非法经营柴油的行为违反了该《管理办法》,等同于“违988382006e0f45dcb67e7602638fd59b反了国家规定”,应当构成非法经营罪。但是,这种定罪逻辑是否准确,笔者认为值得深入探究。
(二)无证经营成品油问题争议焦点
关于成品油的定罪问题,在实践中主要存在两个争议点:第一,无证经营汽油、柴油等成品油的行为是否“违反国家规定”,且违反国家的何项具体规定;第二,对无证经营汽油和无证经营柴油,两者处罚时是否应进行区分。
1997年《刑法》修订前,《关于加强成品油市场管理和整顿的通知》规定是“只要取得许可就可以从事成品油经营活动”。1997年《刑法》修订后,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颁布,国家制定了多项法律、行政法规和决定,成品油经营资格许可制度油然而生,刑事司法中认定非法经营罪的依据就是这一制度和这些法律法规。具有争议性的是2002年国务院发布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管理条例》)仅规定成品油中的汽油属于须经国家许可经营的物品。《管理办法》第四条将汽油、柴油等成品油都纳入了经营许可制度的范围,这就产生了矛盾之处。这也属于成品油的第二个争议点。
在司法实践中,针对成品油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管理办法》是部门规章,《管理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故《管理条例》的效力位阶高于商务部制定的《管理办法》。因此,无证经营汽油且情节严重者会构成非法经营犯罪,但无证经营柴油等其他成品油的行为不是犯罪,只被定为违法。最主流的做法是直接依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将经营汽油和柴油等所有成品油都判定为有罪。由此可见,违反商务部制定的办法,属于“违反国家规定”,可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但是,用这种思路进行推理,会发现只要违反了行政许可,就属于“违反国家规定”,从而构成非法经营罪,导致非法经营罪变成巨大的“口袋罪”。
二、“违反国家规定”与行政法的关系
若仅以“违反国家规定”,就认为未经许可经营柴油、汽油属于非法经营行为,笔者认为有失偏颇。这不仅会使非法经营罪的处罚范围无限扩大,直至变为“口袋罪”,也会使得《刑法》与行政法责任边界不清,使本该由行政法处罚的事项进入《刑法》领域。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非法经营罪的入罪路径进行讨论,明确《刑法》应仅在行政手段不足以有效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时介入的思想,在涉及本罪的行为上处理《刑法》与行政法之间的边界问题,避免《刑法》过度适用。
在1997年《刑法》修订后到《行政许可法》颁布前这段时间,行政许可多以行政审批的形式出现。但是,实际上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完全不同。根据行政法的相关理论,行政许可的特征之一是外部性,而行政审批对内对外事项都能审批。因此,当时模糊了两者的概念,使得行政许可具有任意性特点。当时,我国废止了大量行政审批,这在一定程度上限缩了非法经营罪的范围,使很多行为不再构成犯罪。2003年,为了巩固行政审批改革成果,《行政许可法》得以通过。由于设定经常性许可的只能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故理论上相较于之前行政审批的方式,设定行政许可应当更加严格规范,这样有利于限缩非法经营罪的范围。《行政许可法》实施后,违反行政许可行为的法律性质如何,是否所有违反行政许可的经营行为都属于《刑法》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仍有待商榷。
法律、行政法规数量庞大,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中存在大量违反行政许可的行为,实践中出现许多“违反行政许可的行为即直接等同于违反国家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的情况。由此可见,《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和前置法层级的提升,并未有效缩减非法经营罪的适用范围,正如上文所述的案件中,司法机关在审判过程中甚至会将违反行政许可的行为直接被视为“违反国家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因此,深入探讨违反哪些行政许可才应构成非法经营罪很有必要,不能一概而论。
三、利用行政法限缩“国家规定”的范围
《行政许可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经行政许可,擅自从事依法应当取得行政许可的活动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换言之,应当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设立为犯罪的才是犯罪。这种情况下,非法经营罪已经按照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定罪了。尽管后面对于非法经营成品油的问题又出台了新的司法解释及法律法规,但是按照行政法的规定进行定罪量刑没有遵循《刑法》罪刑法定的原则。因此,我们应当从行政法的角度入手,探讨这一问题的解决路径。
行政许可可以分为五种类型,其中与非法经营罪相关的只有普通许可和特许,两者的性质和功能各不相同。普通许可主要用于控制风险,属于事前监督,而特许则用于资源配置,特许人获得的是国家授予的权利。因此,没有获得特许就从事一些经营行为,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从实体上看,都违反了法律规定。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和第三款规定的都是与违反特许相关的非法经营行为。因此,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思路处理:违反特许应当构成犯罪,而违反普通许可则仅为形式上的违法,属于行政违法范畴。对于违反特许的行为,如果《刑法》已有专门罪名,则应按照该罪名定罪;如果《刑法》未设立专门罪名,但有其他法律或解释规定了该行为,则可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款“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定罪,从而解决非法经营罪中的关于如何界定违反国家规定的问题。
四、非法经营罪的定罪思路
在司法实践中,非法经营罪是一个“口袋罪”,然而“口袋罪”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处于秩序和安全的角度考虑,要处罚某种行为时无法可依甚至“原地造法”也比在法律中留有一丝缺口可怕得多。因此,人们要找出一种限缩这种“口袋罪”的思路或者方法,使非法经营成品油等类似的非法经营行为清晰入罪。
判定一种行为时,要先看其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由于我国有关行政许可的法律法规数量非常多,法官应当判断法律法规中对这种行为设定的是普通许可还是特许。如果行为人只是违反行政许可中的普通许可即可出罪,则定为行政违法;如果违反的是特许行为,再去判断这种非法经营行为符合《刑法》的哪项规定。对于非法经营行为,若《刑法》单独设立了罪名就可以按照此罪名定罪,如果符合非法经营罪第一、二、三项,那么直接按照非法经营罪定罪。当《刑法》没有相关规定时,就要考虑能否按照《刑法》第四项定非法经营罪。应以行为人的非法经营数额为基础,并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前三项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相比较,使用有与之相当的刑事处罚的必要性,判断该行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从而认定是否可以按照“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定罪处罚。
结语
结合上述案件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刑法》应当体现谦抑性,仅在行政手段不足以有效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时介入。因此,刑事责任的适用要求行为的违法性达到较为严重的程度,明确《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侵害或威胁。这一标准需要与行政处罚的轻重相区分,避免《刑法》过度适用。上述案件中,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认定涉及哪些行为构成《刑法》中“国家规定”,不能无限制地进行扩大解释,应当找到限缩这种“口袋罪”的思路或者方法,从而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