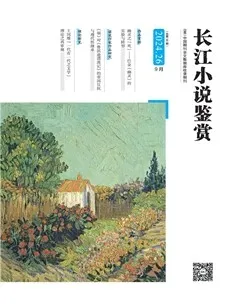于多变中寻求转变
[摘 要] 王安忆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其小说创作主要受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及城市文学的影响。王安忆身处时代之中,不断自觉进行转变,寻求新的突破,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从知青文学影响下稚嫩的青春自叙传写作,到寻根文学影响下对民族文化、家族历史之根的探寻,到女性主义文学影响下大胆的性题材描写、对女性命运的探索,再到城市文学影响下对地域视角的自觉寻找,王安忆不断发现小说创作与自我、社会、人类之间新的可能性,建构出了自己充满温情的心灵世界。
[关键词] 王安忆 知青文学 寻根文学 女性主义 城市文学
1980年代初,王安忆以个人的知青经验创作了《本次列车终点》《69届初中生》等多部知青题材的小说;1985年,《小鲍庄》发表,与当时的“寻根运动”相应和,一跃成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1986年和1987年陆续发表的“三恋”系列小说,以大胆的性描写引发争论,随后王安忆持续关注女性生命体验,探索女性命运;20世纪90年代,王安忆转向寻找创作的地域视角,创作了《长恨歌》《富萍》《天香》等长篇小说。在多种文学思潮的影响下,王安忆始终不拘束于某一种特定的文学思潮,不断自觉进行转变,寻求新的突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
一、知青文学:青春自叙式写作
20世纪80年代恰逢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时期,各种社会思潮与文化思潮相互碰撞、激荡,创造了极为活跃的思想空间。王安忆初入文坛时,以生活经验为材料,顺应当时的流行思潮进行创作。20世纪80年代初,王安忆陆续发表了《雨,沙沙沙》等根据自己两年在徐州插队的经历及六年在徐州文工团的生活经历创作出来的小说,这些知青题材的小说带有强烈的青春自叙传色彩,初入文坛的王安忆用少女般的温情眼光,创作了其温情、稚嫩的早期作品。
1.个人经验的书写
王安忆1970年前往徐州插队落户,1972年调往徐州文工团工作,1978年在知青返城大潮中调回上海,之后在《儿童时代》杂志社工作。从并不完整的学生生涯到下乡当知青再到重返上海在杂志社工作,可见王安忆的人生轨迹是比较简单而明朗的,这些人生经验也是其创作初期的素材。创作初期,王安忆注重使用个人生活材料,书写个人生活经验和独特感受,创作了包括《雨,沙沙沙》《广阔天地的一角》《命运》《幻影》以及《69届初中生》等与个人经验相关的“雯雯”系列小说,此系列小说以女知青雯雯作为主人公,书写了雯雯各个阶段的成长经历和感受。雯雯最先出现在王安忆的成名作短篇小说《雨,沙沙沙》中,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在雨夜下班的青年女工雯雯一路上的所思所想,展现了雯雯对爱情、理想的追求。短篇小说《命运》中,雯雯是上海知名作家的女儿,知青插队时受母亲战友的关照,成为淮北小镇乐团的第二大提琴手。《广阔天地的一角》中,雯雯是十七八岁的插队女知青。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中,雯雯从家里的小毛头、无法送进幼儿园的幼儿、朋友不多的小学优等生,一路成长到在淮北插队的知青,她在知青返城浪潮中返沪,最后结婚生子,小说呈现了雯雯的人生历程。王安忆在与张新颖的谈话中曾谈道:“‘雯雯’这个人物与我个人经验有关。”[1]“雯雯”系列小说中,雯雯的形象有许多王安忆的影子,王安忆本人的早期经历在雯雯身上体现出来,并赋予了雯雯一部分自己的性格特征、理想以及喜好等,王安忆的早期写作中,自我的经验就是构筑其小说世界的最贴切、最直接的原材料。
2.温情笔触代替伤痕叙事
最初一批的知青小说中,作者普遍强调了知青岁月的伤痛,但王安忆别具一格地以温情的笔触代替伤痕叙事,通过平凡人的生活展现时代,从日常生活剖析回城知青的命运以及相应的社会问题,深刻反思之中又不乏温情,王安忆以这样独特的角度开始她的知青叙述及对知青身份的思考。
《本次列车终点》中,王安忆描写了知青陈信历经十年插队重返上海后经历的种种现实矛盾及精神困惑。小说中,作者避开了当时流行的伤痕叙事,进行了温情化的处理。面对知青下乡“两丁抽一”的政策时,妈妈左右为难,陈信主动让哥哥留在上海,自己下乡吃苦;知青返城浪潮中,陈信弟弟毫无怨言地放弃工作机会,选择让陈信顶替下岗母亲,以此调回上海;陈信回到上海后尽管因房子问题与哥嫂产生嫌隙,但仍然彼此体谅,大嫂因担心陈信而落泪,大嫂的一句:“阿信,你可别想不开!”哥哥的一句:“回家吧!”[2]都饱含着亲人之间的无尽温情,而陈信也感念家人的艰辛:“家毕竟是家,就因为太贫困了,才会有这些不和。亲人,苦了你们了。”[2]尽管经历了插队的十年艰辛,重返上海后也感到处处不适应,然而以陈信为代表的知青仍然相信人生中有很多欢乐,仍然相信“只要到达,就不会惶惑,不会苦恼,不会惘然若失,而是真正找到了归宿”[2]。在王安忆的笔下,主人公即使在匮乏的现实生活中依然追求着理想与真善美。她将知青岁月的伤痛以温情的笔触优美地表现出来,文笔虽略显稚嫩却也不乏深刻思考。
二、寻根文学:精神之根的追寻
初入文坛的王安忆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然而很快这种狭窄的个人经验书写就使她感到不满足,她开始寻求新的转变。1983年秋,王安忆随母亲前往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文学活动,不同民族间文化的交流让王安忆打开了视野,逐渐把关注点从自身转到了民族精神文化上来,她开始酝酿创作的转变。回国之后,适逢国内寻根运动正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进一步打开了王安忆的视野。多重影响之下她逐渐从狭窄的个人经验中抽离,站在民族文化的高度写作,创作出更有意义的小说。
1.对民族文化之根的挖掘
《小鲍庄》是王安忆创作道路的新尝试。“小鲍庄是个重仁重义的庄子,祖祖辈辈,不敬富,不畏势,就是敬重个仁义。”[3]鲍五爷老年痛失唯一的孙子,队长及时站出来宽慰他说:“小鲍庄谁家锅里有,就少不了你老碗里的。”[3]曾有人劝鲍秉德跟疯媳妇离婚,再娶一个时,他以仁义之名一口回绝。小说中最能体现小鲍庄仁义精神的,便是小英雄捞渣。捞渣出生于鲍五爷孙子离世那一天,因此鲍五爷对捞渣一直心有怨恨,觉得他的出生抢走了孙子的命。但捞渣却从小就喜欢和鲍五爷亲近,时常给鲍五爷聊天做伴、送吃送喝。洪水肆虐之时,所有大人都只顾自己逃命,而小捞渣却不顾安危,为救鲍五爷而死。捞渣身上体现了中国人的仁义本色。捞渣死后小鲍庄人一边享受着消费小英雄事迹带来的红利,一边却嫌晦气,不肯用自家的扫帚给捞渣扫坟头。这些人的“仁义”建立在愚昧、自私之上,麻木冷漠的“假仁义”行为与小英雄捞渣的“真仁义”之举相比,极具讽刺意味。
2.对家族历史之根的追溯
王安忆将个人的成长史纳入寻根的范畴,创作出了《伤心太平洋》和《纪实与虚构》等小说,追溯家族历史之根,为寻根运动交出了别样的答卷。
1993年,王安忆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构建母系家族神话。从小说的整体结构来看,《纪实与虚构》这部小说史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单数章节横向讲述作家的个人成长经历,复数章节纵向追溯家族历史本源。“很久以来,我们在上海这城市里,都像是个外来户。”[4]外来者的孤独感使“我”感到焦虑,于是“我”开始追溯家族历史,试图寻找到自己母系家族的源头,可惜的是,母亲自记事以来便过着孤儿一般的生活,家族过往难寻踪迹。小说结尾写道:“外公以一个出走的形象结束了我们家族的全部故事。”[4]对母系家族的追溯最终失败。同年,王安忆又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中篇小说《伤心太平洋》,讲述父系寻根的故事,在这篇小说中,作者追溯的父系家族的历史故事大部分都围绕爷爷奶奶在新加坡艰辛的一生展开。在追溯父系家族历史的过程中,王安忆发现父系家族其实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漂泊群体,是无根的浮萍。“人类其实是一个漂流的群体,漂浮是永恒的命运。”[5]在不断的家族探寻中,王安忆将人类个体存在的历史性思索,融入自身和家族历史的寻找过程中。正如张新颖所说:“偶然的个人的寻根行为,实质正反映出社会普遍的无根焦虑。”[6]王安忆借个人寻根的焦虑,描绘出人类社会共有的寻根情结与漂浮命运。
三、女性主义:自觉的女性意识
1980年代中期,王安忆的笔触触及人性中最隐蔽且活跃的性心理区域,创作出了直接写性的“三恋”系列小说。“三恋”之后王安忆鲜少涉及性题材,虽然男女情爱仍是其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但对女性命运的探讨才是其落脚点。女性作家的身份使王安忆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探索有着天然的感知力,她深刻挖掘与剖析女性的真实处境和精神困顿,不断探索女性的生存出路,具有先锋意义。
1.突破禁忌的性爱描写
1986年和1987年,王安忆先后创作发表了小说《荒山之恋》《小城之恋》及《锦绣谷之恋》。“三恋”以两性为题材,从纯粹的性别角度来思考两性之间的内在联系,虽然“三恋”中对性的描写并不十分露骨,但在那个仍较保守的年代,人们依然无法接受这样直接的性描写。王安忆突破常理禁忌,大胆直接地描写了男女之间精神与肉体的吸引与碰撞,既写出了人类的原始生物本能,又具有现代的性爱意识。《荒山之恋》中,金谷巷女孩和“他”相遇在大上海一隅的文化宫,“他细长的手指在她领脖里轻轻地摸索,犹如冰凉的露珠在温和地滚动。她从未体验过这样清冷的爱抚,这清冷的爱抚反而激起了她火一般的激情。他好似被一团火焰裹住了,几乎要窒息。”[7]狂放的爱抚、如火的激情、销魂的窒息,正是王安忆笔下都市女性冲破身体禁忌时的狂放呐喊。《小城之恋》描写了同在剧团的青春男女间欲望的萌动、身体的交锋、肉欲的碰撞;《锦绣谷之恋》写了女编辑精神的出轨,她对性爱的渴望被自我压抑。“三恋”成为20世纪80年代王安忆对人类欲望的一种有效表达,也触及了觉醒女性的性爱悲剧这一以往被遮蔽的话题。
2.和谐的两性关系描写
在处理两性关系时,王安忆坚持男性和女性应该携手共进、互相补充和配合,以达到天然的和谐平衡状态,而非一方压倒另一方。小说《天香》中,虽然“天香园绣”是以女性为主体创造的,故事的主线也是围绕着“天香园绣”的三代传人小绸、希昭、惠兰展开的,女性已然成为叙事的主体,男性虽然渐渐退隐在叙事中心,但在申家女性探索自我价值的道路上依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男性在家族中形象的弱化并不意味着消失,因女性正是经由男性引入园林,从而得以构建自身”[8]。尽管申家女眷已经凭借“天香园绣”盛名在外,能够取得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独立并支撑起了家庭的开支,但不可否认的是,天香园是因男性主人公申明世中进士而造,也正是申明世做官完成了财富累积,天香园中的女性才可以不用顾虑生计等杂事,有时间研习精进绣艺,“天香园绣”能够进入市场,仍需要男性出面交易。小说中,申家的男性虽然挥霍成性,但也并非恶人,他们有自己的享乐观念,没有仗势欺人,只是热热闹闹地享受,更是在朝廷要造丹凤楼时大气地捐款……王安忆站在理性的角度审视两性关系,在以女性为主体的小说中也竭力塑造男性形象,使男女两性达到一种和谐的关系,显示了作者深邃的思想性。
3.女性出路的执着探寻
王安忆一系列女性主义的作品并非以自身女性经验迎合文学潮流,而是出于一种对女性命运的自觉探索。王安忆早期的“雯雯”系列作品中,雯雯始终幻想着有男性救赎自己,如《雨,沙沙沙》中雯雯“将脸贴在阳台的落地窗上,她的眼睛下意识地在阳台下的树影中寻找着”[9],寻找的就是幻想中的“小伙子”,希望他会出现,带自己脱离这庸俗烦闷的生活。这一阶段的作品女性主体意识较弱,伴随着无意识的模仿与依赖,那些女性既渴望反抗男性权威,又幻想男性的救赎。到了“三恋”系列小说时期,王安忆开始尝试用更强烈的反抗方式来凸显女性意识,以情欲的放纵彰显女性的自主意识与反抗。《长恨歌》中,薇薇不介意小林原是被好朋友抛弃的男人,仍以纯粹的真心与小林交往,最后收获了幸福。《富萍》中,乡下女孩富萍面对上海的繁华时仍坚定内心不被诱惑,最终选择了与家庭清贫但为人勤恳踏实的跛脚青年相伴一生,过着虽贫穷却有希望的生活。王安忆自觉地刻画了一系列女性的心灵觉醒与突围,这样的女性探索路径正体现了作家独特的女性思考。
四、城市文学:地域视角的探寻
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城市面貌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敏锐的作家迅速捕捉到城市发展带来的新体验,更注重理解和表现城市。“上海生活是我唯一的写作资源”[10],王安忆以敏锐的眼光审视着上海,记录日新月异的城市景观变化,关注城市人精神的匮乏与迷茫,创作了一大批以上海城市为背景的小说,逐渐找到了自身文学创作的独特地域视角:上海书写。敏锐的生活视角、细腻的女性视角、纪实与虚构的融合构成了王安忆上海书写的鲜明特色。
1.细碎的日常书写
王安忆的作品中很少直接叙述大的历史事件、社会变革,而是以小见大,从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写起,不厌其烦地叙述市井家常小事,通过这些最普通的市井阶层的细碎的日常生活,表现其对时代、社会的思考。《长恨歌》描写了市井女性王琦瑶一生的故事,体现了上海这座城市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的变迁,却没有宏大夸张的历史场面,作者落笔于细小的生活日常,描写的人物大多是平凡的市民小人物,所涉及的场景也大多在里巷弄堂之间。《长恨歌》开篇,作者就花费了一章的内容描写弄堂、流言、闺阁、鸽子及弄堂女儿的代表王琦瑶,不厌其烦地用琐碎的笔调为故事的展开搭建了一个极具世俗化、日常化的场景。小说讲述了王琦瑶从闺阁少女时期到竞选上海三小姐成为李主任情妇,到搬进平安里弄堂的日常生活,打牌、喝下午茶、买菜做饭、围炉夜话、当家庭护士给人打点滴、与几个男人的情爱纠葛、朋友间的友情与隔膜……整部小说充满了细密琐碎的日常生活书写,时代的动荡在王琦瑶的生活中几乎看不到影子。作者正是通过这样一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来表现上海民间的世情风貌,从而揭示上海都市的文化内涵。
2.细腻的女性视角
“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11]女性作家的身份使王安忆天然地具备更细腻、更独特的叙事视角,纵观王安忆上海书写的小说,王安忆惯用也擅长描写女性,将女性的个人命运融入都市的发展之中,通过女性在时代变迁的风云际会中飘摇沉浮的生活来描绘一座城市、展示一段历史。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桃之夭夭》主要围绕旧艺人笑明明及女儿郁晓秋二人的悲苦命运展开叙述。王安忆从最贴近女性经验的视角,用细腻的笔调写出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小说对郁晓秋的描写,涵盖了其儿童时期、中学读书、插队下乡、返城工作到婚姻生活的人生成长脉络,包括母亲的打骂、哥哥姐姐的冷漠疏离、外人的流言蜚语、失败的爱情,最后为替因难产而去世的姐姐照顾孩子,郁晓秋勉强与姐夫组建家庭,作者塑造了一个生活在苦难中仍然坚韧的上海普通女性形象。王安忆眼中的上海即女性的化身,女性的生存底蕴浸润于都市民间精神之中,“她从小就没有目睹过什么幸福,但并不妨碍她欢欢喜喜地长大”[12],郁晓秋的坚忍品质正是上海市民精神的写照。
3.纪实与虚构相融合
“小说的生活就是这样,在真与假之间穿行往来,将真实的存在变为虚假,再让虚假的在纸上重塑一种真实。”[1]王安忆一贯坚持写实主义的写作观,主张文学要通过生活的表象探问本质。从日常生活中积累写作素材,经过艺术加工,虚构、推演出故事发生的路径,以表达对社会、时代的深刻思考。小说《考工记》的创作素材来源于上海一个守宅老头的故事。守宅老头向王安忆讲述了多年来自己向上级部门反映要求修葺这座房子,几番波折,最终却因宅子家族成员问题仍未能成功修葺或置换的种种经历。王安忆把守宅老头的个人遭际与上海都市发展的背景相结合,虚构了陈书玉的一生,展现出人与物的深刻羁绊与人物孤独的宿命感。谈起《天香》的创作缘由,王安忆说:“很早时候就从上海地方的掌故里看到有一种特产,‘顾绣’,描述的笔墨极少,可是有一点却使我留意,那就是女眷们的针黹,后来竟成为维持家道的生计……”[13]对历史记载中女性发展之路的好奇,推动着王安忆用文学的方式还原那个时代的沪上传奇。
五、结语
王安忆是一个不断寻求转变的作家,纵观其创作生涯,她受到了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城市文学等多种文学思潮的影响,但没有一种文学思潮能够完美诠释王安忆的创作,她就是这样一个从不给自己设限、自觉寻求转变的作家。从写作初期只能抓住个人经验书写的不自觉创作,到企图突破个人经验探索人类普遍性的命运,到寻根运动中自觉对民族文化之根的审视,到挖掘女性的独特生命体验、探讨女性命运,再到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Gjab80yDgOGwZjYjHd3tgQ==一系列的上海书写,王安忆的创作历程经历了一个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变过程,最终她将文学视野落在都市民间,用文字建构出自己独特的充满温情的小说世界。
参考文献
[1] 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 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J].上海文学,1981(10).
[3] 王安忆.小鲍庄[J].中国作家,1995(2).
[4] 王安忆.纪实与虚构[M]//王安忆自选集之五:米尼.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5] 王安忆.伤心太平洋[J].收获.1993(3).
[6] 张新颖.坚硬的河岸流动的水——《纪实与虚构》与王安忆写作的理想[J].当代作家评论,1993(5).
[7] 王安忆.荒山之恋[J].十月,1986(4).
[8] 陈树萍.“德”“才”之间:才女主体性的建构——《天香》论[J].南方文坛,2013(6).
[9] 王安忆.雨沙沙沙[J].山东文学,2008(8).
[10] 刘颋.常态的王安忆非常态的写作——访王安忆[N].文艺报,2002-01-15.
[11] 王安忆.上海的女性[J].海上文坛,1995(9).
[12] 王安忆.桃之夭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13] 王安忆,钟红明.访问《天香》[J].上海文学,2011(3).
(特约编辑 刘梦瑶)
作者简介:唐莹,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