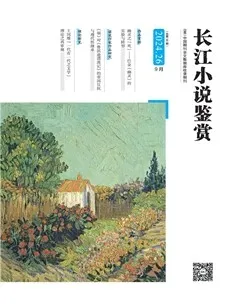不同的地理空间表达
[摘 要] 张贤亮与贾平凹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备受关注的作家。张贤亮与贾平凹建立了友谊,两人的思想和文化趣味差异较大,却能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与两人的性情、包容的文化底蕴有关。他们两人的交往构成了“商州”与“银川”地理空间的表达与对话,实现了主体情绪的共鸣。
[关键词] 张贤亮 贾平凹 交往
张贤亮与贾平凹都是中国当代文坛备受关注的作家。两人在20世纪80年代因文学创作而相识、相遇,经历了时代变化,体现了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
一、现实之中的交往
1.直接的文学交游活动
张贤亮自1979年“复出”后,《朔方》接连刊登其6篇小说,引起学者的关注和议论,成为宁夏文坛的“一棵大树”,他在1981年因《灵与肉》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提升了宁夏文学的知名度。同时期的贾平凹也已经成为陕西文学界重点推介的青年作家,评论组还召开了贾平凹作品讨论会。据宁夏文联大事记载,1982年11月3日,时任宁夏文联委员的张贤亮接见来宁夏召开座谈会的贾平凹、和谷,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两人同为各自省份的文坛新秀,在那个文学氛围浓厚的时代,两人因各种座谈会有不少见面机会。有关张贤亮来西安,陈深有这样的记录:
“最近,应《文学家》编辑部的邀请,张贤亮同志专程从银川赴西安参观访问,我终于有机会结识了这位历尽坎坷的作家。元月十一日上午,我们乘车来到省出版局新近落成的办公大楼七楼会议室,参加《文学家》编辑部为几家兄弟期刊与张贤亮见面而召开的座谈会。”[1]
同时,张贤亮在纪念路遥的文章中写道:“西安笔会还安排我在‘人民剧院’讲了一次‘创作谈’……王愚跟我笑着说:‘对了!贾平凹刚买了个电冰箱,冰箱里放的只是辣面子和醋。’”[2]张贤亮来到陕西,感受到了西北作家与农村割舍不断的情感与生活方式。在此次笔会之前,张贤亮与贾平凹已经有过一次交往,当时贾平凹在陕西已经小有名气,因此当王愚讲到贾平凹的时候,引起了张贤亮的注意。
1990年,两人因庄重文文学奖而再次相遇,1990年度的庄重文文学奖,张贤亮任评委,陕西作家贾平凹、高建群、杨争光获奖。2010年,贾平凹艺术研究院成立之时,张贤亮发来贺信[3],2010年9月12日两人出席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第四届中国作家高峰论坛。张贤亮与贾平凹很少有私下的往来,但彼此关注对方。
2.共同关注社会发展和精神建设
两人不仅以作品反映现实,更以实践的方式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实现知行合一的文人抱负。贾平凹称写作是自己最好的生命形式:“我热爱我的祖国,热爱我们民族,热爱关注我们国家的改革,以我的观察和感受的角度写这个时代。”[4]张贤亮直接接触社会,带动农民工打造文化产业,将精神文化事业落地生根。
为促进西北地区文学事业的繁荣,2009年,张贤亮与贾平凹出席在西安召开的《西北电业职工文学作品选集》座谈会[5]。同时,两人共同参与到《中国治水史诗》的编撰工作中,该书首次以文学的形式全面梳理、褒奖中国历史上的治水功臣[6]。
2014年9月27日,张贤亮去世当晚,时任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立志得知张贤亮离世的消息,马上用短信告知贾平凹。贾平凹很快回复:“不太可能,再核实一下。”[3]听闻好友突然离世,贾平凹不愿相信信息的真实性。事后,贾平凹评价张贤亮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一个真诚的人,一个有趣的朋友”,现在这位朋友远行了,他为其燃了一炷香,在夜里深深地悼念[7]。
“一个优秀的作家”“一个真诚的人”“一个有趣的朋友”是贾平凹对张贤亮的评价。贾平凹曾经说自己认识的人多,好朋友却不多。从贾平凹对张贤亮的评价中可以得知,张贤亮是贾平凹为数不多的好朋友中的一个。
二、文学公共领域的交往
张贤亮与贾平凹不仅有现实的交往,还通过文学作品进行精神的交往。
1.不同的地理空间表达
1.1贾平凹的“商州”世界
任何文学的历史,只有把文学和创造这种文学的人民的社会和精神状态联系起来,只有把它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才能被人理解,才能加以研究[8]。贾平凹对商州的描写,经历了从“无意”到“有意”的过程。陕西作协1982年召开了贾平凹近作研讨会,对贾平凹的创作进行多方讨论,胡采认为贾平凹的经历和政治思想的修养不够h4TCJ29edPaejVMiIsepr7QpsTtGscwu5OtmGHL2hhY=,在这四天会议中贾平凹面色沉重、低头记录、一言不发[9],半个多月不再写一个字,回到商州“再去投胎”[10]。在此之前的贾平凹不免有“为稻粱谋”的创作动机,商州只是他的一个书写对象,而再次回到商州,不仅是因外在风波的触动,还因为自己陷入了创作迷茫期,乡下的生活唤起了他儿时记忆,帮助他度过了迷茫期。
商州对贾平凹而言,不是地图上的一个地方,而是“作为一个载体的商州,是我心中的商州”[11]。贾平凹从商州和西安两个角度看中国,因此在其笔下,商州、西安、中国的地理空间不断扩展,由内至外,由表及里,商州人从商州走向西安。从“改革三部曲”的时间化到“商州系列”的空间化,地方性的生活片段成为文学书写的故事,构建了文学意义上的商州。具体来说,贾平凹在商州的地理空间叙述中,通过具体的人的行为和记忆将当地文化凝固化、资料化。他笔下的人物质朴、善良,也聪慧、机智,能偏安于商州一隅,也能开眼看世界。在对商州地方性的叙述中,贾平凹彰显地方乡音、乡俗、乡情,彰显自身风格,用文学的方法观看商州,使商州生成了“地理自我”。
1.2 张贤亮的第二故乡
张贤亮的创作深受西北地域文化的影响。他自称对故乡江苏盱眙“懵懂、毫无印象”,对他成长的影响说不清楚。“可是我的‘第二故乡’却不少:重庆、南京、上海、北京、银川都可算一份。”[12]张贤亮在1962年赶集的路上偶然发现镇北堡衰而不败、破而不残,这是黄土地特有的生命力。不管是早期的《灵与肉》《土牢情话》还是中期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或是后期的《我的菩提树》,故事背景都是20世纪50—80年代的宁夏地区,小说中的人物是这一时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西北人。底层劳动妇女马缨花天真、爽朗、纯情,少数民族兄弟海喜喜外表看起来粗放不羁、暴躁蛮横,心底却纯朴、多情。宁夏的生活刺激了张贤亮书写的欲望:“我现在写作品,成了一名作家,是因为我头脑里的东西非喷射出来不可,正像怀孕九个多月的妇女要生出孩子一样。”[13]宁夏也为张贤亮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张贤亮对自己的生活背景的体认使其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宁夏乃至整个西北的自然风景、风俗民情、方言民歌等都是张贤亮作品的表现内容。
张贤亮小说的故事主要发生在西北的宁夏地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黄土高原的台地……一边毗邻内蒙古沙漠,一边紧靠着黄河的河套地区”[14]。“春天到了,从西山倾泻而下的大风,卷起细砂,铺天盖地地刮来土暴。”[15]宁夏的民俗也是其作品的重要内容之一。《灵与肉》中,“我”给马喂夜草,体现了宁夏20世纪50—80年代初的宁夏地区的主要耕种方式——“二牛抬杠”。张贤亮以自己突出的文学才能,创造了一个以宁夏地区为故事背景的小说世界,由此表现西北文化精神,进而扩展到对普遍人性的思考,让西北人和西北文化走向更大的空间[16]。
根据哈贝马斯前期对文学公共领域的探讨和后期对“戏剧行为”的言语交往活动的阐述,文学交往可被定义为平等主体之间以文学为媒介,在语感形式的共契、情感的共鸣、意义的共识三个层面达成的交往型意义活动[17]。同为作家的张贤亮与贾平凹在创作领域深挖自己的精神故乡,在私人叙事与文学公共领域的审美活动中体现了物感/语感之感性层面的审美价值,体现了情绪共鸣,完成了主体间的理解与共契,实现了精神上的沟通和对话。
2.文学表达情绪的理解与共振
张贤亮与贾平凹的生活经历虽不同,但内心深处都有孤独与自卑的情绪,在文学领域的审美交往中实现了共鸣,他们将主体的共鸣拓展到现实的公共空间中实现与世界的对话。
2.1主体生存情绪的共鸣
首先,他们内心深处都有孤独与自卑情结。情感的价值在于真实,文艺作品的价值也取决于真实。厨川白村认为,“无压抑即无生命的飞跃”[18]。痛苦产生文学,作家在身体或思想上陷入苦闷与徘徊后,产生了“不可言喻的情绪”,从而激发了文学作品的产生。物质生活的贫乏、精神的压抑和痛苦使张贤亮孤独和寂寞,这种孤独和自卑的情绪构成了其思想的深刻性。写作就是向人倾诉他的感受,他的孤独感并没有因为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而消除,于是只有不断地倾诉下去[19]。贾平凹自卑情结的产生主要因为少年时体质弱,在大家庭中不受重视,很少得到外界的肯定和赞扬。他在孤独的情绪中以书为友,凭借自己的写作能力赢得村里人的尊重,甚至被领导干部看中,并因自己出色的表现被推荐到西北大学学习,由此开始,其对人生的态度变得积极主动。但贾平凹在遭遇人生的重大变故如父亲去世、婚姻突变、疾病缠身后,内心深处的自卑感又再次出现。创作对贾平凹而言是苦难生活中甜蜜的梦,他从外界的认可中获得了价值感,同时这种孤独与自卑的情绪也使他的作品中出现一系列对神秘现象和对人特殊的感知力的描写,他描写了一种在主观与客观、想象与现实的互相渗透中形成的“混沌”状态,这是他表达情绪的方式。
其次,他们具有反叛和创新勇气。他们的交往时间发生在激情的20世纪80年代,两人有着共同的生命共振和相互理解的生命体验。他们的创作经历了从早期“为稻粱谋”的创作心态到逐步走向内心自由的状态。张贤亮在20世纪80年代大胆写性,用诗化的语言回望自己的人生情感历程和对生命的思考,表现人在灵与肉两方面的痛苦和悲哀。贾平凹被称为文坛的“鬼才”,在不断的艺术探索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精神,从早期对商州的探索,到20世纪90年代对西安的书写,再到21世纪的《秦腔》,贾平凹将笔调伸向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表现。
2.2公共情绪的共鸣
文学作品因能引起公众情感的共鸣而成为经典。首先,张贤亮与贾平凹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私人书写体现人文关怀。张贤亮在《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中对知识分子所受的性压抑、精神压抑做了集中表现,精准击中人内心隐秘的世界,激发了情绪的共鸣。贾平凹的作品通过空间化的精神寻根表现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
其次,贾平凹与张贤亮实现了对当时大众精神的慰藉。20世纪90年代,文学和社会活动呈现生动、活跃、无主调的时代特征,个人化的私人领域表现和日常琐事的原生态叙事成为文学的主要表现内容。贾平凹将关注点伸向个人隐秘的心灵世界,关注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细节和心理变化。张贤亮以实践型作家的身份在宁夏大地上进行立体创作,开发宁夏的历史人文资源,表现了开拓进取、吃苦耐劳、兼收并蓄的西北文化精神。两人多次共同参加文化活动,以资深作家的身份助力地方文化的传播和精神文明建设。
三、结语
张贤亮与贾平凹的交往是基于个人感性审美经验的主体间交往活动在生活世界内不断生成的过程。其交往意义对体察时代情绪与人心具有重要作用。另外,两人不是简单地讲述自身思考的结果,而是在对话交往中互相“呼应”。两人的交往不仅有助于弥合主体之间的隔阂,实现审美经验的对话,也对确立当代文学和文化合理性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深.他也是黄河的子孙(作家专访)——张贤亮在西安[J].延河,1984(4).
[2] 张贤亮.未死已知万事空[J].幸福(悦读),2013(5).
[3] 剑指仁川.著名作家张贤亮走了[N].西安日报,2014-09-28.
[4] 王辙. 一部奇书的命运 贾平凹《废都》沉浮[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1.
[5] 王保明,段捷智.《西北电业职工文学作品选集》座谈会在西安举行[N].西北电力报,2009-02-19.
[6] 彭诚.《中国治水史诗》首发式暨研讨会召开[N].检察日报,2010-07-09.
[7] 夏明勤.作家张贤亮辞世留下一座影视城[N].三秦都市报,2014-09-28.
[8] 斯达尔.斯达尔夫人论文学[M].徐继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9] 李星.孙见喜.贾平凹评传[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10] 郜元宝,张冉冉.贾平凹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11] 贾平凹.浮躁[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12] 张贤亮.张贤亮散文 繁华的荒凉[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
[13] 张贤亮.心安即福地[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
[14] 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15] 张贤亮.肖尔布拉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16] 陈一军.西北文化与张贤亮小说[D].兰州:兰州大学,2007.
[17] 吴兴明,张一骢.交往论视野:一条文学研究的新路径[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
[18] 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9] 张贤亮.我的倾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特约编辑 刘梦瑶)
作者简介:李鑫,宁夏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