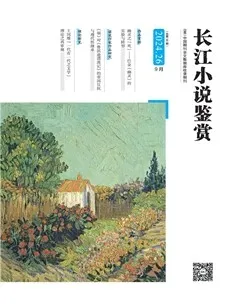后殖民叙事:《福》对《鲁滨逊漂流记》的帝国反抗与现代性继承
[摘 要] 库切擅于运用后现代文本互涉的技巧影射西方经典作品来表达后殖民时代的问题。他在小说《福》中,尝试运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对《鲁滨逊漂流记》的帝国形象进行了重写,以探讨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政治中暗藏的暴力,进而思考弱势的边缘群体如何运用抵制话语来维护其文化属性。
[关键词] 《福》 《鲁滨逊漂流记》 后殖民叙事
库切1986年出版的小说《福》是对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笛福的经典作品《鲁滨逊漂流记》的再度创作,库切借鉴了笛福的写作风格,以一种特殊的手法再现了笛福小说中的重要元素。库切的作品与原作相比有较大的不同,《福》虽然脱离了南非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但表现的仍然是库切一直关注的问题。
《鲁滨逊漂流记》出版之后,鲁滨逊这一形象作为经济个人主义的神话变得十分流行。而库切的《福》则在人物形象的建构、无处不在的失语表征及其背后的帝国建构三个方面对鲁滨逊的个人经济主义神话做出了质疑与反叛。
一、人物形象的模糊
对比两部著作及时代背景,《福》的人物形象更具有模糊与不确定性:《鲁滨逊漂流记》中,不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其身份、来历、目的都较为清晰,小说以鲁滨逊·克鲁索的自述为主线将各个人物串联起来,并在第一人称的讲述中构建出了一个物产丰富但人迹罕至的荒岛样貌。
在长达二十八年的荒岛建设中,鲁滨逊或自言自语,或日记记载,或符号记录,或内心独白,以多种方式不断强化对自我文明的构建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自然时序被量化在符号中,也在不断加强他对自己所属文明的热爱,即便有偶然的错序发生,《圣经》也能给予他心理上的宽慰。因此,文明与宗教帮助鲁滨逊在流落荒岛的时间里不忘其记忆中的欧洲,他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也驱使他“奋斗”不止。
除了自我身份认同,他者对鲁滨逊身份的构建进一步推动了鲁滨逊欧洲中心主义者这一身份的形成:不明脚印反衬欧洲文明的先进,制裁反叛者显现欧洲文明的人道,鲁滨逊一步步确立起对所属文明的坚定信仰。此外,星期五远离故土、融入城市的结局更让鲁滨逊认为文化殖民是具有可行性的,他将文化殖民付诸实践,至此,其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彻底完成,鲁滨逊在荒岛上构建了一套严谨的文化殖民体系。
与此不同的是,《福》中的人物都较为含混模糊,他们既不知来历,也不知归路。贯穿全文的书写行动源于船长一时兴起的建议,寻找女儿的终极目标也在叙述中逐渐边缘化。寻找女儿的行动进展缓慢,随后便被承担部分叙述的苏珊抛到脑后。其他人物如星期五、作家福、苏珊的女儿等更具模糊性,作者以此实现对原世界的重构。
《福》中的苏珊为了寻找女儿而出海,不料意外流落荒岛,遇见克鲁索,然而这里的克鲁索与《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史鲁索不同,他没有明确的进取目标,没有确定自己身份的日记簿甚至没有重返文明世界的想法,他对于荒岛的改造只为自己存活下去,对星期五也并无教化之意,他们如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互不打扰,克鲁索永远保持一副沉思的样子,让人难以理解他在想什么。
结合小说的时代背景,《福》中的克鲁索孤独、空虚、无聊,生活状态如死水一般,再没有当时鲁滨逊的活力,这是工业文明下个人的普遍精神特征,这种特征在18世纪的鲁滨逊身上已初见端倪:“一个内在的声音一直在暗中告诫我们,个人主义所促进的人的分离是痛苦的,最终将导致一种冷漠无情的动物性的生活和精神错乱;而笛福却充满信心地回答说那只是每个人潜力最充分的说明。”[1]鲁滨逊见到陌生脚印和大船的恐惧与野心到了克鲁索的时代则表现为面对汪洋大海的无情无欲、面对苏珊的懒散随意以及和星期五的互不干涉。至此,他从帝国形象的代言人变成了一个庸俗懒散,不思进取却具有强烈孤独感的现代个体,最终没有回到所属文明的土地。可以看出,“苏珊”笔下的克鲁索从思想、言语再到行动都是高度模糊的,直至死亡也不过是“夜里我听见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2],而后克鲁索被海葬。这种现代个体的空间感与内倾性也预示着帝国统治的逐渐没落。
克鲁索死后,叙述主体苏珊与星期五来到英国,想让作家福把她的经历写成小说,然而在经过一番争执后,苏珊完全消失,最终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写成,他塑造出一个虚拟的鲁滨逊。可以看出,性别和阶级双方面的博弈结果使福能够进一步通过写作展现其话语权。此外,作者还把焦点放到了全程游离于主干情节之外的星期五身上。星期五无法说话,因而其行为的解释权归于苏珊,但他本身的行动力又具有强烈的存在感和叙述性,从而形成种族和文化维度的话语纠纷。可以说,《福》正是借用主体形象的模糊性完成对多维度话语权的解构,以实现对《鲁滨逊漂流记》的重写。
这一系列解构主要由叙述的不确定性完成。小说以第一人称限知视角为主,个人化的叙述本就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库切在写作中却不追求“真实书写”,反而描写了大量关于克鲁索的虚构情节,且对苏珊流落荒岛之前的经历进行了细致描写,因此,《福》相比《鲁滨逊漂流记》便天然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真实性,从而构成了元文本的虚假特征。另外,第一人称叙述者苏珊的描述也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她是荒岛中唯一有叙述权的人,她以克鲁索的妻子自称,获取了其在荒岛上的合法地位,能对沉默的星期五的行为进行阐释,都体现了苏珊对掌握话语权的执着和其话语叙述的多重性,从而“消解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用语言和叙述所建构的历史真实感,揭露了历史写作中的权力结构”[3]。
二、失语的时代表征
对比两部小说会发现,不论是《鲁滨逊漂流记》还是《福》,星期五都具有失语化的特征,而二者失语的不同表征则反映出不同背景下现代性的不同呈现方式。
《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在荒岛生活了二十五年后才遇见并救下了星期五,对他进行了全面的文化渗透和影响,正如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言:“文化在帝国构建中扮演了一种非常重要、真正不可或缺的角色。”[4]鲁滨逊对星期五的文化渗透是其构筑文化帝国大厦的重要手段,渗透的过程也是星期五隐性失语化的过程。《鲁滨逊漂流记》对星期五的过去一概不提,他在对“先进”文化的学习中也没有表露出一丝自身民族的文化特征。名字是文明的产物,在荒岛上,言语称呼和住宿环境充满着等级性,星期五的生活习惯也逐渐向“文明”靠拢,这些都展现出星期五自我本位的缺席与文化的失语。在宗教方面,鲁滨逊以彻底否定贝纳默基“我对星期五大做工作,戳穿这种鬼把戏”[2]来实现对星期五的“再造”,最终星期五“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而他那样的虔诚,是我一生中难见到的”[2]。
因此,鲁滨逊对星期五的原有文化是漠视的,星期五学习的新语言和形成的新生活习惯以及对基督教的皈依都显示出其失语化的特征。此种失语教化的结果与18世纪欧洲的时代背景有密切联系:宗教改革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人更加自由,私有财产和经济个人主义的观念随之兴起,由此而来的经济扩张和文化中心主义思想遍及欧洲,奋斗精神渗透到欧洲人殖民行为的各个方面,即“当英国人通过他们的帝国改变别人的同时,帝国也改变着英国人,这形成了英国人对他们民族特征的看法,即他们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帝国的中心”[5]。《鲁宾逊漂流记》中,欧洲以外的“边缘”民族只能被迫失语。
相反,《福》中的星期五则是以显性失语的方式表达对失语的反抗,无法说话的客观现实不能阻碍其主体性的发展。这种对文化霸权和文明中心主义的反抗与消解让星期五的沉默在不可靠叙事中反而大大增加了其可靠性,从而成为压倒一切的叙述力量。这也是苏珊想要一直探寻的精神实质——沉默以一种无处不在的对抗显示着其内在的权威性。
与星期五有力的沉默对应的是苏珊对福消极的沉默,这一沉默对照组的出现为星期五的行为“言说”提供了强大的吸引力和探究性。发生在苏珊与星期五之间无休止的怀疑与探寻让星期五行为的说服力不断提升。在南非社会里,这种苦难和身体的权威性的不可否认不是出自逻辑的原因,也不是出自道德的原因,而是出自政治的和权力的原因,不是一个人赋予遭受苦难的身体以权威,而是遭受苦难的身体本身就有这种权威,换句话说,它的力量是不可否认的[6][7]。因此小说结尾处,作者才会用一般现在时写他的行为是“无言的溪流”[8]。
《鲁宾逊漂流记》和《福》中的两个星期五在无言与有言中形成了对比。18世纪的星期五的无言并非无法讲话,而是中心文明对其他文明的暴力“拔舌”,而后,中心文明向其他文明植入一套新的价值体系,从而实现帝国文明的一体化与“包容性”。话语在有形之声中遭到无形腐蚀,促使不同文明共同步入现代文明。
20世纪的星期五的无言则彰显了沉默的作用,“边缘”文明学会了反思和拒绝。《福》中的星期五的举动如撒花、吹笛、跳舞,因其神秘性在苏珊的讲述中备受关注,他在无法言说的话语边缘反而掌握了话语权,但库切表示:尽管如此,话语内容终以“无舌”消弭,即20世纪的现代环境给予了其他文明一定的关注度,但这种关注度并非实质性的话语权力,如星期五的沉默那样,读者可知其强烈的叙述权威和对中心文明的反抗与拒绝,但其终在沉默中被模糊了诉求。
然而,《福》中,星期五的话语权威也仅在苏珊的话语体系中占有一定地位,不论是克鲁索还是小说家福,他们都没有过多关注星期五的沉默。可以说,在女性的叙述里,身为黑色人种的星期五才有显现自身权威的可能性,但此种“权力”又在星期五无舌的生理条件下展现出空白,揭示出“代表着失去舌头的这些人利益的历史空白该由谁来填充呢?”[9]的历史含义。
因此,即使是在20世纪的现代语境中,性别与种族的言说权力依然处于“被填充”而非“能发声”的阶段,《福》中,叙述者苏珊只能拆穿小说家福的强大话语权的虚假性却无法证实自己发言权的真实性,从而在有形的失语中迈向多重叙述的无形失语。
三、帝国构建的现代化
《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在离开荒岛的八年后再一次回到荒岛,并建立起自己的帝国,而代理人摧毁了部落,进行了开化教育,体现出鲁滨逊对暴力的默许,“岛上完成了欧洲中心主义者的身份蜕变,而后拓展帝国的物理空间”[10]。
而《福》中,库切在对帝国主义、文化中心进行消解的同时也构筑出容纳不同个体的现代帝国。小说整体呈现出一种内倾化、沉默化和自语式的特点,不论人物还是环境都具有空间封闭性。克鲁索将他人排斥在外,“站在悬崖上远眺,其实是在凝望海与天的交界处”[7],他在荒岛上既不想建造帝国,也不愿回归文明,他认为:“并非每一个漂流到孤岛的人,内心都会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7]他在荒岛中构筑起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帝国,最终克鲁索尸沉大海的结局也象征着他对现代经济“启蒙”的反叛与逃离。克鲁索的形象不再是欧洲殖民者集体形象的代表,而是代表了自由的个体,即“社会生活中移去了人为的共同权力,但保留了所有人在这样的权力之下的共同生活的经验……身上都还带有对这部人造机器幽灵般的记忆”[11]。
除克鲁索外,《福》的女主人公苏珊和星期五的交流互动也反映着现代帝国的构建方式。星期五沉浸在自我文化的复现与强化中,他对欧洲文明的反抗和消解天然地具有沉默性,他的动作体现出的神秘文化便成为他个人主义的外溢表征,因此,星期五的主体性就具有了双重属性——既非传统文化的真正继承者,也非异质文明入侵的确定占有者。而苏珊对星期五的影响便成为现代帝国建构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从对撒花行为的疑问到试图理解并参与其中,苏珊明白“他并不是因为迟钝才将自己封闭起来,而是拒绝与我有任何交流”[7],之后的共舞使苏珊逐渐懂得“星期五在英国跳舞的原因”[7]。苏珊认为,“他眼神中似乎闪烁着理解的意思”[7]。“没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一致感或共同的标准,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要求在感情上把握和理解的强烈的愿望,而这种愿望的满足只能仰仗于人际关系的隐秘的揭示”[1],在苏珊模糊地对星期五进行探究的同时,也在叙述话语中建构着星期五个体现代化的“非个体性”。
小说《福》中,无论是克鲁索、星期五还是作家福都或多或少地被苏珊主观地评价过,这是一种具有女性色彩的后殖民主义书写,但小说中苏珊失控的情绪表现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话语权的让渡和妥协,即“叙事,或者阻止他人叙事的形成,对文化和帝国主义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12]。同时,权力让渡也让苏珊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自己的性别:与克鲁索的共寝让她得到了作为克鲁索夫人的权力;以克鲁索夫人作为自己的名字又赋予了她诱惑别人的资本;和福先生亲密的关系让苏珊享有了获知小说内容的权力;小说内容的虚假性写作又促成了日记这一前文本的出现。
如果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荒岛帝国是现代化进程中外向性的构建,那么《福》更多的是人物形象在模糊中的内向性的构建。二者在内外不同的帝国构建中反射出强烈的时代色彩和现代意义。
参考文献
[1] 瓦特.小说的兴起[M].刘建刚,闫建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2] 笛福.鲁滨逊漂流记[M].徐霞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3] 黄晖.《福》:重构帝国文学经典[J].外国文学研究,2010(3).
[4] 泰勒.原始文化[M].蔡江浓,编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5] 马歇尔.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M].樊新志,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6] 岳峰,孔建平.经典殖民叙事的时空重构——《鲁滨逊漂流记》与《福》对读札记[J].中国比较文学,2018(1).
[7] Coetzee J M. 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8] 库切.福[M].王敬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9] Morgan P E.Foe’s Defoe and La Jeune Nee:Establishing a Metaphorical Referent for the Elided Female Voice[M].Philadelphia:Critique,1994.
[10] 许存勇.《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后殖民主义因素[D].合肥:安徽大学,2012.
[11] 李猛.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12]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责任编辑 陆晓璇)
作者简介:高彬倩,上海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