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乡土志中的国家认同与爱国主义表达
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认为,传统认同的危机是导致现代认同产生的必要条件①。自鸦片战争以后,“天朝上国”的观念受到强烈冲击,清政府被迫开始认识到自身的落后性与西方国家的先进性,中国传统的“天下观”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国家观”;尤其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基于皇权正统性和道统合法性为基础的国家认同体系全面崩溃。要想维护政权稳定,使国家能够正常运转,就必须建构新的国家认同体系。
有学者认为:“从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来看,历史与地理教育一直是建构民族国家共同体、启蒙和培育民众对于民族国家认同感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这亦是史、地二学科在近代学科建设中备受重视的重要原因。”②教育改革是清末改革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其中乡土教育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乡土教育的教材之一——乡土志,作为历史、地理的结合体,也备受重视,在新的国家认同体系构建中起到了几乎无可替代的作用。
四川有悠久的修志传统,历史上名家辈出、名志叠见。在清末民国乡土志编纂的浪潮中,四川也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乡土志,现存达76部之多,占全国现存乡土志总数的12%左右。这些乡土志对于培养近代四川人的国家认同观念与爱国主义情怀,起到了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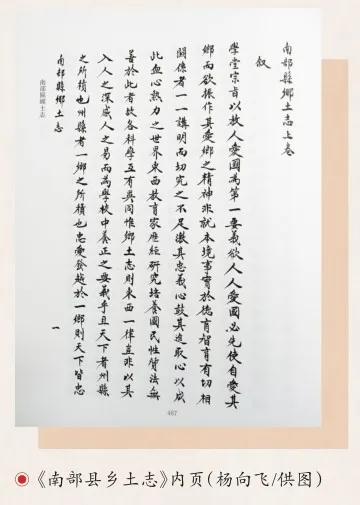
一、乡土教育:重建国家认同的尝试
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教育起源于欧洲,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模仿欧洲的乡土教育政策,并取得了极大成功。在甲午海战失败后,清政府也开始向日本学习,其中乡土教育就几乎完全照搬了日本的做法。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管学大臣张百熙赴日本考察学务后,初步确定编书大纲。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编书局监督黄绍箕受张百熙之命,撰写《乡土志例目》。学部采纳了黄绍箕的方案,并通饬各省遵照《例目》编纂乡土志。自此,全国各地掀起了编纂乡土志以“务使人人由爱乡以知爱国”的高潮,各地无不以编纂乡土志为急务,甚至被提升到国策的高度,从中央到基层都十分重视,是此时清政府为加强基础教育、培育儿童爱乡爱国思想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
有学者认为,“清政府不仅希望学堂承载传播一般科学文化知识的使命,而且希望其成为理想的官方政治文化传播场所,负担起向学生灌输官方意识形态的职能。”①因此作为官方修订、审核的乡土志,理所当然也承担有这样的职能。现代人常常诟病于乡土志的简略,但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探讨为什么乡土志要简略。“存史、育人、资政”是地方志三大功能,“存史”是其最直观的作用,另外两者可以说都是在“存史”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功能,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而乡土志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在民族生死存亡、国家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产生的,其阅读对象又是国家的未来——儿童,其编纂不能像传统方志那样“三管齐下”,必须突出主线,这条主线就是“育人”,主要指的是“爱国”这个主题,而志书其他两方面的功能都被人为地弱化了。这是乡土志与中国传统志书最大的区别。
乡土志编纂的初衷,就是对小学生讲授本地各方面的知识,并借以进行爱国教育。乡土志编纂者认为,“学堂宗旨,以教人爱国为第一要义。欲人人爱国,必先使自爱其乡;而欲振作其爱乡之精神,非就本境事实于德育、智育有切相关系者,一一讲明,而切究之不足,激其忠义心,鼓其进取心,以成此血心热力之世界。”②清末乡土志的编纂紧紧抓住这条主线,其所记、所载无不体现爱国、爱乡思想。清宣统《大邑县新修乡土志》将爱乡与爱国的关系阐述得尤为详细:
将欲使民爱国,必先使其爱种;欲将使其爱种,必先使其爱乡。乡者,种之至亲,而国之所积者也。今就本乡之事实为童蒙之讲授,以引起其爱种爱国之心,则一乡之前言往行,可以动其观感效法焉;一乡之礼乐风教,可以启其政治思想焉。即一乡之一山一水、一木一石,亦足以开通其智识,发舒其精神焉。知一乡以知一国,知一国以知天下,而学术乃日隆矣;知爱乡而知爱种,知爱种而知爱国,而国势乃日强矣。……而今而后,吾民将起而为日新之民,吾国亦将起而为日新之国矣。然则乡土志之修,其功岂浅鲜哉?③
为更好地反映地方实际,培育儿童的爱乡爱国情怀,乡土志编纂者往往对本地优越的自然环境大加赞叹。如清宣统《温江县乡土志》:“吾邑建置,历千二百年,其地土脉冲融,江水温润,无粗恶险怪之性意,必有仁义中正伟大不世出之贤笃生其间。”④类似的表述在其他乡土志中不一而足,而且大多开宗明义放在卷首,并在正文中不断强化,使学生牢固树立爱乡以致爱国之情,加深其国家认同感。
二、国家与世界:危机中的觉醒意识
清末的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之前的闭关锁国政策被完全打破,中国开始真正融入世界发展洪流之中。面对西方的强大,有识之士对自身的困境进行了深刻反省,表现在思想领域即是危机意识、自强意识与改革意识的觉醒,这些在四川乡土志中都有所体现。
一是反映社会危机。《金堂县乡土志》中对于我国在国际商业中的弱势地位感到担忧:“中国自长江开埠,二十七口岸通商以来,银币之漏出外洋者,如水之趋壑,每岁动以亿万计,谈之者无不咋舌色骇,今欲闭关绝客,虽秦皇汉武生于世,亦势有所不能。”⑤《安岳县乡土志》对我国传统工商业受到西方冲击的情况也进行了总结:“海禁大开,重门洞辟,工固拙矣,商亦败绩。彼持筹而来,我莫算以往。吾恶知赢绌之分,竟相悬于霄壤。”⑥
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在乡土志的编纂过程中,处处可见编者对国家富强的建议与期待,如《新津县乡土志》表示:“近年新政日颁,东游之士杨君泽彰归来,家颇殷实,自制织布机器,仿照外洋,将来逐渐推广,新邑之布素称精良,行销外处,由此必更加增。工业日盛,商业自无不发达之理。”①清光绪《金堂县乡土志》中记载了洋绸、洋缎等商品的销售情况,并进行总结:“惟有推广商务,以与彼族互市,尚可挽回利权,不可谓非转贫为富,转弱为强之机也。”②反映了外国势力在金堂县的渗透,唤起人们实业救国、抵御外权、维护国家利益的意识。乡土志着重强调社会危机、民族危机,对于培育、树立儿童的爱国情怀与觉醒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传播西学。传播西学是乡土志的一大功能。如《灌县乡土志》说:“遇有新学发明者,尤阐扬不遗余力。”③当时有人将西方强大而中国贫弱的原因全部归功于西方的发明创造,《蒲江县乡土志》说:“西人有汽学、电学,则援亢仓关尹以先之;西人有光学、重学、化学、机器学,则翘墨子以抑之,而率无一人为能如西人之求新理、辟新机者(如喀马特造气球、阿勒德造飞车、爱迪生创留声机、西里司创无线电报诸类),中国所以愈贫弱,西人所以愈富强也。”④
在四川乡土志关于西学的表述中,《中江县乡土志》最具代表性:“西人游历之所及,凡山川道里之可以凿矿而兴水利,安轨而立埠头者,无不绘图列说,详加记载,甚至飞潜、动植、瓦砾、泥沙亦必考究其形模、性质,以备分合变化之用。而又博加甄采,以及人事之进化、风俗之改良、物产之兴盛衰败,间岁以修,目为最新,历史俾世之览者,得以恍然;于优胜劣败之故,故能握五大洲之利权,而为最富最强之国。”编者游夔一的这段话对西方之所以强大作出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并说明中国可以成为富强之国的环境、物质基础,号召国人奋起直追,积极参与世界竞争,通过工战、商战,最终成为富强之国。应该说游夔一的看法非常具有代表性和前瞻性,后来一百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融入世界,最终实现了“英华富于一乡,名誉胜于一国,而影响亦遂及于天下”⑤的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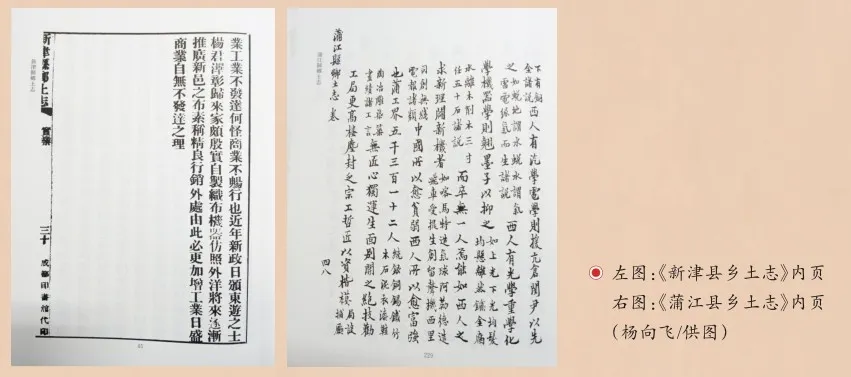
三是宣传预备立宪。“预备立宪”是清末的一项重要政治改革,是从根本制度方面重建新的国家认同体系的举措。宪政(Constitutional Politics)指的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在皇权至上的中国,这注定是一场失败的政治改革①。但由于其自身具有现代性和进步性,在民间也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其影响在四川乡土志中也有所体现。如《郫县乡土志》说:“朝廷预备立宪,预备之道,从地方自治入手。郫邑十六万人,剖郫邑为十六万分,人人皆为地方一分子,则凡郫邑之绅界、学界、农工商界中人,又乌可放弃责任,不图进步,以速国家立宪之期耶?吾愿读斯志者,即以斯志为地方自治之参考书可也。”其中包含了编纂者对清末新政的期待和憧憬,并呼吁人人担当,“以速国家立宪之期”②。另在《大邑县乡土志》中,最有特点的是书后附录《大邑新政》部分,详细记载了清末新政在大邑县的贯彻落实情况,如高等小学堂校制、规制、地点以及警察局、劝工局、团练等方面的情况,是研究清末新政对基层行政单位影响的重要资料。
三、启示:今天的地方志如何弘扬爱国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地方志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应当要承担起弘扬爱国主义的责任。今天距清末已经过去一百余年,我们国家不再面临当时“瓜分豆剖,祸在燃眉”的局面,但乡土志的编纂思路和方法,对于今天的地方志工作依然有参考价值。
一是大力宣扬爱乡思想。爱乡与爱国是密不可分的,爱乡是爱国的基础,而爱国则是爱乡的扩大。对乡土的热爱,是地方志诞生的前提条件之一。如开地方志先河的《华阳国志》,作者常璩就是怀着对故乡深沉的热爱之情,用志书来展现巴蜀大地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以颉颃中原,压倒扬越,以反抗江左士流之诮藐”,从而发挥志书“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③的重要作用。从古至今的修志者莫不如此。而反过来,作者的这种爱乡之情,也可以通过地方志来感染、教化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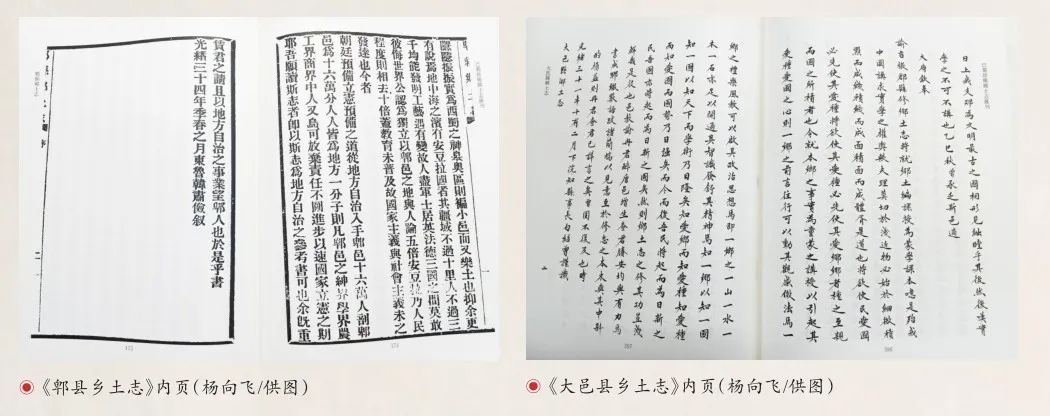
地方志虽然秉持“述而不论”的基本原则,但并不影响编纂者将爱乡情怀贯穿于书中,如在志书中必须记载的山川名胜、资源禀赋、文化发展、科技进步等,都能展现某一地区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盛,体现某一历史时段的各项成就,以此来增强读者对于乡土的热爱之情。正如著名方志学家董一博先生所说:“志书中的山川胜迹、丰饶资源、淳厚质朴的风尚、灿烂文化、科技发明、专家学者、先进人物、人民领袖、革命志士以及奸宄邪恶的坏人等等,都足以启顽立懦,提高人民的思想情操、精神文明素质,振兴奋起,增强爱家乡、爱祖国的观念,进行思想道德品质教育。”①目前,全国第三轮修志工作即将开始,第三轮志书时限范围恰好涵盖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因此,在这一轮修志中,要突出十八大前后区域内各项事业的“新旧对比”,充分反映新时代的崭新风貌,着重突出新时代的伟大成就,以此来激发群众对于家乡乃至国家高速发展的深刻认识,加深群众对新时代的认同感、归属感。
二是利用地方志进行乡土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虽没有再进行大规模乡土志编纂,但乡土教育在很长时期内不仅并未中断,反而得到不断加强。早在1958年,教育部下发的《关于编写中小学、师范学校乡土教材的通知》,就指出:“教学乡土教材,可以补充全国统一教材的不足,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充实、生动具体,能更密切地结合地方实际情况,能更好地适应我国地区辽阔、情况复杂的特点。”之后,在全国掀起了编纂乡土教材的热潮。改革开放后,乡土教育的地位更加突出,全国各地都结合当地特色,编纂了大量乡土教材。而进入新世纪后,随着课程改革的持续深入,“乡土教材被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取代”,乡土教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日渐凋零”②。
乡土教育,主要包括乡土历史、乡土地理两大类,而这两个方面也是地方志记载的主要内容,因此可以说,地方志在乡土教育方面具备天然的优势。1994年全国地方志工作座谈会明确指出:“新志书和各种地情资料及地情研究成果,可以转化为向各类干部和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③乡土教材就是地方志书转化的一个重要方向。一些地区的地方志机构已在进行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如上海、吉林、新疆等地。但总体上看,地方志机构在乡土教育中的缺位还比较明显。
目前的地方志,普遍部头太大,不适合作为教材,各级地方志机构有必要继承清末乡土志的编纂传统,对现有志书进行深入精简、高度浓缩和二次创作,编纂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乡土志”。同时,应针对不同受众的认知水平,如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甚至机关干部等,分别编纂不同程度的乡土志书,并与中小学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党校等机构合作,开设乡土教育课程,推动志书进校园、进课堂,普及乡土知识。
四、结语
乡土志的诞生和大规模编纂,正值清末西学东渐的持续发展和清朝新政的全面实施时期,这些都在乡土志中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作为小学教材,乡土志真正承担起了一代人的启蒙作用。郭沫若曾回忆道:“监学易曙辉先生,他教了我们一些乡土志。这是比较有趣味的一门功课……这虽然是一种变格的教法,但于我们,特别是我自己,却有很大的影响。”④郭沫若所说的“变格”,其实就是近代西方教育观念对传统中国教育方式的冲击。乡土志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教育理念,向学生普及了西方新学,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们爱乡爱国的观念,这对于塑造国民意识、增强国家认同和强化民族团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的时期,地方志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爱乡教育和爱国教育方面,应当承担起更多责任。各级地方志机构要在继承前人优秀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创新,为乡土教育贡献地方志力量。
(作者单位: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①(美)里亚·格林菲尔德著、王春华等译:《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16页。
②何思源:《地理书写与国家认同:清末地理教科书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安徽史学》,2016年第2期。
①白文刚:《清末学堂教育中的意识形态控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期。
②(清)王道履编:《南部县乡土志·序》,光绪三十二年抄本。
③(清)白邵曾修、査体仁纂:《大邑县新修乡土志》,白邵曾序,清光绪三十一年抄本。
④(清)曾学传编:《温江县乡土志·地理》,清宣统元年刻本。
⑤(清)刘肇烈纂、陈佳树、刘容光分纂:《金堂县乡土志·凡例》,清末抄本。
⑥(清)高铭箴修、张光溥等纂:《安岳县乡土志·商务》,清光绪稿本。
①(清)禄勋编:《新津县乡土志·实业》,清末抄本。
②(清)刘肇烈纂:《金堂县乡土志·凡例》,清末抄本。
③(清)钟文虎修:《灌县乡土志·序》,清光绪三十三年刻本。
④(清)佚名:《蒲江县乡土志·实业》,清光绪三十四年抄本。
⑤(清)游夔一编:《中江县乡土志·序》,清末抄本。
①樊锐、陈纯柱:《我国晚清预备立宪的困境研究》,《重庆行政》(公共论坛),2011年第5期。
②(清)黄德润修、姜士夸纂:《郫县乡土志·序》,清光绪三十四年铅印本。
③(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12《序志》。
①董一博:《论方志的五大作用》,《董一博方志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②石鸥、周美云:《试论乡土教材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意义与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③《全国地方志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国地方志》,1994年第4期。
④郭沫若:《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