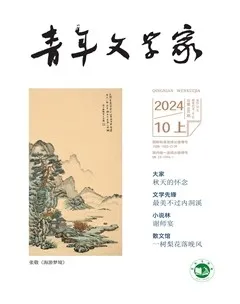“书画互生,溢为行草”

书画大家黄宾虹(1865—1955),不仅在中国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书法方面也极有建树。我国自古就有“书画同源”之说,所谓“同源”者,往往互生互发,相得益彰。“吾尝以山水作字,而以字作画。”黄宾虹的款识书法,有其画之精神意韵,画之笔墨技巧反过来对书法产生作用,因此说“字中有画”;“以山水作字”可以看作黄宾虹引画入书的典范。黄宾虹一生大部分时间用来思考绘画,黄宾虹书法的成熟,除了他对绘画观念的重视外,黄宾虹关于书法上的技巧与经验,都是在绘画中发展、积累而成熟的。绘画笔性不可避免地对书法产生影响,其中的影响又体现在笔法、墨法、体势的变异上。
一、黄宾虹“书画同源”的艺术观与学书渊源
(一)黄宾虹“书画同源”的艺术观
书画互生的前提是“书画同源”,因此,研究“书画互生”的前提之一即是对书画同源问题的诠释。占主流地位的文字学起源观点,并不认为文字是从图画跨越过来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初造书契……”许慎认为文字并非源于图画,而是源于八卦结绳一类的抽象符号。
但是从现存的甲骨、青铜、钟鼎彝器以及彩陶等上古器物的纹饰中,我们确实发现它们具有绘画因素的同时,与文字也有某种相似的特征。基于此,唐代张彦远首次提出书画起源相同的理论,即“书画同源”“书画同体”“同源而异流”之说。绘画最初被排斥于六艺之外,到了唐代,张彦远用文字与绘画的“象形”这一相同之处来提高绘画的地位,他在《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说:“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绘画与文字分别承担了“形”与“意”。将绘画与文字并列起来,强调绘画的重要性。这时的“书”指文字,“画”指绘画。与后世讲的书法、绘画在概念上并不完全一致。
自魏晋始,书画同源命题迈入了第二阶段,此时的书画同源已经演变到了“书画用笔同法”。张彦远在其《论顾陆张吴用笔》中解释道:“昔张芝学崔瑗、杜度草书之法……一笔而成……世上谓之一笔书。其后陆探微亦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张彦远通过“用笔”将“书”与“画”两种不同功用的艺术形式联系起来。使得后世单独讨论“书”与“画”的用笔用墨成为可能。
到了宋代,“人能知善书执笔之法……善书必能画,善画必能书,书画其实一事尔”(赵希鹄《洞天清录·古画辨》)。此时已经发展为书画兼善,“书画同源”在此时在理论上已经从单一的“书家”或者“画家”的要求,发展为“书画家”了。这种身份的双重认证对后世以书入画或以画入书提供了全面的可能性。
1934年,黄宾虹与临川书家陈鸿图先生于沪上论书法,陈鸿图在当时提出了在元明之际书法中有画意这一现象。清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则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字画本自同工……以书法透入于画,而画无不妙;以画法参入于书,而书无不神。”在周星莲的论述中,书画同源得到了“以书入画”和“以画入书”双向的、辩证的注释而更加丰满。黄宾虹的“书画同源”艺术观正是对明清以来这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1940年,黄宾虹时年75岁,同年的一月,黄宾虹在《画谈》这篇文章中谈到一个观点:“练习诸法,成一笔画。一笔如此,千万笔无不如此。”黄宾虹把用笔、笔法作为书画相通的桥梁,他打破了书法与绘画之间的壁垒。对此,他有一段生动的叙述:“吾尝以山水作字,而以字作画……我以此知字之布白,当有顾盼,当有趋向,当寓齐于不齐,寓不齐于齐。”在这段论述中,黄宾虹充分认识到绘画的笔墨、造型、趣味等可以丰富书法的形态特征,以对自然生命的感受和理解,明确提出了绘画对书法的美学和技法意义并观照汉字的空间构成以及书写过程。
(二)黄宾虹的学书渊源
黄宾虹在学书的历程中,着意于画家书法的临池参悟,在黄宾虹幼年时,就从倪逸甫处得“当如作字法,笔笔分明”的教诲,这使得他从小就有了关注书画内在联系的潜意识,黄宾虹自言“闻其议论,明昧参半,遵守其所指示,行之年余,不敢懈怠”(《黄宾虹文集·杂著编》)。这为黄宾虹日后的书画互参埋下了伏笔。“书画家”比之“书家”,多了一种身份,也多了一种视角,往往以画家视角审读书法;比起“画家”,他们还精通书法,往往会在书法中参以绘画的因素。例如,倪瓒的画荒疏孤介,却又有朗朗清气,在书法上,倪瓒隶意横出、结体疏朗的小楷书与其画风相得益彰,董其昌评其书法“从画悟书,因得清洒”。在黄宾虹的师法名单里不仅有赵孟頫、倪云林、徐渭、董其昌等书画俱佳的大家,还有如吴镇、姚绶、法若真以及其他明清人的作品,其中包括祝允明、文徵明、张瑞图、王铎、傅山、伊秉绶,也包括一些并不以书名世的人的作品,如詹景凤、罗文瑞、李流芳等。他常以书家眼光审视绘画,以画家眼光审视书法,在其《讲学集录》中引用了周星莲的观点:“可知夫字贵写,画亦贵写,以书法透入于画,则画无不妙;以画法参入于书,而书无不神……”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黄宾虹不仅在画中汲取书法的营养,在他的书法上,也同样从画中受益匪浅,款识书法自其诞生之初就与画密不可分,黄宾虹所书所画,相得益彰。黄宾虹书法的成熟,以及关于笔法、墨法、结字、章法等书法上的技巧与经验,都是在绘画中发展、积累而成熟的。
二、黄宾虹绘画笔性对款识书法的影响
(一)款识书法笔法的变异
黄宾虹的书法筑基于金石,黄宾虹的款识书法的发展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尊古习古的接受期,这一时期黄宾虹的笔法来源主要是魏碑和帖学的传统用笔方法,从书法的用笔上来看,早期用笔上受帖学影响更深,起多方折而少圆转。笔法相对单一,笔画内部的动作也不够丰富;在整体风貌上,介于唐楷和魏碑之间。对碑的理解仅停留在表面的模仿上。
黄宾虹成熟时期的笔墨,从金文中汲取的营养最多。可以说,对于线的理解,黄宾虹更看重“质”上的灵动和飘逸。这部分作品基本上结字还处于以褚楷为框架,参以温泉铭的体势变化,用笔上在之前帖学笔法的基础上加以对金石的理解。对于金石气的表现在黄宾虹的中期款识书法中,主要是通过在书写中加大提按的力度、留驻,长线条的波动等方式表现金石气,将六朝碑版、金石铭文中的残破斑驳引入了款识书法。虽容易表现斑驳的视觉效果,以顿挫、留驻、提按之法运笔,易得苍老但少文雅。一味苍辣,则容易因药生病。
黄宾虹晚年在借助绘画笔性的基础上,使他的款识书法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在用笔上,颤动、波动被简化为与他山水画笔触相似的“一波三折”;在通篇的运笔中,减少了表现金石气的通用方式—顿挫、提按,放弃了书法中复杂精妙的技巧,只关注书法中几个基本的问题,如力度、节奏等几个最基本的问题。综上所述,黄宾虹绘画笔性对他笔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笔法的精简和深化,使得用笔更加凝练,使得黄宾虹对金石笔法的认识突破了以往的桎梏。
(二)款识书法墨法的变异
在唐以前,对书法用墨的理解,大多是一种在实践中的经验性判断,对墨法的描述相当简练,浓而润是晋唐时期墨法的基本形态。在元代以前,墨法在书法中的地位是模糊的,尽管在宋代已经出现了对墨法追求的自觉倾向,但还是以笔法为主,对墨法的重要性做出正确判定的是明代的董其昌,其在《画禅室随笔》中讲道:“字之巧处,在用笔,尤在用墨。然非多见古人真迹,不足与语此窍也。”在要求用笔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对“用墨”技巧的把握。明清时期的墨法呈现多姿多彩的局面。对墨法的理解是在对前人墨法经验的关注和总结中不断走向自觉的。黄宾虹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对墨法有着独特的见解,绘画中墨法的应用,在“书画同源”观念的作用下,渐渐渗透在此后的书法创作中。黄宾虹从绘画的角度提出了“七墨法”,并在书法中实践。第一个提出书家不通墨法谓之“奴书”的观点,并且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古代书家“以画的墨法通于书法”的观点,“书家有笔法无墨法,谓之‘奴书’……古人善书者必善画,以画之墨法通于书法……真者用浓墨,下笔时必含水,含水乃润乃活……”(黄宾虹《黄宾虹谈艺录》)书法的节奏感从用笔上来讲是用笔的轻重、缓急、虚实、转折等的矛盾对立与统一,表现在笔画形态上则是平正、方圆、曲直的变化,在章法中单个字形的夸张、欹侧、字距的远近以及行与行之间的开合变化等因素的有机组合。其中又离不开墨的参与。在作者情感的贯穿下,墨法的组合不只是在单字内实现了墨色的对比,同时也打破了行与行间空白对比的单一性,扩充了书写的笔墨语言,这种对立又统一于气脉连贯的书写中,墨色也随性情流动,这种墨法的组合使书法犹如绘画般具有了画境。墨法在情感的贯穿下在章法中得到了有机组合,使得款识书法更具魅力。
(三)款识书法体势的变异
“书与画同出。画取形,书取象;画取多,书取少。”(郑樵《通志》卷三十一)书法以汉字为造型基础,变化的抽象笔画及笔画的组合方式,以对立统一的哲理、节奏来表达书家情志,但总离不开汉字的框架。明清时期,文人画在摆脱形的束缚后逐渐向着抽象的书法艺术靠拢。为此,在绘画中对形的突破向着书法的抽象意味转化,具体形象在文人笔下成了程式化的符号,如画竹时的“个”字、“介”字等。这种对摆脱自然物象束缚的理念,同时也影响到书法,书法通过文人画解散形体的启示,书法对汉字形体也有摆脱的倾向,特别是在行草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或简而再简,或繁而更繁,或墨色淋漓,或对字法笔画进行夸张来实现对汉字固有形体的解构,大大提高了书法的表现力。在黄宾虹的行书题款中,有时会不顾笔法与结字的要求夸张其中的横画,同时他还在结字时打破五体间的壁垒,篆隶楷行草,各有自己的单字结字准则。黄宾虹在结构的营造上一为造险,二为营造稚拙的结字,他在行草书中杂以篆隶,用篆书“草”的字法,杂以行草之中,不惜打破结字的固有规范,营造一种古朴浪漫的结字奇趣。以画家的奇思妙想巧设结字,使得书画融为一体。在黄宾虹的山水画题款中,通篇笔势流动,笔画间多有散脱处,其中书法与绘画的运笔节奏相似,笔画被打散,行书的结构最大限度地脱离汉字自身结构的束缚,究其原因正是受其绘画运笔习惯的影响。
三、黄宾虹绘画笔性的启示
中国艺术在表现手法上往往采取一种圆融贯通的表现手法,书画相通、书画同源与中国哲学中的美学追求相贯通,艺术家往往有意将二者拉近,使之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古来书画家往往虽然十分重视在绘画中汲取书法的营养,以书入画,却很少有人关注书法可以从绘画中学习什么的问题;发展至后期,更有一些书画家粗浅地解读“书画同源”的概念,将画法生搬硬套到书法中,坠入魔道。
黄宾虹的艺术实践,特别是他在绘画与书法艺术方面的探索和创新,不仅反映了他个人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现代变革的适应,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的自我更新和发展。黄宾虹擅长山水画,其画风融合了宋、元各家之长,又有所创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宾虹山水”。在书法方面,黄宾虹同样造诣深厚,他的书法既有古意又不乏现代气息,尤其是他的行草书,更是将绘画的笔墨语言和书法的节奏韵律完美结合,展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
黄宾虹认为的“用笔之法,书画既是同源,最高层当以金石文字为根据”是对书画同源“度”的限定,回答了书法可以向绘画学什么的问题。基于对书画同源独特的认识,从黄宾虹的款识书法探索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书法与绘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两者相互依赖,不可分割。另一方面,书法与绘画的结合需要时间上的锤炼。黄宾虹款识书法在“以画入书”的探索上为后人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