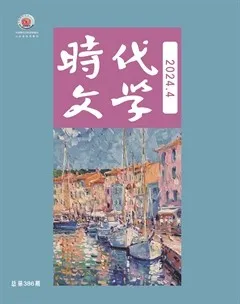大漠花开
1949年下半年,10万解放大军抖落一身硝烟,从解放大西北的战场向着新疆浩荡行进。下一场战役,是区别于以往任何战役的史诗般的屯垦戍边。一路飞沙走石,遮天蔽日,悠长的军号声,战马的嘶鸣声,武器撞击的叮当声,与匪兵的厮杀声,古丝绸之路上霎时生出一种悲壮与激昂。
历朝历代,不乏向万古沙漠宣战的强者。可每每风沙疯狂反扑,旱魃凶煞逼迫,他们又不得不曳兵弃甲,怆然而退,空留交河、楼兰等故城遗迹让后人凭吊。
从炮火硝烟中走来的解放军勇士,与陶峙岳将军率领的在疆10万起义兵一起,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着天山南北的荒漠宣战,对国境线重新布防,接下来是长期的坚守和捍卫。20余万大军胸挡着进逼的沙漠,背靠着祖国的围墙,坚挺地树起新中国第一代军垦人的钢铁形象。
有名谚道: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向前看戈壁滩,向后看鬼门关。
面对浩荡无垠的荒漠,勇士们放下背包,支起刀枪,开始了“冲刺”前的热身——搭草棚子,挖地窝子,吃野菜蘸盐水。夏天蚊子能吃人,冬天屋里能结冰。乌斯满等匪徒到处挑衅残害军人和老百姓,骑兵团还要进深山沙漠剿匪。战士们肩扛着使命,甩开臂膀,开始了永不复员的军垦生活。
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库尔勒、轮台一带有个“吾瓦”,在维吾尔语中意思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很久以前,美丽的孔雀河曾流经此地,地肥水丰草美,后来河流改道,这里变成焦渴荒芜的戈壁滩,当地百姓盼水盼得望眼欲穿。有个叫玛洛伽的美丽姑娘,为了给乡亲们找水,独自一人进入塔克拉玛干。一年,两年,十年过去,玛洛伽没有找到水源,却在干渴中倒下,再也没有回来。春天带着暖阳来到吾瓦,沿着玛洛伽的足迹开出一簇簇娇艳的野麻花。乡亲们用一首悲凉的歌谣来纪念这位勇敢善良的姑娘:“看见野麻花,想起玛洛伽,幸福城我不见啊,玛洛伽啊,不见你啊,只见野麻花……”
踩着10万解放军进疆的足迹,很快跟上来“八千湘女”“两万山东女兵”,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支边女青年。这些从战乱中走过来的姑娘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和满腔热血,用青春和汗水编织梦想,要当人民的“玛洛伽”。她们迎风沙而立,逼旱魃退让,跟男兵一起开荒造田,上山背石头,挖水渠,用坎土曼刨芨芨草、红柳根。那些千百年的老根深深扎进土地里,她们磨得双手都是血,常把坎土曼撅断,疼过哭过后,又擦干眼泪和血迹继续战斗。
她们把祖国大西北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当画布,画出粮棉遍野、瓜果飘香、绿树成荫、清水荡漾、鸡鸭满圈、牛羊满坡的巨幅画卷。她们给“戈壁茫茫浩无边,只见风雪不见天”的塞上播撒绿色,种下希望,让沉睡了千万年的这方厚土升腾起人间烟火,焕发出勃勃生机。可以这么说,没有这些女兵,就没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今天;没有这些女兵,就没有今日之新疆!
王秀兰是1947年走进山东军区渤海教导旅的。在解放大西北的战场上她是战地救护,为救伤员立过三等功,还把一个不满百日的儿子牺牲在了战场上。到天山以南的焉耆后,她同丈夫一起参与了地方新政权建设。她的丈夫胡敏是从延安到山东渤海区带兵的红军干部,先是在焉耆县公安局任职,后又调到轮台。王秀兰开始是焉耆公安局内勤,到轮台后在县委任秘书。她工作上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在家庭,挑起所有担子,努力做好丈夫的后盾。
不久,胡敏被安排到中央党校西安分校学习,王秀兰作为家属带着孩子一同前往。她的“厄运”也伴随而来。在搬家的路上,她的档案被丈夫的秘书不小心弄丢了。
丢了档案,王秀兰成了一个没有身份没有工作的人。没有工作,当然就没有工资。没有工资还在其次,没有了工作,对于向来积极上进的王秀兰来说,等于要了她的命。
在西安的两年里,王秀兰忙着家务,照顾三个孩子,生活倒也充实,回到新疆后,又先后生下三个女儿,依旧没有工作。在以后的30多年里,王秀兰依然如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提倡“勤俭持家”,许多女同志辞职回家带孩子,她就没有再提档案和工作的事,尽管她内心还是希望回到工作岗位上。
胡敏的弟弟一家从老家投奔来到新疆,吃住在他们家。王秀兰不久得了严重肾病,不得不把母亲从老家接来帮着照顾孩子。家里生活更困难了。但王秀兰始终铭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按时缴纳党费。有段时间,丈夫所在单位打算给王秀兰一点生活补贴,被她婉拒,她说自己没有为国家做事,补贴坚决不能要。
王秀兰对档案丢失、工作丢掉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她觉得这是剥夺了她为党工作的权利。她是抱定了吃苦奉献的思想进新疆的,谁承想时间不长,竟以“不工作”的方式奉献了自己。王秀兰确实做到了勤俭持家,她必须勤俭持家。全家11口人吃饭,靠丈夫每月200多元的工资。她粗粮细做,精打细算,非常俭朴。衣服是小孩穿大孩的,大孩的则都是大人的旧衣服改做的。她规定孩子们吃饭不能剩饭,不能掉米粒。她的儿子说,这个“铁规”在家庭中延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现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她的身份终于被证实。王秀兰在丢失档案30多年后,总算恢复了公职。恢复了公职的王秀兰欣喜若狂,她似乎又焕发了青春。她的职务依旧是轮台县委秘书。不幸的是,王秀兰恢复工作两年后病逝,那一年她还不到57岁。
在进疆的山东渤海老兵中,有一位赫赫有名的传染病专家。她从医60多年,为新疆军人、新疆各族人民的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她就是王云。
王云个子不高,满头银发,腰板直挺,很是干练。近90岁的老人,说话有条有理,走起路来带风。在她身上有着很多“不可思议”——她一个农村出身的“简师”女生,毅然决然弃学从军上战场;在解放大西北的战场上,日行军百八十里,不少女兵甚至一些小男兵都累垮了,掉队了,而16岁的医助王云却从来没掉过队;进新疆后,为了心爱的医学事业,她先后三次离开家,只身到上海等地学习深造,前后有八九年时间……
进疆后王云在师部医院任医生,几年后被选送到新疆军区卫校学习,当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在外地学习,她便把孩子托付给焉耆的一位维吾尔族老人照看,自己到千里之外的乌鲁木齐去求学。几年后,她又到第二军医大学学习临床专业。三年后完成学业回到新疆,被分到军区12医院当内科医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王云有幸被选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再次深造,专攻传染病学。她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再次放下家庭和家中的三个孩子。五年后她回到新疆军区,在总医院传染科任主治医生。一路走来,她全身心投入,勤奋地奉献着,由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直到被评定为技术四级、正军职待遇。
王云毕业的第二年,新疆边防部队发了严重的流行性痢疾。王云带队到一线调查,很快找出致病源,研究有效治疗方案,短期内就控制了疾病的蔓延。她把一个昏迷7天7夜的重症病人从死亡线上抢救了回来。在那次流行病治疗过程中,王云和她的团队创出抢救800多例中毒性痢疾患者无一人死亡的佳绩,得到军区嘉奖。
王云始终把病人当亲人,把职责当生命,在新疆军区总医院传染病防治领域,创造了多年的辉煌。横向比,在全国各大军区传染科,新疆军区总医院的传染科始终名列前茅;纵向比,在整个新疆,她和她的传染科更是首屈一指,成了权威、标杆和旗帜。王云,一位名副其实的传染病专家。
根据当时需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王云把主攻方向定位在肝病防治上。先是成立康复科,后改为康复医院,对重症肝炎、肝腹水、肝癌晚期患者的抢救治疗做了大量有益探索和尝试,并取得显著效果。她负责的康复医院,发展成新疆医疗技术高、科研能力强、设备先进的肝病治疗中心,也成为军区总医院的王牌科室。
王云主持开办的新疆最高水平的肝病防治学习班,在全国同领域引起轰动。她邀请国内外七八名顶级专家,为新疆肝病防治工作者进行系统的专业培训。王云是这么想的,新疆这么大,如果各地的肝病防治业务都开展好了,人们就不用不远千里把病号送来新疆军区总医院,那要为老百姓节约多少时间和金钱啊!
这位赫赫有名的女军医像一株常开常艳的美人蕉,85岁高龄还绽放在自己的岗位上。
60多年前,从南疆穿越天山到北疆并没有路。随着新中国第一代军垦人开进新疆,一条翻越天山的路——乌库公路(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筑路计划很快出炉。新疆兵团从部队抽调人员组建的工程支队,主要承担天格尔冰峰明槽湾道至巴拉堤沟的筑路任务。五位兵团姑娘主动请缨上冰峰修公路。她们是姜同云、刘君淑、陈桂英、田桂芬、王明珠。她们中最大的23岁,最小的只有17岁。
天格尔冰峰,天山腹地海拔4280米的冰达坂。这些兵团姑娘平时在戈壁荒滩上开荒、修渠、放牧、种棉种粮,巾帼不让须眉,可这是在“氧气吃不饱,风吹石头跑,人在冰上走,云在脚下飘”的极端地带修筑天路,中原地区来的女孩子哪里吃得消。工程队和所在连不予批准。不批准就写申请,递保证书,软磨硬泡。领导终于答应让她们试试。她们兴高采烈。
这是1957年。来自山东莱阳的军垦女兵姜同云与未婚夫举行完婚礼,第二天夫妻二人就分别上了天山,待两人再坐在一起吃饭已是一年以后的事了。刘君淑也是刚结婚,丈夫与她隔山相望。
风使劲舔着脸,雪疯狂割着肉,脚艰难踩着冰。上到半山腰,姜同云突然一脚踩滑滚了下去,人们被这瞬间险象吓呆,幸亏后面眼疾手快的战友使劲将她顶住。
两个月后,新修公路延伸到冰达坂下边,要上天格尔冰峰了。队长宣布:“女同志在山下做后勤补给工作,不上山。”姑娘们一听又急了:“我们就是来上山修路的。别处不去。”
“山上水烧不开,吃盐水泡饭;渴了,抓一把雪塞进嘴里;馍馍冻成坨bZqTt9uNX34xQ5gmTh5B49HVO8B+5lUVJawQStlCUAE=,用石头敲碎,含化了再咽。” 刘君淑回忆当年的情景,沉重得像是又重走了一趟冰达坂。
刚到冰峰,姑娘们就遇到困难,因受强烈冰雪光芒刺激患上雪盲症,眼睛流黄水,看不到东西,疼得把头直往雪里栽。不得已,用湿毛巾搭到眼睛上捂,多日才慢慢恢复。
在冰峰上修路,就是与冰雪、冻岩和极寒气候较劲。抡铁锤、打炮眼、放炮这些危险又困难的工作,女兵都抢着干。入冬后的冰达坂气温在零下40多摄氏度,一不小心,抓钢钎的手就被扯下一块皮。冰峰的地质构造特殊,刚打好的炮眼,过一夜里边就渗满雪水,姑娘们都是早上提前去先把炮眼擦干再装炸药。“即使是夏季,白天干活也要穿棉衣,夜里则要穿皮大衣。钢钎打进去,水从石头缝里流出来,溅到身上冷冰冰的。”
危险像潜伏的幽灵,无处不在。一天,王明珠所在爆破组放了一枚哑炮,她主动要求前去察看原因。当她系上保险绳,冒着烈风小心翼翼地靠近哑炮时,“砰”的一声巨响,石头和冰块齐飞,被气流掀翻的她仰坐在地上,几乎同时,一块巨石从她脚尖处滚了过去。“好险啊!”
乌库公路通车了!五位筑路姑娘被兵团誉为“冰峰五姑娘”。以那条跨越天山的公路为背景的“冰峰五姑娘”雕塑,成了一道人人仰慕的绝美风景。时光荏苒,一个甲子年匆匆而过,国道 314线乌鲁木齐至库尔勒路段早已升级为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和高速公路,海拔4280米处的天格尔峰路段被弃用,但那条天路两旁的冰达坂上,却年年盛开着高洁的雪莲花。
1952年夏日的一天,新疆军区来山东济宁招女兵了,这让19岁的金茂芳兴奋不已,她立马报了名。接到入疆通知,没敢等外出的父亲归来,她在母亲的泪眼婆娑中卷了床被子就住进招兵办。
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终于到达新疆,金茂芳被分配到石河子垦区。下车一看,荒漠连着戈壁,一间房子也没有;漠野的秋风一阵阵吹过来,像一群人在哭。老天还来了个下马威,没过中秋节,一场大雪就把地窝子给封死了。金茂芳当初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地方待一辈子。
新兵培训结束后分配工作,金茂芳的愿望是当一名拖拉机手。她如愿以偿,三个月集训结束就开始跟车了。她对自己说:金茂芳,国家把这么贵重的机器交给你,要好好干,可不能对不起这台拖拉机和这身军装啊!
第一次独立驾驶拖拉机,金茂芳兴奋极了。她驾驶的苏联产“莫特斯”,当时全兵团仅有8台。“莫特斯”是轮胎车子,不仅能犁、播、耙,还能挖甜菜挖洋芋,冬天就跑运输。那时拖拉机是稀罕物,长年不停歇,把作用发挥到极致。
金茂芳和同伴们天亮就起床,深夜才收工,喝凉水,啃干粮,累了就靠着拖拉机打个盹儿。“莫特斯”没有驾驶篷,夏日中午的荒原天上降火,地上冒烟,老远见不到一棵树,休息时就往拖拉机底下钻。开着车作业还好些,一停下来,蚊子就成群结队来围攻。新疆的蚊子又多又毒,凡裸露的部位都被咬得稀烂,有时她们被咬得直哭。后来,有人想出一个办法,往身上涂抹泥巴防蚊咬,大家纷纷效仿,出工时一个个像兵马俑。
金茂芳开着拖拉机四处作业,偌大的戈壁荒原都是她的家。她和机车组的同志从一开春出去,到十一月份天寒地冻不能犁地了才回连队。漠野上秋冬的风如鞭似刀,夹裹着沙粒在身上又抽又刮,皮衣皮帽皮毡筒都失去了效力,这让金茂芳原本白皙娇嫩的皮肤在炎夏挂了一层黑红的“釉”,秋冬又长出角质丰满的“保护层”。
“男女兵白天一起开荒,晚上就挤在一个铺上睡觉。那时条件艰苦,环境恶劣,都模糊了男女界限,有的是军人们一颗颗闪光的心。”一天晚上下起大雨,离连队太远回不去,四个拖拉机手就金茂芳一个女的,住一个苇棚,她就跟徒弟钻一个被窝睡,紧张得徒弟一宿没敢伸腿,可她放倒身子就呼呼睡着了。
1954年,机耕队实行男女混合开车,金茂芳与王盛基同车b1YIsLx4JqP9IPGHwaaCHalH/c0+HQ9Gle/0BSeOEVU=。在共同艰苦奋斗的日子里,他们演绎了一段爱情故事。王盛基大她两岁,人实诚帅气,技术好又肯干。他们恋爱后,虽然没有花前月下,但互帮互助,互为依靠。开荒的日子艰苦,爱情又使苦日子变得甜美和畅。1955年,两人随着十万大军一起转业,成了军垦职工。
甜美的好日子并没过长久,16年后王盛基因病去世,撇下年纪轻轻的金茂芳带着两个收养的孩子艰难度日。她一人拉扯两个儿女没有再嫁,就像自己坚守新疆屯垦戍边一辈子一样。
金茂芳一路走来,踏平坎坷,收获喜悦。她是兵团的“十大戈壁母亲”、自治区首届“新疆十大杰出母亲”,2019年,她荣获全国“最美奋斗者”称号。她还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第三版人民币一元纸币上的女拖拉机手原型,一个是石河子“戈壁母亲”雕塑中怀抱婴儿的母亲肖像原型。
金茂芳,一朵盛开在新疆戈壁滩上最美最艳的花!
胡杨,沙漠的图腾,秋天最美的树,在烈日中娇艳,在旱地上挺拔,不怕盐碱侵入骨髓,不畏风沙铺天盖地。我几次走进新疆塔里木,见到了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胡杨林,如醉如痴,流连忘返。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是“这一株”。
1952年秋天,新疆军区一领导到南疆塔里木垦区视察,军垦女兵胡子秧作为拖拉机手参加了座谈。领导被这位来自山东蒙阴的姑娘的自我介绍给逗乐了,建议她把名字改为胡杨,并鼓励说革命战士就要像胡杨一样,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从此,胡子秧成了胡杨。
1953年春天,胡杨驾驶着“阿特斯”,在疏附县草湖的千里漠野开出了第一犁。之后的岁月里,她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这条古丝绸之路,开垦了三十多万亩荒地。
面对家乡人,胡杨给我讲起了她的“新疆史”——
一天,我正在苇子滩开荒,指导员叫我到办公室去一趟。我明白,这是组织上来当红娘了。副处长指着一个大高个对我说:“他叫李建修,刚调过来的,是个很不错的同志,你们多了解一下。”就这样,我和李建修慢慢走到了一起。这是1956年的春天。
老李为人正,脾气好,技术棒,包容又幽默。结婚后,我开我的车,他量他的地,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老李奉命沿着叶尔羌河一路勘察设计。他走过的地方,一个个新农场被规划出来,我和我的机耕队就跟过来开荒,兵团随后在我们开出的地上组建新农场。到1960年,他的测绘队在叶尔羌河下游规划出最后一个农场,测绘队和机耕队就奉命全部留在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离麦盖提60多公里的一个农场,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
羊塔克,维吾尔语“八千里胡杨林”的意思。胡杨不光是最美的树,还是最大气最包容的树。它以独特的风骨,把自己活成“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的精灵。看着这些铁骨铮铮的胡杨,摸着这些断干少臂、流着血还硬挺着的胡杨,我常常被感动。我告诫自己,要向它们学习,做一棵名副其实的胡杨。
胡杨,一位传奇式的军垦女兵。她在死亡之海的边缘开了25年拖拉机,战斗生活了40多个春秋。她将自己长成一株坚韧无比的大树,活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胡杨。
褚春云和褚秋雨,一对来自山东沂水的姊妹花,“以身相许风雪国境线”的女英雄。姐妹俩作为“三代”工作队骨干,先后从不同垦区开进边境达因苏草原。几百号人汇集到大草原上,吃饭一时成了最大的难题,每人每天八两原粮根本不够吃,只好采野蘑菇打野菜充饥。
褚春云是卫生员,此时她的重要职责就是试吃战友采来的野蘑菇、打来的野菜,检验是否有毒。有一次,她因试吃了毒蘑菇被毒“死”了。大家忍着悲伤把她从卫生所抬到太平间,领来衣服棺材准备入殓,“死”了半天的她突然又活了过来。躲过一劫的褚春云丹心不改,继续为战友们当舌尖上的“扫雷英雄”。她因长期过量尝食有毒菜菌患上皮肤病,每到春季就全身皮肤大面积溃烂,一生未能根治。但由她建起的该地区一百三十多种山野菜和三十六种野生食用菌类的档案,以及举办了数百次的食用野生植物培训班,让后来进入该地区的边防部队再没有发生过类似中毒事件。
妹妹褚秋雨也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一位了不起的边地母亲。尽管为了戍边,她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
褚秋雨所在的牧业连,一年四季在草原上奔波,从夏牧场转到冬牧场,从冬牧场转到夏牧场。
褚秋雨与爱人是在1965年结的婚,婚后三天她就随牧业连去了冬牧场。在冬牧场放牧,几个人守着一大群羊,在空寂荒凉的山谷里一待就是半年。冬牧场往往离连队远,回团场要在白雪茫茫的草原上徒步四五天。大雪封山了,在撤回牧场的途中,褚秋雨所在的连队遭遇暴风雪袭击,三千多只羊被吹散。“三千多只羊,可是一个牧业连全部的家当啊!”为找回集体的羊群,她一个人与暴风雪搏斗了两天半,迷路后的褚秋雨最后被冻昏在雪地里,后来她被赶来救援的战友找到并救活,却被迫摘除了子宫。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是一群模糊了性别又有着明显性别标志的军垦战士。艰苦的条件,恶劣的环境,更坚定了她们的信念。她们从渤海湾畔来到新疆边陲,为了心中那份信仰,屯垦戍边一辈子。对于这些女兵来说,垦荒年代荣誉比健康更重要,信念比生命更重要。
这些进疆女兵,如同遍布新疆荒漠的野麻花,一年一年,一代一代,花开花枯,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