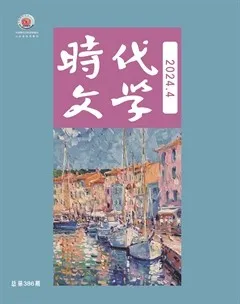密州的苏轼
飞蝗蔽空的日子
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来到号称“山东第二州”的密州(今山东省诸城)任知州,“新法”的弊端似乎具有高速的传染性,初来乍到,他就发现情况不妙。
密州其实是一个小城,街道冷清,建筑简陋,城外就是荒芜的旷野,大风呼啸,飞蓬在荒野肆意乱滚。这里不但无法与杭州相比,也远不及江浙很多富庶的县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前后,一场大旱灾袭击了密州、沂州等地,随后引发了铺天盖地的蝗灾。苏东坡在往密州赴任的路上,回想起几个月前杭州各个属县也爆发过蝗灾,当时蝗虫厚如乌云,一波一波从西北方向飞来,似乎西北有一个蝗虫的大本营!他曾经这样记录:“见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苏东坡所见的自西北方飞来的蝗虫,正是当时汴京以东一带蝗灾的余波。
苏东坡进入密州境内时,就看到田间道左,男女老少三五成群在奔忙不已,奋力捕杀蝗虫。他停下来仔细观察,发现村民用杂草将死掉的蝗虫包裹起来,挖地深埋。捕杀的场景一直绵延两百里地,累累虫坟不可胜数。
苏东坡一到达密州府上,就立即着手调查蝗灾、旱灾情况。这一年密州的秋旱特别严重,从夏至秋滴雨不落,秋小麦无法下种;等到一场不大的雨降临时,小麦已经错过了播种的季节,即使勉强种下,麦苗也无法生长。由此可以推断,明年春夏之际,密州将面临严重的饥荒。他注意到一个惊人的数字:当地捕杀蝗虫已有3万斛了。这是什么概念呢?宋朝时1斛为5斗,1斗就是10升啊。但飞蝗来势太大,简直杀不胜杀。
他拜访老农,研究剿灭蝗虫之法,终于懂得了蝗旱二灾发生发展、相互依存的关系。于是大力倡导“秉畀炎火”(火烧)、“荷锄散掘”(泥埋),利用雨后土质湿润松软的有利时机,深埋蝗卵,根绝后患。他鼓励百姓积极灭蝗除卵,深埋肥田,一举两得。
到任后的一个月里,苏东坡上《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和《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奏折,报告蝗灾的严重情形,对其前任的一些官员欺上瞒下的说法进行了批驳,比如,当地官吏认为蝗虫未构成大的灾害,有的甚至发出了“蝗虫飞来,能为民除草”的大谬之论。苏东坡请求朝廷豁免赋税或暂停征收青苗钱,否则,“饥羸之民,索之于沟壑”,而“寇攘为患”,“势必不止”。
但苏东坡内心充满了愤懑。他相信“头顶三尺有神明”,自古以来,连年冬天不下雪,夏天蝗虫必过境,这被视为“天罚”的征兆。他进而认为蝗虫之所以这么多,都是王安石推进的新法给闹的,他在给弟弟苏辙的诗中说:“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穷苦自招渠。”他的老朋友孔武仲对蝗灾抱有深仇大恨,认为比蝗灾更严重的就是眼下推行的新法。蝗灾还有消尽的时候,而且只有部分地区受灾,但是新法流布全国,看不到尽头,其危害比蝗灾严重多了。
不少人均有这种“新法引发天灾”的认知,旧党中的官员,尤其是每天要去田野捕蝗虫的官员,就借机上书神宗皇帝,要他赶紧向老天爷认错,废止新法。但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认为这世间事与老天爷没有任何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们更愿意相信雨多、雪多才是消除蝗灾的关键,捕杀蝗虫卵才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所以雨和雪变得弥足珍贵,它们关系到老百姓的粮食,也关系到新法能否顺利推行。
由此可见,雨雪是否降临,已经成为博弈的天平指针。
就在这时,开封飘起纷纷扬扬的雪花。新派官员蔡卞欣喜若狂,岂止是“瑞雪兆丰年”!这一场雪,对于新派改革生死攸关。蔡卞书《雪意帖》,记录了这场大雪对于嗷嗷待哺的黎民百姓和矛盾四起的朝政的深远意义。
问题在于,京城的雪能否挽救密州的百姓?
不能!
为了说服丞相,苏东坡动之以情:我这样守在边远地区的一个小官,都不值得朝廷杀我的头。如果飞蝗根本没有造成灾害,我怎么敢拿这事欺骗朝廷呢?如果您不相信我所说的,还要反反复复地考察验证,丧失了救民最佳时机,那么等到朝廷来人察访饥民时,恐怕只能在山谷间找到被抛弃的尸体了……
苏东坡深感后悔,为什么当初要自请移守密州,这样的心态在《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其二)中呈露无余: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
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
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
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
治理蝗虫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可喜的自然现象:“县前已窖八千斛,更看蚕妇过初眠。”因为“蚕一眠,则蝗不复生矣”。
来到密州的第一个春节就这样在沉闷和抑郁中默默度过了,好不容易盼来了上元节,本以为可以热闹一番的苏东坡再次深深地失望了,对杭州的思念突然如钱江潮水般涌来,他在《蝶恋花·密州上元》中说: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
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
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
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这“昏昏雪意”,延宕到第二年的四月,干旱和蝗灾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发严重了。苏东坡不能坐以待毙,他沐浴焚香,素食斋戒,两次登临境内有名的常山,虔诚祈祷。据《唐十道四蕃志》记载:“密州常山,齐时祈雨常应,因以得名。”苏轼两次率吏民群众登常山祈雨救旱,果然得雨。苏轼又发现常山“庙门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车轮,清凉滑甘,冬夏若一……乃琢石为井,其深七尺,广三之二”,此乃雩泉,苏轼又为百姓寻到了水源,使抗旱救灾进一步取得实效。
而这两次祈雨的结果,与他在凤翔府登太白山祈雨一样,天降甘露。苏轼欣喜若狂,他写《次韵章传道喜雨(祷常山而得)》:
山中归时风色变,中路已觉商羊舞。
夜窗骚骚闹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
従来蝗旱必相资,此事吾闻老农语。
庶将积润扫遗孽,收拾丰岁还明主。
春食苗,夏食叶
1075年正月二十,王弗的弟弟王缄从眉山来看望苏轼。看到妻弟,苏轼感慨万千,几杯酒下肚,他就醉了……他在密州时给叔丈王庆源写信提到:“近稍能饮酒,终日可饮十五银盏。”后来到了惠州时又给表兄程之才写信坦诚:“弟终日把盏,积计不过五银盏尔。”可见,他的酒量在逐渐衰减。
他刚一到任密州就遇天灾,而新法又让百姓负担加剧,社会民不聊生,盗贼四起……苏轼原来就没有储蓄的习惯,不料现在身为堂堂知州,竟然到了衣食难以为继的地步了。
王安石推行新法,大力削减公款费用,各级政府的小金库几乎都被收空,因此地方官员可支配的款项暴减。比如密州的政府用酒,一年不得超过一百石(一石约为100市斤)的规模。为此苏轼写诗发牢骚说,当年陶渊明区区一个县令,可以用官家田两顷中的50亩种上高粱酿酒,我如今身为知州,却只能“岁酿百石”,何以醉宾客?他情不自禁地怀念起身在富裕杭州的岁月。
无酒是小事,但饥肠辘辘,日子实在艰难。遥想唐朝诗人陆龟蒙写过一篇《杞菊赋》,讲自己实在没吃的,只好以杞菊(泛指野菜)为食。自此,枸杞和菊花固定成为一个高洁的意象,彰显了遗世独立、清贫自得的人生态度。古语里的菊,不仅仅指菊花,主要是指菊花菜,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茼蒿,这在古代甚至有“皇帝菜”的美称。苏东坡多半会想起屈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固然是中国最早食用花卉的记载,但痛AUCc+l9x+k1A6WyqPZEtNg==饮甘露、采食杞菊,仅仅是一种高洁的修行,并非长久之计。但事已至此,只能囫囵填饱肚子再说。
为此,苏轼写下《后杞菊赋》一文。他在序言讲自己曾读到陆龟蒙此文,一开始不以为然,觉得读书人即便坎坷,但生活俭省一点也可以对付下去,至于一个地方官饿到要吃野菜,那也太夸张了。现在呢,苏轼平生第一回体验到了这个境况。他承认自己为官19年,日渐贫困,衣食越发不如以前……
在自嘲之外,他更有椎心泣血的寄语:“……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核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据说有一次,孔子的学生曾参对子夏(卜商)说,退休之后准备到西河去养老。孔子死后,子夏到魏国西河去讲学,活到九十多岁。《抱朴子·仙药》中说:“南阳郦县山中有甘谷水。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堕其中,历世弥久,故水味为变。其临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食者无不老寿:高者百四五十岁,下者不失八九十,无夭年人,得此菊力也。”又据传说,河南南阳郦县饮甘谷水的居民均高寿,后以“西河南阳之寿”为咏长寿之典。
显然,苏轼在此使用的是反语。
情况万般无奈,他与当地通守刘廷式一起,每天沿城墙根寻找野菜来果腹……幽默是苏轼的天性,两人寻觅到野菜后,迫不及待地放到口中一顿大嚼,互相指着对方的肚子,哈哈大笑。
知州大人以野菜充饥的事传遍了密州城。城里富家被感动了,拿出粮食救济灾民,百姓才勉强度过了这个荒年。后来,民众在苏轼挖野菜的地方修建“杞菊园”,成为名胜景观。
自此,杞菊不断出现在他的诗文里,散发持续幽香。比如《超然台记》中“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唐陆鲁望砚铭》中“噫先生,隐唐余。甘杞菊,老樵渔”,《过云龙山人张天骥》中“饥寒天随子,杞菊自撷芼”,《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中“无复杞菊嘲寒悭”……
由此可见,苏轼笔下的杞菊,比起隐士们的清纯意象,又多了一层刺骨的寒意!
到“乌台诗案”爆发时,政敌们翻找苏轼作品,这篇《后杞菊赋》便成为证据之一。
举目满眼凄凉,苏轼的心情颇为抑郁。晚上回到家,有时小孩还缠着他哭闹,苏东坡有点不耐烦,禁不住发火。夫人王闰之开导他说,你怎能和小孩一般见识呢?不高高兴兴过日子,整天愁眉苦脸有什么用?听完,苏东坡恍然一怔,深感惭愧。王闰之为他洗好酒杯,让他以酒解愁。此事让他十分感慨,有如此豁达通透、善解人意的妻子,夫复何求!便作诗《小儿》,在诗中把王闰之和魏晋南北朝时刘伶的妇人进行一番对比,说闰之比刘伶妇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大胜刘伶妇,区区为酒钱”,自己自然也要比刘伶幸福得多。
其实,这分明是苦中作乐啊。
射虎的豪放词
有一个妇人白天把两个小孩放在沙滩上,自己去河边洗衣服,老虎从山上跑下来,妇人慌忙潜入水里躲避老虎,两个小孩子却依然在沙滩上玩耍……
老虎仔细看了很久,甚至用头来触碰两个小孩子,希望其中一个能够感到害怕,可是小孩子很天真,竟然不知道虎为何物。老虎感到无趣,便离开了。
老虎捕食,必定首先向对手施加淫威,但是对于不害怕者,老虎的威力不就没有施展的地方了吗?“是人非有以胜虎,而气已盖之矣。使人之不惧,皆如婴儿、醉人与其未及知之时,则虎畏之,无足怪者。”
这是《书孟德传后》的大致意思,这篇文章是苏轼根据苏辙的散文《孟德传》而写。现在他真的要与比老虎更凶猛的物种打交道了。
初冬的密州,一片萧条,到处都是光秃秃的,了无生机,寒冷如影随形,令人瑟瑟发抖,在旅途劳顿之中,苏轼竟遇到了一群骑马的土匪,他们提着翅膀乱抖的鸡鸭,拎着大包小包,马车里还有女子的啼哭声,很快消失在望不到尽头的路上。
苏轼询问前来接他的密州通判刘庭式,为什么密州的土匪如此猖狂?刘庭式不住地叹息,一言难尽啊。这群匪徒的头目叫何四两,他们打砸店铺,抢夺财产,侮辱妇女,老百姓每天过的都是胆战心惊的日子。苏轼不语,但下决心一定铲除这帮匪徒。
匪巢在哪里?这成了一个难题,被掠女子的丈夫名叫孟元,他告诉苏东坡一个线索,匪巢可能在常山深处的一座山神庙里。他把认识的老猎户余七请到密州府上,余七对那一带比较熟悉。苏轼在老猎户的帮助下,做好了抓捕匪徒的准备工作。
老猎户余七常年在山中穿行,苏轼向他悉心请教,包括如何狩猎野兔,如何骑马射箭,还有怎样驯鹰等。苏轼随余七一起到山野狩猎,他右手臂上架有一只被驯服的老鹰,肩上背着一张弩,左手牵着一只大黄狗,悄悄地为一举消灭匪徒做准备。那些官员们见苏轼整日狩猎,私下议论他不务正业,他笑而不语。他的很多苦闷不能与外人说,只能自行排遣。北宋前期,整个词坛沉浸在低回、纤细、粉色迷离的抒情中。苏轼置身北国高天,他那深沉辽阔的情思自然一泻千里。
熙宁八年(1075年)寒冬时节,苏轼在密州写出了一首流传千古的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
上阕说,我姑且抒发一下少年的豪情壮志,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托起苍鹰。诗人再写,我头戴华丽的帽子,身穿貂裘的衣服,带领抓捕匪徒的队伍席卷山岗。为报答全城人随我一同出来狩猎,我要学习孙权,亲自射杀猛虎。下阕写道,淋漓酣畅的沉醉,让我胸襟更开阔,胆气更豪壮,尽管两鬓已微微泛白,但又有什么关系!诗人说,等到皇帝派人下来,就像当年汉文帝派遣冯唐到云中赦免魏尚那般,对我重新予以信任,那时我会拉雕弓似满月一般,瞄准西北方向,射击侵犯之敌。
《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作品中极有分量的一篇,它不仅仅是记录游猎之词,更是苏轼亲手抓捕匪徒为民除害的热血之作。壮志男儿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力透纸背。作品豪迈旷达,别开生面,千年之后读到这首词,依然可以感受到作者立志保家卫国的沸腾热血和豪迈勇气。这可以看作北宋军民对外敌的强力回应,令人振聋发聩。
苏家兄弟幼年时,父母对他们讲述并演习孔子倡导的“射礼”。射箭是古代传统的技艺,也是评判君子之德的重要标准。嘉祐六年(10688ad9b73a702e1405d68d462e3d0e4f61年)底,苏轼来到了自己的人生仕途第一站:签书凤翔府判官。公务之余,血气方刚的苏轼对射箭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与当时北宋所面临的边境形势有关。北宋重文轻武,国力渐弱,边境烽烟四起,只能不断赔款,屈辱求和。苏轼在这段时期学习射箭,渴望自己能文武兼备。他写信告诉苏辙自己射箭的成绩:“官箭十二把,吾能十一把耳。”意思是自己练习箭术后,12把箭能射中11把!接到弟弟回信后,他意犹未尽,写下“穿杨自笑非猿臂,射隼长思逐马军”。自己射术甚佳,几乎百步穿杨,只是膂力差了。一个渴望驰骋疆场的“爱国诗人”形象呼之欲出!而经过这段时间的专心操练,他也有不少“文武打通”的心得:“共怪书生能破的,也如骁将解论文……观汝长身最堪学,定如髯羽便超群。”意思是感慨同僚对自己善射的赞叹和惊奇,指出无论是书生还是将军都应当文武兼修,也存有对北宋重文轻武的善意批评,体现了强烈的报国情怀。文末,他还不忘“调侃”弟弟,你长得比我高大,学习射箭肯定比我更出色。由此看来,苏洵“颇好言兵”的习惯深刻影响了两个儿子。
按照苏辙诗《闻子瞻习射》所载,苏轼“力薄仅能胜五斗,才高应自敌三军”。我们虽不至于过于较真,但大致可以推测出苏轼的膂力较弱,智力超群,所谓“良家六郡传真法,马上今谁最出群”,苏辙自然明白,哥哥胜在出众的指挥才能。
超然的境界
苏轼的杀虎之举声震四野,但刚刚收复的自信心,迅疾就被内心的忧伤所覆盖了。
有时,他只能写信给弟弟大倒苦水,感叹:“子由啊,你看我也当了这么多年的官,怎么日子越过越穷啊!”为排遣忧愁,他只能去哲学家庄子的神游思想中领略超然的境界……
诸城西北台下巷城墙上,有一座古意盎然的“废台”。
《超然台记》里有这样一段话:“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这就说明,苏轼修葺超然台绝不仅是为了一己游乐所在、忘忧之台,也是为“修补破败”。刚到密州的苏轼曾写下《雪后书北台壁二首》,其中就有“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之句。这就是说,在他来之前,北台就是城墙上的赏景之处。苏轼予以“增葺之”。熙宁八年(1075年)十一月,台成。苏轼写信告诉子由,子由依据《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意,将其命名为“超然”,并作《超然台赋》予以赞咏。超然,即超脱尘世、乐天知命的意思,弟弟也暗示哥哥,希望他彻底摆脱一度排遣不了的种种羁绊,这才有了《超然台记》这一千古名篇。有人赞说:“若无子由明兄意,神州那得超然台。优游物外迪心智,诸城至今寻旧台。”诚哉斯言!
《超然台记》里叙述了自己的生命状态,其实并非“不乐”。证据是苏轼在密州“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密州真的成了苏轼返老还童的福地吗?倒也未必,这是他的反讽策略,他不能让人从中找到“腹诽”朝政的明证。所以,他一再强调:“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而且,这个“物外”,是心系民瘼之余,放弃生活中的一切争斗,不为世俗物欲所累。
他的认识非常清醒:“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在如此“赢少输多”的博弈之下,他豁然开悟了,那就不再博弈,可否?
也就是说,苏轼最终选择了介入现实与超然物外并行不悖:满腔热忱介入现实,清心寡欲超然物外。密州时期苏东坡的文学创作出现了明显转变,他的文学救赎、责任担当、心灵寄放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厘清。
他找到了寄身天地、接通历史血脉之河的要津。
他必须学会放下。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里有绝妙概括:“人生最长也不过三万六千日,但是那已然够长了;即使他追寻长生不死的仙丹妙药终成泡影,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
苏轼自然是希望登台的人们登高四望,置身于忧愁之上,企望自己能超然于欲望之外,知足常乐。
知足。知足。
窗外的知了为什么一直叫个不停?铁锅炒沙子的声音是在提示什么?只要不是忧烦的步履声,就比一切都好!
夜里,恍惚的垂柳枝用最柔弱的细叶拂动水面,将蛰伏的暑气唤醒。水上的夜色像一个半醒的梦,让微光与水浪从头顶越过,就仿佛自己的手刚刚放下毛笔,从朝云的长发间穿过!
窗外的世界,看起来就是一泓波澜不兴的墨汁。墨汁什么都可以承载,却唯独不会承载自己。以墨显墨,不成立啊。
知足。知足吧。
熙宁九年(1076年)的中秋佳节,皓月当空,银光泻地,菊花游走在浮荡的银箔上,步步生韵,恍若仙佛镜像。
苏轼登临超然台,他对着一轮明月,抚琴、赏花,通宵痛饮。大醉之后,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苏轼想起了7年未能晤面的弟弟,他曾送扬州土产给子由,自谦“且同千里送鹅毛”。现在呢,密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寄送到济南那里了,好在兄弟同在一片月光下,那就送一片月光!月光会为每一个微笑镀银,月光会照彻历史的骨头,发出幽幽磷火。
他挥笔写出了一首足与星月同辉的杰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青壮时代的“狂”与“野性”,在这里早随风而去了。
可是,很多人忽略了词里昭示出来的苦闷,那种“进亦忧退亦忧”、进退失据的无奈。
苏轼的诗词流自于内心,他较少引经据典,那宛如岷江之水直冲霄汉的情怀撞击着历代读者的心弦。巡望宇宙人间,仕途浮沉不足虑,得失荣辱不足念,最需要小心呵护的就是一个人如同白驹过隙、与大自然相通的生命。人生的祝愿说一千道一万就集于“但愿人长久”,只要相知相思的人能够平安生活,生活就会因此而充满希望。
可以想象,飘荡在月光下,苏轼快浮起来了。超然台上,月华铺满天空,就像挥之不去的乡愁。谁都可以走进中秋时节这动人的一幕:山巅举起了湖泊,让平静的水融化在月光中,像一场大梦,酒杯则在月光的注视下变成了琥珀。这就像一棵大树不断向湖水派发树叶,而树叶转身眷恋大树。
不同时代的人朗诵着苏轼的词句,思绪已飞越了时间与空间。那些词句融入一束束烛光,融入一波一波的流水,也融入了每个人不同的生活。月光笼罩村庄和城市,笼罩大地与山峦,笼罩人间的欢喜和悲哀,但明月坦然而沉默,不动声色。数不清的月缺月圆,数不清的多愁善感,古往今来人们每逢佳节倍思亲,就是渴望融进那轮明月。明月如同一面镜子,也必会将同一轮圆月下彼此的思念、彼此的牵挂分赠给对方。人的生命因为月光而获得皎洁。
面对苏轼笔下放旷的辞章,难怪后人会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评价非常之高。它与《江城子·密州出猎》等词联袂而起,开启了豪放词的健雄罡风。而当时社会流行的词,不过是供市井消闲的柔美歌曲而已,至多只能展现私人生活和个性狭窄的侧面,低吟浅唱,属于佐酒的产物。谁有苏东坡这种豪迈的气象、敏锐的生命反思和深沉感情的倾泻?
苏轼初到密州之际正逢旱灾肆虐,并伴随严重的蝗灾与此起彼伏的匪盗。在他的精心治理下,到了1076年春天,密州的情况已大有改观,东坡心情大好,登上超然台,看到密州的景色,他突然觉得,这里的春色有一种人间的温情,氤氲一般从柳林间升腾……他写下了《望江南·超然台作》,俨然是一幅描写人文市井的画卷。这首词以潇洒清丽的文笔勾勒出了密州城无边的春色。这花木扶疏的春柳春水,固然引发其不尽的故园之情,他却又能从这种思乡情切中超然出来,“且将新火试新茶”,在酌酒吟诗中领略大好春光。然而细细品味,我们又分明能感到那种“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乡愁更为深切了。
“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殊。”如今江山依旧,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他的确难以抵达清静无为、独善其身之境,是故进亦难、退亦难。这就是苏轼“真是个超然”的尴尬世界……
熙宁九年(1076年)底,苏轼要调离密州了,他希望接任的知州孔宗翰可以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并一再嘱咐:“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
苏轼离别密州时百姓们前来送行,遮道哭泣,洒泪相别。密州的百姓绘东坡像立于城西的彭氏园中,春秋二季前往拜谒,这也成为当地“寿苏会”的肇始。
元丰八年(1085年)十月,苏轼赴登州任太守时途经密州,在此小住了几天。知州霍翔在超然台上设宴款待,当地百姓听说后,都来看望他。“重来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那些曾被苏东坡收养的弃儿及其养父母,都相继赶往州衙拜谢救命恩人。“山中儿童拍手笑,问我西去何当还?”乡亲父老的不舍挽留,是对苏东坡的最高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