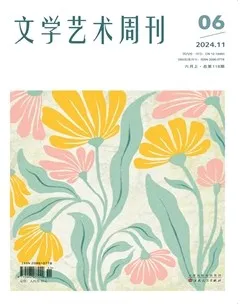从《金锁记》英译本变迁史看张爱玲的离散体验、 创作心境与文化记忆
张 爱 玲( 英 文 名 Eileen Chang,1920— 1995)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充满传奇色彩 的女性作家和翻译家。《金锁记》是张爱玲最 为成功的小说之一。傅雷盛赞《金锁记》是 “张女士截至目前的最完满之作……至少也该 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夏志清更 是评价它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 说”。张爱玲本人也对这部作品格外看重。当 她于 1955 年远走美国,决心在异国他乡重新开 启自己的文学事业时,她选择将《金锁记》的 英译本 The Pink Tears 作为在美国文学市场的第 一次试水。遗憾的是,The Pink Tears 并未获得 出版的机会。之后的十余年内,张爱玲将《金 锁记》改写为《怨女》并同步自译为 The Rouge of the North,后又应夏志清编撰中国小说选集 之邀,第三次将《金锁记》自译为 The Golden Cangue。如此曲折复杂的自译历程,放在整个 翻译史上也实属罕见。这一过程既深受她本人 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和文化场域影响,也与其离散体验和文化记忆紧密相连。本文将张爱玲 定位为“离散译者”,并将以“离散”和“自 译”两大关键词为抓手,运用文本分析和超文 本分析并行的研究方法,试图全景式地勾勒出 《金锁记》英译本的整个变迁史,以揭示张爱 玲自译行为背后的深层心理与文化烙印。
一、《金锁记》与 The Pink Tears:未能面世的 首次尝试
The Pink Tears 是《 金锁记》 的第一个英 译本,也是张爱玲想要进入美国文学市场的 首次尝试。遗憾的是,The Pink Tears 接连遭到 Scribner’s(斯克里布纳出版社)、Knopf(克 诺夫出版集团)、Norton(诺顿出版社)等美 国知名出版社的拒稿,最终无缘出版,连底本 也没有留下。因此,我们无法对《金锁记》 与 The Pink Tears 做文本比对分析。然而,了解 The Pink Tears 的自译过程,对于分析后来第二
个译本 The Rouge of the North 还是具有重要意 义的。
首先,通过考证张爱玲与好友宋淇的书信 内容,可以推断出张爱玲在 The Pink Tears 中已 经有“改译”的动作,再更进一步推测,The Pink Tears 很可能就是 The Rouge of the North 的 雏形。张爱玲在书信中说: “上次我告诉 Mae (即张爱玲好友邝文美)不能决定 The Pink Tears 下半部怎样,现在已和 Mrs Rodell(张爱 玲在美国的出版经纪人)讨论过,她认为可以 完全不要,plot(情节)不要太复杂。我也觉 得现在这故事发展得和从前很两样,前半部已 经成了个独立的故事。”从张爱玲的自述中可 以得知两个关键信息:一是 The Pink Tears 相 较于《金锁记》篇幅更长,分为上下两部;二 是前半部的故事是张爱玲新加入的,并足以被 视为一个独立的故事。种种迹象都可以证明, 张爱玲起初便打算改译《金锁记》,将其以新 的内容和形式呈现给英文读者。但这一意愿首 先遭到了美国编辑泼冷水,他们不约而同地表 示该小说“人物太不令人同情”,这些评价折 射出美国编辑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及受冷战思维 影响的政治疑虑。从 The Pink Tears 的翻译过 程,我们可以一窥张爱玲初到美国时的心态。 彼时的她身上既有要靠出版作品维持生计的焦 虑,也有对作品艺术性的高要求。关于她具体 是如何在英译本中倾注个人情感,传达艺术追 求,则要分析成功出版的《金锁记》的另外两 个译本——The Rouge of the North 及 The Golden Cangue。
二、《金锁记》与 The Rouge of the North:改 译过程中的情感转向
《金锁记》在改译中被赋予了结构功能, 成为 The Rouge of the North 的叙述功能体,承 担了作为叙事起因或发展枢纽的责任。而在The Rouge of the North 的改译中,有几个明显的 改动体现出张爱玲的情感转向。
( 一 )英文译名的由来和在小说中的回扣
在小说题记中,张爱玲特意为英文译名 The Rouge ofthe North 做注解:The face powder of southern dynasties, The rouge of northern lands.Chinese expression for the beauties of the country,Probably seventh century.(南朝金粉,北地胭脂。中文泛指倾 国之美女,大约始于七世纪。[1] )
该题记言明英文译名出自中国典籍里“倾 国之美女”的说法——南朝金粉,北地胭脂。 张爱玲此处的引用,不单是想借中文典故表明 The Rouge of the North 的女主人公银娣的美貌 与传奇性。在正文中,她也多次回扣“南”与 “北”这对地域概念。银娣本身是南方人,嫁 到北方的大家族中,逐渐被同化,喜欢自己涂 抹胭脂后的样子,因为那样显得她像北方人。 即使后来因为战乱逃亡到南方,她也一直念着 “还是北方好”。这种对南北差异的反复书写 是《金锁记》中所没有的。
(二)故事情节的增补、删减和结局的改动
在正文中,张爱玲有意增补、删减和改动 了部分情节,这些变化也体现出了她的情感转 向。在增补部分,The Rouge of the North 没有沿 用《金锁记》那个著名的以月亮为意象的倒叙 开头“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 而是平铺直叙,从银娣在娘家的生活写起,以 纪实般的笔触记录了媒人说亲、举行婚礼、新
婚生活、怀孕生子的全过程,之后的故事才与 《金锁记》开头的时间衔接上。在这段增补的 内容里,张爱玲不仅详细介绍了银娣的家世、 性格和新婚时期的遭遇,也对中国的传统习俗 做出了细致入微的刻画,这成为英译本的一大 特色。笔者认为,这更像是张爱玲在离散状态 下试图回忆、梳理祖国的文化,并在这种回溯 中不断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定位。
在人称和俗语的翻译上,张爱玲坚持先用 拼音传递中文原意,再在后文追加解释其英文 含义。这样做实际上会比中文版《怨女》的语 句更为累赘,但也体现了张爱玲对中华文化主 体性的坚持。
"Have tea, Gu Ya and Gu Nana",Bingfa's wife used the polite terms for the son-in-law and the married daughter of the house, called Master of Miss and Madame Miss.
(炳发老婆捧上茶来,茶碗盖上有 只青果。“姑爷姑奶奶吃青果茶,亲亲热 热。”——《怨女》)
在这段文字中,张爱玲先是音译了“姑 爷”和“姑奶奶”这两个名词,然后解释这是 对银娣丈夫和银娣的礼貌性称呼。
在其他段落中,比如翻译中式婚礼上常见 的食物及其象征意义时,张爱玲保持了中文音 译先行、英文注释后行的原则,如“ching guo, green olive”指的就是青果,还有常用的祝福语 如“ching ching jurhjurh”(亲亲热热)、“tien tien mimi”(甜甜蜜蜜)等。
在删减部分,张爱玲最大的改动是删去了 《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女儿长安的角色,由此 舍弃了将女主人公曹七巧的恶人形象推向巅峰 的高潮部分——因嫉妒设计拆散女儿与其如意 郎君的美好姻缘。这一做法直接弱化了原作曹 七巧那种疯狂极端的恶。若要深入探究张爱玲
改译的心理,则应与张爱玲后期写作风格的转 变和离散经历的投射有关。其一,张爱玲在赴 美前与胡适的通信中,就已经表示出对《海上 花》式的“平淡而自然”的向往。在 20 世纪 40 年代出版的小说集《传奇》的绮丽烟火逝去 之后,张爱玲就开始了对新风格的探索,《十八 春》《小艾》《秧歌》等作品的风格都尽力向 “平淡而自然”靠拢。而到了改译 The Rouge of the North 的时候,张爱玲对于驾驭新的小说 风格已有不少经验心得,银娣人物性格的平淡 化和细腻化与全文的风格改变一致,不显得突 兀或者令人惋惜。其二,针对 The Rouge of the North 中女主人公银娣恶的减轻,高全之认为, 其根源在于作者艺术距离的拉近。前文提到, 银娣的“南人北化”与张爱玲的离散经历互通 表里,而为了更好地将自身情感投射到银娣身 上,张爱玲选择“善良化”银娣,拉近与她的 情感距离,也使读者更容易理解与接受这种投 射。
在对结局的改动中,作者的情感倾向也很 明显。《金锁记》中曹七巧的结局是迫害尽身 边人,然后在病榻上孤独地死去。The Rouge of the North 则结束于银娣的幻梦:
Everything she drew comfort from was gone, had never happened. Nothing much had happened to her yet.
"Miss! Miss!"
Her name was being called. He was calling her outside the door.
(她引以自慰的一切突然都没有了, 根本没有这些事,她这辈子还没经过什么 事。
“大姑娘!大姑娘!”
有人在叫着她的名字。他在门外叫她。) 如果说《金锁记》中曹七巧的结局是“恶
有恶报”,其用笔之狠辣,仿佛是作者对曹七 巧累累恶行的最终审判;那么在对银娣的人生 做总结时,张爱玲却变得格外仁慈,赋予她幻 梦一场后回归本真的权利。在结尾处,张爱玲 让银娣重返故事的起点——她不谙世事的少女 时期,后续的一切错误都还没发生。不似曹七 巧那般万劫不复,银娣似乎还有重生的可能。 这种怜悯和关怀的情感更是作者与角色之间艺 术距离拉近的有力证明。
三、《金锁记》与 The Golden Cangue: 忠实自 译背后的离散情绪与文化记忆
1966 年,受夏志清邀请,张爱玲又将《金 锁记》直译为 The Golden Cangue,于 1971 年 收 入 夏 志 清 主 编 的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 。再 次选择对《金锁记》进行翻译是张爱玲自己的 意愿。她在写给夏志清的书信中解释道:“因 为这故事搞来搞去有四分之一世纪之久,先后 参看或有猎奇的兴趣。”然而她自己却对翻译 成品不甚满意。对密友宋淇更是直言“译《金 锁记》非常倒胃口,这话不能对志清说,仿 佛我这人太不识好歹。总之‘you can't go home again’”。赴美后几次英文小说出版的受阻 和市场的冷遇,让张爱玲彻底认识并接受自己 的作品与西方读者存在无法跨越的“语言之外 的障碍,如‘东方主义’、政治因素、意识形 态,及真人真事作为原型的复杂性,等等”。 离散多年,创作心态和写作风格早已改变的张 爱玲,要想再用英文重现她 20 世纪 40 年代那 种“大红大绿式对照”的飞扬风格,已经是心力不足了。
尽管如此,张爱玲还是尽己所能地还原 《金锁记》的风貌。The Golden Cangue 与 The Rouge ofthe North 在翻译策略上的显著差异是注 释的有无。The Rouge of the North 全文无注释, 张爱玲要么直接在后文加补充说明,要么则根 本不说明。The Golden Cangue 中共有 16 个注 释,主要针对一些中国文化专有词汇,如“朵 云轩”“锯了嘴的葫芦”“葱白线香滚”等。 这种极度认真的态度,体现出中国古典小说传 统在张爱玲心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将这种 传统准确无误地传递给西方读者的愿景。
四、结语
张爱玲对《金锁记》的三次英译,是其离 散经验累积、文化记忆回溯、创作心境变化等 多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结果。张爱玲在翻译过 程中的情感和心境,表现出其与中华文化若即 若离,需要不断构建和对话的不稳定状态。而 这也正是离散者的典型特征。萨义德曾这样描 述离散者的状态:“他们存在于一种之间状态, 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 离。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 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张爱玲就处在这样一 种中间状态,勉力维持自身平衡,抗拒全盘遗 弃祖国文化或者全面投降于新文化。
[ 作者简介 ] 许以萌,女,汉族,福建泉州人, 厦门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翻译史与翻译 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