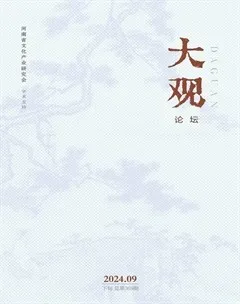从《查波罗什人复信土耳其苏丹》看列宾人物形象的再创造
摘 要: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19世纪中叶出生于乌克兰的楚谷耶夫。列宾青年时代曾接受过完整的学院教育,并赴西欧留学。列宾的创作题材涉猎广泛,包括历史画、风俗画、肖像画等。他着重表达沙皇统治下俄国劳动人民的苦难,主张真实地描绘俄国的历史与社会生活,深刻揭露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矛盾。他创作的主题性画作,对人物的性格、情绪、精神状态都有着精彩的表现,体现了现实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观众以强大的震撼。通过对历史画《查波罗什人复信土耳其苏丹》在造型方式与形式语言方面的分析,还原列宾创造出鲜活的艺术形象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研究油画本体语言与主题性创作有着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关键词:列宾;人物形象;主题性创作;现实主义
一、艺术形象的创造与升华
谈到主题性创作中的人物形象设计,列宾在创作之前就已经形成大致的形象轮廓,这得益于他对于历史和文学的兴趣。也就是说,列宾画面中的人物形象来源于他的想象和对模特的观察研究,由二者相互结合而成。列宾说:“我总是依据模特和自己的想象力作画。”[1]这种形象的创造既是对人物共性的一种艺术归纳,又赋予了人物特征具体性。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认为作品中的典型就是一个人,同时又是许多人,也就是说在描写一个人时,使他自身包含表达同一概念的许多人[2]。
《查波罗什人复信土耳其苏丹》这幅作品于1891年首次向观众公开展示。这也是列宾第一次在皇家美术学院举办个人画展。同年该画被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以35 000卢布购买,成为俄罗斯绘画史上最高价格的作品。列宾制作并推敲这幅作品用了很长的时间,这幅作品诞生于列宾创作最为繁盛的时期。
在这幅作品中,对立的双方一方为奥斯曼土耳其,15—19世纪他们称霸欧洲,并想对抗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另一方则是无休止扩大疆域的沙俄。双方战事频繁。17—19世纪,双方经历了十几场战争,是有史以来交战最多的两个国家。这幅作品就是描述这个历史0e550336f12ca7db5828dba9e80423fd5dbe6866bf19b37d26623224bf4536e8背景下苏丹王企图劝降哥萨克人不成反被嘲笑的故事。
本文以这幅作品的两个版本为例,从构图安排来看列宾创作的不同视角。在第一个版本中,构图上列宾以首领谢尔各和手握白色鹅毛笔的书吏为中心,其他的哥萨克战士排列周围,使整个画面形成一个同心圆。这种构图的方式曾多次出现在列宾的画面中,如《国务会议》和《亚历山大三世在莫斯科彼得罗夫斯基宫殿的院子里接待农村地区的老人》都采用过这种环形的构图框架。在这幅画的左侧有一个背对观众站立的人物,画面右侧则站着一位同样背对观者的穿白色大衣的男子,为画面视野增添了边界感。中心背对着观众的白衣光头男子身体侧倾,从其光秃秃的头顶到画面中心的书吏形象再到头戴金色帽子的老头,他的右手高高挥起指向后方,形成了空间的纵深感。列宾在创作中,又安排了各种不同的面孔,通过正面或侧面角度的穿插,有效地组织和暗示了画面的空间位置。这种安排使作品和观者之间产生一种交流,使观者仿佛置身于场景之中,为其带来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在第二个版本中,画面右侧人物服饰最为丰富,色彩也最为艳丽,神情夸张的人物成为画面的一个焦点。在这个版本中,左上第三42340a0d2611787b5fcfb6a516424fe34d0f5ca6a42c3d53fa105a6300e19b11个人物头戴红色黑边帽子,表情严肃紧张,形象十分独特。这个人被视为列宾的化身,表现出画家的批判性视角。第二个版本的构图采用了多个画眼的画面布局,通过浓郁的色彩、夸张的表情在画面中同时形成多个视觉焦点。
从画面的色彩来看,第一个版本的色彩更为浓郁,色调也更为接近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色彩;第二个版本的色彩相对于第一个版本色彩更为艳丽,具有浪漫主义气质。总体来看,这两幅作品的视觉效果画面凝重,笔触、色彩、肌理都极具油画语言的美感,造型严谨,体现了形、色、笔三者的高度结合;画面薄厚有序,且相互交替;对于人物的塑造,体块的归纳结实有力,下笔见形、见质。这些特点体现了列宾从写生中锤炼出的高超的造型能力。
二、情节与细节
在这幅作品中,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是通过对笑的描绘表现出来的。这幅画可谓是一本关于“笑”的百科全书,列宾的创作基于他的想象和日常写生,经过反复提炼,不仅构建出一个人为的现实场景,还传达出这个场景以外的要素。《查波罗什人复信土耳其苏丹》便是如此。在观看这幅作品的时候,人们仿佛能够听到画面喧闹的氛围之外各种隐隐约约的笑声。画面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在笑,而且每个人的笑容都不尽相同,有人捧腹大笑,有人讥讽地笑,有人诡秘地微笑,有人会心地微笑,有人挖苦地笑,有人讥讽地笑,有人戏谑地笑,也有人轻蔑地笑……各种各样的笑形成宏大的画外音,可谓此处无声胜有声。这是列宾创作中鲜明的特点。
从列宾的肖像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是画手的大师,也可以发现列宾对细节的极致推敲与精益求精的精神。在《查波罗什人复信土耳其苏丹》一画中,列宾描绘了不同姿态的手,每一双都是鲜活的。首先,一些手可引导观众的目光在画面中游走,或是引导观众的目光到画面的消失点。如画面右侧穿白色大衣的人,他的手指向画面中央的人物群组,这群人是反映画面主题的核心。这里手的姿态起到引导观众注意画面中心的作用。其次,有些手可辅助点出画面的主题,如画面中心上部,刻画了一个左手拿着烟管,头戴金色帽子的老头,他的右手高高挥起指向后方。将这个手势结合人物的表情来看,体现了一种和回信内容相一致的戏谑。再次,有些手的姿态增强了现实主义绘画作品的生活性,增加了真实感,呈现了人物自由与随意的姿态,提升了画面的生动性。例如:画面左侧第一位突出的人物,他黑黝黝的健壮手臂捶在同伴的后背上;画面左下角醉倒不起的酒鬼,右手无力地伸出来;右侧有着红鼻头,头戴白色帽子的长者捧腹大笑时张开的手等。这些手都很好地表现出哥萨克人热爱自由与豪放乐观的性格特点。
这幅作品高度体现了列宾对生活的热爱。在《查波罗什人复信土耳其苏丹》的画面中,很多细节的组织安排体现出哥萨克人的特征。例如:画面中每一个主要人物的身上都配有一个小酒囊,桌子上放着酒壶;画面中的人物很多都是微醉状态,豪放的酒神崇拜和狂欢文化是哥萨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列宾的细节描绘体现了哥萨克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酷爱饮酒的生活习惯。为了创作这幅作品,列宾曾仔细研究各种考古资料,了解哥萨克人及整个部落的特点,观察他们的生活。在没有照相机的时代,他用油画和水彩不厌其烦地记录了很多具有民族特征的道具和饰物。列宾通过这些细节展现了哥萨克人的奔放、乐观、热爱自由的精神面貌,以及富有魅力的文化特征。
纵观列宾的这幅作品,大量的人物特征、饰品、道具、服装都来自他对日常生活的写生。他运用导演一般的组织整合的能力,创造出带有极强时代精神与特征的现实主义画面,甚至为人们带来超越视觉感受的其他感官刺激或心理感受。从事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创作者必须学习和掌握这种解构重组的技术手段,而不是借助摄影简单地再现对象。
对列宾的油画《查波罗什人复信土耳其苏丹》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列宾创造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的过程。此画所涉及的事件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至今尚未确定,但列宾通过历史叙事的文本、对俄罗斯历史场景的研究以及主观想象,成功地重构了视觉叙事的场景和情节,创造了极具艺术感染力的人物形象。列宾卓越的艺术才华,将查波罗什人的外貌和复杂的情感表达得如此贴切、深刻。他以精湛的技艺创造出的人物形象情感充沛、有血有肉,可称为“神来之笔”。笔者叹服于列宾对人性的深刻体察,以及创造人物形象的能力。同时场景、环境、光线的设计也最大化地配合人物形象。在这一切因素的作用下,画面形成了一种现实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贴近了更高层次的真实,而这种真实的载体就是一个个闪耀着人性光芒的带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精神的艺术形象。
三、现实与想象
在西方,绘画是造型艺术的一个种类,形象的创造才是绘画艺术的永恒命题。从列宾开始创作这一主题时的草图来分析,对于画面戏剧性场景的设计和安排,他没有直接描绘战士们慷慨激昂的战斗瞬间,而选择了回信嘲讽土耳其苏丹的瞬间。这一设计让观众感觉到查波罗什人乐观、诙谐的艺术形象,从而感受到一种轻松有趣的气氛。这个瞬间所带来的时间感和激发的想象力,完美展示了戏剧性情节在平面绘画中的张力。作品努力避开了对战场的直接描绘,而着力于塑造回信时战士们勇敢、轻松的形象,他们的表情、状态、动作可以唤起观众对人性话题的思考。这正是在探讨诗歌、文学与造型艺术区别时莱辛所强调的“视觉形象与文学形象在表现同一情节时必然具有的不同侧重面——文学中具有诗韵的‘哀号’恰恰不能转化为视觉造型,视觉造型的瞬间选择必须符合造型审美的要求。”[3]因此可以看到,在列宾画草图或构思阶段,人物动作关系、场景、光线都是在写生中完成画面整合的。对于写生与创作的关系,列宾是先创作或想象一个场景,然后在现实中寻找相应的人物形象、构建某种和预设相似的典型环境,甚至连道具、服装他都亲手制作。这种对于场景、人物、道具的设计让人想到了电影和戏剧艺术,而列宾就像一个脑子里已经有了剧本的导演。
当然,创作的过程因人而异,不可能全是上述的过程。有时候在生活中偶然遇到的场景也可能触发艺术家的创造思维,成为画家灵感与想象的来源。但是主题性创作绝非对生活真实的简单还原,也不是对一个人物形象的照搬。笔者认为,欧洲优秀的绘画传统从未将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描绘视为艺术的最高境界。即使在画面中设计出戏剧性的场景和人物,也不是简单地复制事件和人物的原始形态。戏剧性叙事是一种通过有限平面最大程度地展现事件的社会意义与人文内涵、传达人物关系以及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创作方法和语言,而绝非还原真实现场的某种手段。很多时候,艺术家甚至需要跳脱这些所谓的真实现场,才能创作出具有宏大气象的史诗作品。在图片时代的大背景下,很多创作者把精力都放在画面的细腻描绘上。因此画面虽然写实,但空洞无味。这种情况反映出创作者缺乏对生活的观察和提炼,缺乏对于社会生活和人的理解,因此,对画面中的人的描写只停留在对“像”的模拟层面,谈不到人物形象的再创造。
写实并不是对物象亦步亦趋的描摹,而是对视觉对象的一种提炼和概括,体现出画家的审美素养和追求。同时每个艺术家对写实的表达也不是千篇一律的,更不是相片这类机械图像可以替代的。因此,创作者应静下心来深入研究西方油画的造型规律与本体语言,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人云亦云。
同时,表现一个人物的形象与性格并不一定需要宏大或特殊的场面作为背景,日常的环境或场景往往就是很好的背景与舞台。在很多优秀的作品中,一个平凡的背景、一个简单的人物或组合往往就能够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特征。例如,《查波罗什人复信土耳其苏丹》的环境设定在一个普通的战场上,没有壮丽的俄罗斯风景,没有某种暗示冲突或斗争的复杂背景。然而,这幅画向人们展现了现实生活中更为深刻的人性特征和由此形成的经典人物形象。这种对画面形象和环境关系的处理是他作为现实主义画家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难能可贵之处。
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在创作一幅主题性画面时,其实也是在构建一种真实。这种真实不是普通平凡的真实,而是排除了日常可见的一切琐碎与干扰之后的更高意义的真实,是艺术的真实。而列宾追求的就是一种超越肉眼所见的、带有时代特征和民族性的、更贴合社会与大众心理的真实。这种真实准确地表现了俄罗斯民族的精神,也只有这种真实才能使绘画作品产生超越时代的艺术感染力,使不同地域和民族的观众都能产生强烈的艺术震撼与深刻的共鸣,因此对这种民族精神的准确表达才是俄罗斯油画艺术的灵魂。
四、结语
在图像时代,架上绘画逐渐被边缘化。随着科技的进步,未来的人们也许轻敲几个按键,就能通过人工智能软件快速输出一幅特定主题的视觉艺术作品,并且几乎没有成本。但当人们再度审视和品味百年前列宾的作品,依然能被创作者极高的艺术才华与创造智慧所震撼。关于要不要在快节奏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去继承列宾所代表的写实绘画或主题创作的传统这一问题,艺术圈可能会有很大的争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艺术创造以及这种创造的品质将是人类最终区别于人工智能或电脑算法的核心领域。
参考文献:
[1]普罗罗科娃.列宾传[M].焦广田,译.郑州:海燕出版社,2005:193.
[2]袁菲,江振兴.从《杨靖宇》看主旋律人物电影的类型探索[J].电影文学,2020(4):112-114.
[3]莱辛.拉奥孔[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0.
作者单位:
中央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