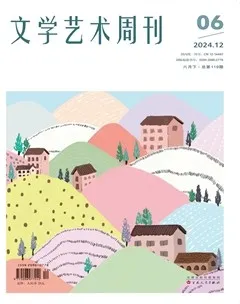《女勇士》中移民对身份的探寻与认同
《女勇士》基于作者汤亭亭亲历的文化身份探寻与认同过程,讲述了第一代移民与第二代移民的经历。其中,第一代移民的故事包括:在中国曾是一位成功医生,后搬往美国一切生活重新开始的母亲勇兰;前往美国寻找丈夫,被拒之门外后精神状况堪忧,后被送往收容所的姨妈月兰。第二代移民指的是在美国出生并长大的“我”,和“我”认识的华裔女孩,她们的生活刻上了美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双重烙印。本文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美籍华裔的身份探寻及结果,得出结论:不论第一代移民还是第二代移民,都无法维持单一的文化身份。移民的双重文化身份恰恰形成了区别于母国文化和移民国文化的第三种文化。
一、背景介绍
美国文学以其多元的民族性为特色,即主流文学以白人为主,同时伴随着较为强大的黑人文学和犹太文学。自 20世纪60年代起,美 国华裔文学作为一股强大而充满活力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美国华裔文学通常指在美国出生并长大的美籍华裔作家的著作。他们从小接受精英教育,能够熟练掌握并用地道的英语进行写作。受中国父母的影响,美国华裔作家自然而然地继承了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和传统。
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作品通常聚焦于中国传统、礼仪、习俗,特别是美国华人社区的状况,即唐人街的人文风貌。第二阶段,作家们开始关注中美文化之间的碰撞与冲突,如第一代移民与其在美国出生的子女之间的代沟。尽管第一代移民留在了美洲大陆,但他们在精神上仍然牵挂着祖国;与此同时,子女们则将父母的传统观念和习俗视为外来之物,更认同并追求自己的西方生活方式。第三阶段,相关作品聚焦于第二代移民如何同时融入两国的文化中。由于移民的情况已不如之前那样罕见,年青一代更倾向于以积极的态度接受外来文化。第四阶段,美国华裔作家倾向于从美国人的视角观察中国文化,并重新思考原生的中国文化与美国现实之间的关系。
汤亭亭是一位美籍华裔小说家,祖籍中国广东。她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语文学系。20世纪60年代起,汤亭亭在加州中学担任英语教师,后移居夏威夷。目前,她继续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教学工作。1992年,汤亭亭当选为美国人文和自然科学院士,并在2008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文学杰出贡献奖。汤亭亭的主要作品包括《女勇士》(1976)、《中国佬》(1980)和《孙行者》(1989)。作为汤亭亭的首部作品,《女勇士》的出版奠定了她在美国文学界的地位。该书以中美两国作为背景,展现了一个女孩的童年记忆和华裔移民的生活状态。在作品中,汤亭亭探讨了作为华裔美国人的深层含义。从对中国的幻想跳跃到美国的现实,该书通过华裔美国女性的生活轨迹,反映了移民对文化身份的追寻。作品以大胆的想象力和简 洁的笔触,特别强调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文化冲突等议题。
二、第一代移民的文化身份探寻与认同
第一代移民指的是“我”的母亲勇兰,她努力做出各种尝试积极适应美国生活;“我”的姨妈月兰来到美国寻找她的丈夫,但无法很 好地融入新环境,最终住进了收容所。
(一)勇兰的探寻与认同
《女勇士》描绘了“我”的母亲勇兰赴美之前在医学院学习并最终成为医生的经历。作 者以勇兰的话作为整本书的开头,“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事”,这无疑是一种吸引读者继续阅读的手段。此外,这也暗示了母亲勇兰给人的第一印象,即一个机智的故事讲述者和一个谨慎的秘密守护者。
在描写勇兰的章节中,文本中的意象总是围绕着一个词:鬼怪。比如,房间鬼怪、出租车鬼怪、公交车鬼怪、警察鬼怪、火灾鬼怪、电表工鬼怪、修剪树木的鬼怪、廉价商品鬼怪、吉卜赛鬼怪、报童鬼怪、水井鬼怪、杂货店鬼怪、顾客鬼怪、牛奶鬼怪、邮件鬼怪、垃圾鬼怪、社会工作者鬼怪、公共卫生护士鬼怪、工厂鬼怪、窃贼鬼怪、流浪汉鬼怪、酒鬼鬼怪、红嘴鬼怪、黑鬼怪和白鬼怪。在与“我”的一次交谈中,她表达了自己对鬼怪的感受——她总是害怕那些无法控制的力量,认为这个世界是由鬼怪构成的。事实上,母亲讲述的故事暗示了这本书的副标题,即“一个生活在鬼怪中的女孩的童年回忆”。
在中国时,母亲勇兰讲述她的故事,在那里,她作为一位成功的医生被村民们所敬仰,甚至在婚后还保留着自己的姓氏,成为一位现代女性。勇兰还认为如果一直在中国生活,她现在仍然会很年轻。勇兰在她的余生中,一直坚守着对东方世界的记忆。毫无疑问,“我”的母亲曾过着体面的生活,但搬到美洲大陆后,她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挫败感:一位中国医生竟然要靠经营一家洗衣店谋生。在美国社会的背景下,“鬼怪”在某种意义上摆脱了迷信的原意,而是指普通人,尤其是白人。隐喻白人无法接纳其他有色人种群体,拒绝接受外来的文化,而有色人种则非常努力地想要融入以白人 文化为主流的社会。因此,美国可以被比喻为“沙拉碗”,但永远不能恰当地被称为“大熔炉”。不幸的是, 勇兰成为美国这个“沙拉碗”中的一位移民,她像一名战士一样,不断地努力尝试融入当地生活,却总是在边缘徘徊。
(二)月兰的探寻与认同
姨妈月兰来到美国,是为了与母亲勇兰相见并寻找丈夫。由于月兰在中国生活多年,她注定无法适应在美国的生活,最终在这个异国他乡以悲惨结局收场。与母亲勇兰不同的是,姨妈月兰在接近暮年时才踏出国门,而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人通常很难再学习新事物。月兰可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她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说服自己迈出这一步。其中一个可能的自我安慰是,月兰将住在勇兰家里,这让她想起自己其实不必过于担心,因为她有一个意志坚强的姐姐,以及几个外甥和外甥女。更重要的是,尽 管月兰害怕见到那个多年未见、一直生活在神秘大陆的丈夫,但这个理由也激励着她做好出发的准备。然而,月兰从未意识到,异国他乡的现实和不确定的丈夫,就像一股无形的力量,足以摧毁她心中的美好幻想。
“西宫门外”是本书唯一从第一人称叙述 转变为第三人称叙述的章节。显然,“我”试图避免与姨妈月兰交谈,而且“我”肯定不是唯一一个觉得与月兰相处时无言以对、毫不自在的人。“她快把我逼疯了!孩子们用英语互相告诉对方。”不仅孩子们如此,月兰的那些奇怪的提问、疑虑和行为也让她的姐妹感到尴尬。一方面,勇兰同情她的妹妹,一再催促她与丈夫见面;但另一方面,她也认为妹妹似乎成了这个美国家庭的沉重负担。如果月兰对她 姐姐来说是一种耻辱和负担,那么她对她丈夫来说也注定是一个被排斥的人。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警告她:“你来这里是个错误。你不属于这里。你没有适应这个国家的坚忍。” 月兰最终被送进了收容所,孤独离世。
勇兰的家庭已足够包容,试图给月兰提供更多的安慰,并以友好的方式接纳妹妹。然而,月兰丈夫的冷酷无情则直接导致了月兰的异常行为。一个合理的猜测可能是,月兰典型的传统中国女性特质——保守、顺从和依赖——使她成为受害者。月兰出国时已经身处暮年了,没有人期望她能遵循美国社会的一切规范。显然,一位多年来被传统观念折磨的女性在面对异国他乡和新事物时也仅能表现出逃避情绪,月兰亦从未为进入新生活、适应新环境做出任何改变。
姨妈月兰的身份是一个依赖自我生活的中 国女性。一方面,月兰大半生都是一个人度过,与一个虚无缥缈的丈夫相隔千里。除了部分经 济支持,她几乎都是依靠自己生活。另一方面,在作为原配夫人与丈夫失望地会面后,月兰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她变得更加胆小,经 常产生危险的幻觉和不安全感,因此她的亲人们把她视为一个奇怪的中国女人。最后,她进入了一个只有自己的世界——没有人打扰她,也没有人能带她走出来。
三、第二代移民的文化身份探寻与认同
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令人欣慰的结局可能是像勇兰那样,一定程度上能够独立且幸福地生活。相比之下,月兰则展现了另一种典型情况,即无法且不愿适应新生活。对于第二代移民而言,他们的困难已从“生存问题”转变为“生活问题”。事实上,第二代移民面对的情况可能更为糟糕,因为他们甚至别无选择——生来就具有双重身份。
“第二代移民”指的是“我”和其他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孩子。通过重新撰写“无名 女子”和“花木兰”这两个中国故事,“我”逐渐意识到“我”在中国故事与美国现实之间 的探寻与认同,并开始书写“我”自己的故事。
(一)从“我”的角度解读“无名女子”
“无名女子”是从未谋面的“我”的姑姑。这个故事发生在姑姑作为淘金者妻子的身份留在中国大陆家中期间,她出轨并怀孕,这引起了村民们对其身体的攻击。最后姑姑生产,并带着刚出生的婴儿一同投井,绝望地结束了生命。从“我”姑姑的故事来看,人们严格遵守传统习俗,并剥夺了她的名字,以此作为羞 辱她的手段。
当“我”的母亲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正被教导成为一个传统的女性。也许“我”的家人曾经同情过姑姑,然而自从她 离去,由于传统价值观在第一代移民中根深蒂固,“我”的家人在讲述故事时不得不谨慎措辞,毕竟这些移民邻居将与“我”的父母在美国共度余生。相反,“我”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一丝火花,渴望加入一个全新、现代、开放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存在于“我”所处的地方,而不是去遵循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传统习俗。当“我”讲述关于移民的残酷事实时,这个故事就变成了对“我”的一种告诫。
“无名女子”的故事是对副标题“幽灵间的少女时代回忆录”的呼应。“我姨妈缠着我——她的鬼怪吸引着我,因为五十年来无人问津,只有我为她写下这些篇章。”如果“我” 没有在美国生活中受到那些关于女性的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就不会产生将姨妈描绘成鬼怪的两种猜测所带来的困惑。
(二)“我”对花木兰故事的改写
qnVnrCHeXU6TM+wH93Er3tfo3pl6+zX+Bkx5kqNvTuY=在中国读者熟悉的花木兰故事中,花木兰为替代父亲乔装成男性参军。在战场上奋战多年后凯旋,从此在家中照顾父母。在“我”的改写中,保留了替父从军、荣耀归乡和孝顺父母的情节。在以“我”为中心的花木兰故事中有几个变化:增加了幻想色彩,比如学习并掌握了一些使“我”与众不同的超自然技能;“我”的背上刻着誓言和名字;“我”没有隐瞒女性的身份。通过加入这些狂野想象,“我”跳入了这个故事,梦想着成为像花木兰一样的女勇士,来保护那些像“我”的母亲勇兰、姨妈月兰和无名姑姑这样的女性。作者将改写版本中的花木兰塑造成一个为村民复仇的领袖形象,她在军队中以女性的身份存在,但在战场上却表现得像男人一样坚强。
“我”笔下的花木兰代表着女性的独立和勇敢。作为一个美国华裔女孩,“我”将家庭 教育中的东方传统和学校教育中的西方思维结合。“我”必须不断通过区分中国故事和美国现实来调整“我”的位置,以便决定“我”在中美价值观念认同中的摇摆和思考。杨春曾指出,故事中的“我”觉得自己可能永远无法像美国本地人一样获得平等,于是将自己置于美 国社会边缘的位置。然而,“我”仍然努力为成为一名“女勇士”奋斗,为自己讲述的第二代移民的故事而感到自豪,不是用美国的方式,而是用“我”自己的方式。
四、结语
移民们不断努力探寻自己的文化身份,尽管结果可能并不令人愉快。将自己置于另一个世界并完全融入其中是一种幻想,因为肤色、语言、风俗习惯以及其他因素在移民的生活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本书来看,即使作者成年后回顾过去,在中国故事和美国现实之间做出艰难选择的记忆仍在不断延续。“我”继续分辨出哪些“只是我的童年、我的想象,只是我的家庭,只是我的村庄,只是电影,只是生活”。作者在书的开头就提出了自己文化身份的问题,但到结尾时,她仍在寻找一个合适的答案。显然,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她。总之,交织的文化身份是移民的独特标志。像勇兰一样的第一代移民从中国移居美国后,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美国特征;而像“我”一样的第二代移民,在美国成长的过程中则在某些方面呈现出中国文化特征。因此,第三种文化或双文化主义,成为探寻文化身份认同的答案。
[作者简介]尹筱艺,女,汉族,四川成都人,成都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研究实习员,硕士,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