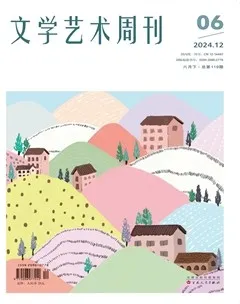黄州之月目视心寓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贬谪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大难不死后的反思、贬谪新生活的体悟、时间淘洗之后的沉思,都被他写入诗文中,心境的种种变化,更明显地反映在46篇有关月的诗文中。
一、定惠院之幽月
家眷未至的三个月时间里,45岁的苏轼刚刚逃脱大难,这时的心情,既有惊魂未定的余悸,也有高洁自我不被世俗所容的失落,而才名远播的自信是他始终不变的底色。所以,暂住定惠院期间,他有意地远离人群,夜晚、月光和此时的他格外适宜。
身陷囹圄前不久,苏轼虽然惊惧、愁郁,却也保持着可以折磨不可以屈服的傲骨,他看到栖身高槐的乌鸦,虽然巢破枝空、啄雪当饥,却眼见他的煎熬窘迫,替他哀声啼叫不忍离去,便有了“疏影挂残月”[1]。
而定惠院的缺月,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好似害怕惊扰到深夜无眠的幽居之人,只默默地从疏落梧桐之间投送淡淡的抚慰。有飞鸿的孤影隐约掠过,惊醒正来回踱步的幽人,回头寻觅,四围静悄,无人省识他的痛苦,那孤单的飞鸿也“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的沙洲、缺损的夜月、幽居的人、孤飞的鸿,都笼罩在清冷之中,却又各自坚持,互相致意。
二月的夜,还带着寒意。月亮飞上枝头,香雾缭绕,江云清媚,竹露莹洁。柳树在东风 中低头,梅花却还在凌寒独放。酒助诗兴,他 想要赞美月下的美好、莹洁和坚忍,因言获罪的过去,让他只能“清诗独吟还自和”。酒尽人醒,最是时光留不住。过去的一切让人叹惋,却已无法改变,无法挽回,也无须留恋。让人担心忧虑的,是那些欢愉的心情不能常有。平 淡的生活最踏实,苏轼回到竹篱茅舍中,在美酒中安放自己。然而,苏轼也有酒后吐露真言的时刻。还是家人的怀抱最温暖、最安全,有了家人的陪伴,世人的嘲笑和辱骂就随它去吧。
想到家人,他不由忆起:去年此刻,他还是徐州知州,和老朋友、青年学子经常“对月酣歌美清夜”,而今自己却在独自赏花。世间的变化就像花开花落,没有定期,以后的岁月,就像壶里的酒容易倾尽,又想起父亲的厚望、送父归葬时在此地的停留。那时,他是被宰相欧阳修极力推荐的国家栋梁,而今的他,除了堪比鲍照、谢灵运的诗才,连长沮、桀溺的五亩栖身之地都没有,希望是“倒吃甘蔗”——少时辛苦老景安闲吧。现在暂且安居,穿过花径、踏着月色、畅饮乡村浊酒,只要避免醉醺 醺地回去被人责骂就好。
白天,酒足饭饱之后,苏轼拄着竹杖,四处寻赏修竹。他一直都喜欢竹子:“不可居无竹……无竹令人俗……士俗不可医。”他无意间发现,定惠院东面,满山草木之中,那一株独出的海棠,在粗俗桃李之中,更显出它自然高贵的风姿、鲜艳姣丽的神采。也许是造物主的眷顾,把它安置在这幽静的山谷。密林深茂、雾绕光暗、朝阳晚照,却也使得它尽享旭日温暖、春风轻拂得以神完气足。也会有雨中饮泣的时刻,但“月下无人更清淑”。清刚淑慧的海棠本是西蜀多产,现在的沦落,就像他自己,骄傲而孤独。让他心有所感的,还有不与百花争先的酴醾,寂寞地开在暮春时节。“不妆艳已绝,无风香自远。”芬芳馥郁,清丽婉约,花里带着绝世美人的芳魂,映着微月,悠远而冷艳。
此前的诗文里,只有在初次离乡、首次离开父弟时,苏轼的笔下才出现“残月”的描写。定惠院里的幽月,是他政治劫难和伤痛心情的投射。这种隐痛一直持续到家人来后的七夕,虽然一家团圆,可是苏轼看到初升的“弯弯月”,还没等光华绽放就先忧虑它的残缺。人间夫妻恰如天上牛女,“更阑月坠星河转”,相聚如梦,梦中惊醒,依然泪零,幸福随时会被人打破,快乐也是不踏实的。
二、东坡先生的明月
定惠院寓居,长子苏迈的陪伴和对小妾朝云的思念,让月变得明亮、美好,“明月好风闲处、是人猜”“清风来无边,明月翳复吐”。
随着家人团聚、主官推崇、亲友追陪,更重要的是开荒东坡,雪堂建成,夫耕妻织,有室安身,有谷饱食,苏轼变成了东坡先生,写了很多关于记梦、唱和、写景的诗文,心境逐渐向晴,充实、安然、自在,笔下的月也变得明媚、轻快、怡人。
即使偶尔有思乡之念,但“临皋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山水。吾饮食沐浴 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1]。
心神安定,他有了自嘲和嘲笑他人的兴致,“空堂明月清且新”,他梦入神仙洞府,径直采摘品尝有着紫藤赤叶、口感像蜜藕和鸡苏的石芝。尽管会被神仙嘲笑举动轻率无礼,也胜于嵇康没有品尝稀世之珍的口福。
他也会在清风明月之夜,梦回从前在杭州的自由快乐时光;故去的友人也在他的梦里出现,闾丘显在栖霞楼饮宴宾客云集。醒后,“但空江、月明千里”,前尘如梦,恍然间已物是人非。
最让人欣喜的是他付出辛苦之后的田间巡视:庄稼长势喜人,月下的秧苗上,露珠就像珍珠。耕作如陶潜,东坡似乐天,他开始体察四季的变化,关注身边的人,体会他人的情意:迷蒙的花前月下,朝云安静弹琴,琴声激越有力。
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的月,都善解人意,“明月多情来照户,但揽取,清光长送人归去”。他对月充满怜惜之情,“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碎琼瑶”。他把明月看作知己,醉酒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对照密州中秋词,少了疏狂和乐观,多了寂寞和自在。
苏轼也会在雨雪后独自拄杖去寻幽探胜。看到雪花飘飞,云月长在,一片雪白,也会停 留一宿,观赏乌鸦喜鹊在雪后新晴时刻的欢快 飞舞,谛听屋檐雪水倾泻到柱子上的清脆声响。
面对官长的盛情款待,他会自谦“贫家何以娱客,但知抹月批风”,如同清风是大地之音,明月在大地上书写天空的容貌,诗文是他真实的心声。
心境的淡定和从容,让他或者集句为诗,或者采伯父诗句为韵作诗,或者在织锦图上题写回文诗,或者改写陶渊明、欧阳修的作品为长短句。这里的月,也是娟娟可爱,即使“夜凉低月半枯桐”“残雪消迟月出早”“香雾空蒙月转廊”,他也不再有初到黄州时的凄怆。
三、闲人的圆月、江月、欣月、皓月
元丰六年(1083)的月,明亮、沉静、从 容、涵容。
赤壁七月半,圆月临空,清风拂面,江水平静,苏轼对酒当歌,吟诵《陈风 ·月出》。而吹箫之客由明月、诗歌、赤壁想到当年的曹操和周瑜,当年英雄一世,而今已化为历史陈迹,哀叹人生渺小而短暂,想要“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终是奢望。苏轼从水和月的变与不变加以引申,得出结论:从运动的观点来看,自然万物的变化和人类的代谢更新,都是无穷无尽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人不能占有自然的一切,但可以去体验和感受。
当然,赤壁之战时的周瑜也让他伤感:对比周瑜的青春得意,家庭事业幸福美满,自己痛失爱妻,中年被贬政治失意。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1],故人今人终将被历史大浪淘尽,人生若梦短暂而虚幻。但“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2],只有江水江月,涌动而永恒,贯通古今,可以让他以杯酒怀念古人。
十月十二日,入户的月,唤起了苏轼的游兴。身边许多人,全都“无与为乐”[3],此刻他只想去找住在承天寺里的张怀民。“亦未寝”三字背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二人同行,无须言语。这夜的月,分外透明,竹柏映在月下的疏影,浑若水中纵横的藻荇。知音相伴,一切都是美景。个人独处时看重的明月、修竹、松柏,都显得无足轻重。拥有同样的贬谪经历、被排斥出政治领域处境的两个人,反而“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能够身闲心安,领略生活的真谛。
十月十五日,月圆之夜与客再游赤壁,奇险之处一人独探,他在山顶长啸,山水的巨大回应让他也心生悲惧,“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下阕用与“横江东来”之孤鹤化身的道士的对话,抒发他此次赤壁之行的感悟。结合《和刘道原见寄》“独鹤不须惊 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之句以及“飞鸿雪泥”之语,可知他此时的思想:高绝而自由的境界伴随着孤独,但是值得去追寻。
于是,有了《满庭芳》的潇洒和轻松:不值得为名利奔忙,有限的人生,更应该尽兴、疏狂,沉醉在人生的每一天。那些朋党之争、政治是非都不必放在心上,“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人应当保持心灵的独立、思想的自由,去享受美好的自然。黄州之月的不同情状、不同质地、不同性情,见证着苏轼的蜕变和成 长。
[作者简介]刘莲英,女,汉族,河南周口人,渤海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与古代文化。
[1]出自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本文所引苏轼诗、词、文章均出自此集,不再重复注释。
[1]出自(宋)苏轼撰,王松龄点校《东坡志林》,中华书局出版。
[1]出自(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2]出自(清)彭定求等编,陈尚君补辑《全唐诗》(增订重印本),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
[3]出自(宋)苏轼撰,王松龄点校《东坡志林》,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