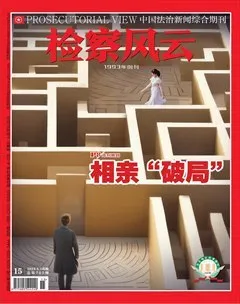“过后辄翻异”的另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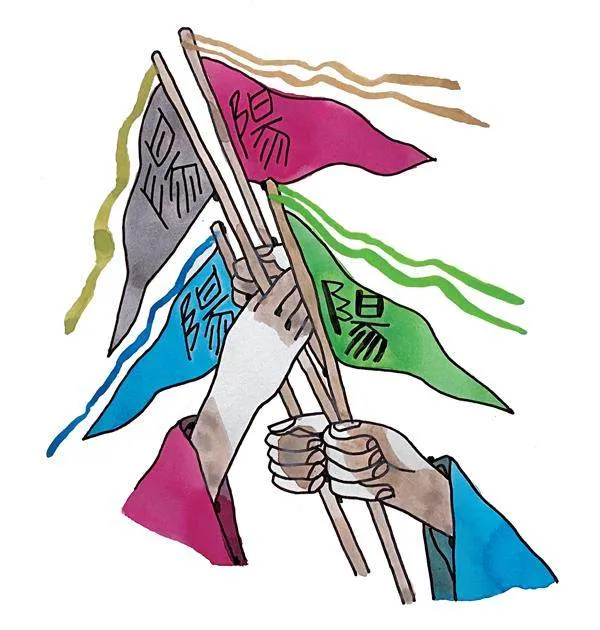
执行的重要性人所共知,但如何执行却历来需要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世说新语·政事第三》中有个故事,颇具启示意义:
东晋时,太尉陆玩每次到丞相王导那里商询事务,“过后辄翻异”。王导“怪其如此”,一次特问陆玩。陆玩回答说:“公长民短,临时不知所言,既后觉其不可耳。”说的就是:您的地位高,我的地位低,议事之时我不知说什么好,但事后发现不能这样去做。
故事写到这里,刘义庆先生没有再写下文。显而易见,经陆玩这样一解释,王丞相认可了,至少没有发火生气。正是这一“认可”,故事才有了另一面的看点:要让下级有效执行,而不是表面上虚应故事,要义在上级给予宽容,以便下级轻装上阵、放开手脚干事。也就是说,下级敢于作为,源自上级的信任。这是一个双向互动,也是一个被若干实践证明了的成事之道。

这里的道理不难思量:任何一级领导指示,任何一项商询计划,都带有主观上的想定性,进入生动的具体实践,很多时候难免客观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觉其不可耳”。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盲目地执行上级指示,看起来好像是认真得很、忠诚得很,实际上却如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所批评的——“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因为,这样执行的结果,往往导致上级指示和原计划“跑偏”“变味”,难以真正有益于大业。这就启示人们,正确地执行上级指示或是事先商询好的计划,需要勇于和善于从实际出发,包括“过后辄翻异”。
然而,在教条主义盛行的干事生态中,“书呆子”式地搞“本本主义”容易,“觉其不可耳”勇于“翻异”以真正“求实”则难。难在哪里?难就难在敢不敢于从实际出发,是否害怕领导“怪其如此”。所以,这当中缺乏“心底无私”的担当精神便不敢造次,没有一个“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品格便做不到。
古时候,湖南道州出产侏儒,自隋炀帝登基时始,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若干人到宫中当太监,以供皇帝作优伶戏弄取乐。唐德宗年间,阳城就任道州刺史,他关注民生,怜悯侏儒家庭生离死别,拒绝再进贡侏儒。朝廷派人去要,阳城呈上奏章,写道:“州民尽短,若以贡不知何者可贡。”坚决要求罢黜此弊政。同样幸运的是,德宗皇帝竟然同意了他的上奏。此举大得民心,道州城里欢声雷动。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阳城的功德,当时道州百姓生男孩皆以“阳”为字,并立祠祭拜,同时将当时的主街改名为“阳城街”,永志纪念。作为一个古代官吏,竟有这等为民情怀和敢于“违例”的胆识,实属难能可贵,因而这一故事在新旧唐书中均有记载。
不过,就进贡侏儒这项弊政最终被废除而论,唐德宗的准许乃为至要和关键。否则,一个阳城不愿意进贡,朝廷大可再派一个愿意进贡的人去干刺史。从这个角度而言,道州百姓在感恩阳城敢于担当扛事的同时,似乎亦应给唐德宗的宽容点一个“赞”。
无论古今,对上级决定或交办的事情,下级按要求和成例执行总是无虞的。而陆玩、阳城之为,显然是因为他们怀揣的是一种从实际出发,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对上负责”。站在其上级那一面考量,这等“翻异”和“违例”,最终得以“无虞”,个中所闪现的无疑是一种“宽容”和“开明”。故而,故事在鼓励和支持求实上都闪耀着“些许亮光”。
图:王俭" " 编辑:黄灵" "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