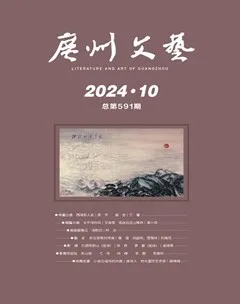父子之间
西北的一个小县城,城郊的八盘磨是我们的家。门前一条水渠叫二道渠,平日水流细小,隔上十天八天涨水,颜色又红又绿的,味道刺鼻难闻。人们像是习惯了,那是上游的毛纺厂在排水。奇怪的是,突突的水流里,有时候竟然携带下来了破箱板、烂棉絮和死猪,虽然没一样值得打捞,也让河边看热闹的人兴奋。
水渠又一次涨水那天,父亲一把抢过我正在看的一本书,使劲撕成两半,呼一下扔进了水渠。父亲的动作太突然,我没有防备,手里一下子空了才反应过来。我顺着水渠追,这怎么追得上。眼看着那本书在水里翻腾了几下,沉入水中,被冲远了,一点踪影也没有了,消失了。
那是一本《水浒传》,是我跟同学借的。
这拿什么还呀,我愁得不行。
而父亲的愤怒,似乎还没有消散,这又让我很是害怕。
我害怕挨打。父亲打我,都是在我晚上睡下后,猛一下揭开被窝,挥着木条打屁股,打腿,打得可疼了。什么时候不打我的,应该是我高中毕业前夕。有一次我在外面和人打架,把对方头打破,大人找上门,手指指着发了一通火。说好话把人劝走,父亲怒气未消,等不到天黑就要动手。情急之下,我拦腰把父亲箍住,父亲动都动不了。我立刻松开手,父亲愣在原地,没有再打我。这以后,也没有再打我。
一直是这样,我要是做作业,父亲如果忙完了,就在一旁看着,神情是喜欢的。我要是读课本,父亲有时候停下手里的活计,侧耳听一阵,听得很认真。
可我看闲书,父亲是不允许的。而且,在这之前,已经进行过口头警告,我竟然沉浸在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情节中,没有把书收起来。这就严重了。这是挑战父亲的权威。
我上学那阵子,小学到中学,在20世纪70年代。课本就那么几本,似乎也够了。不过,有的学生,会拿着小人书看,拿着小说看。这是凭兴趣看的,看着自然也是过瘾的。
课外活动倒是经常组织。还走出校园,跨过泾河,到马家庄的一个山顶上住了一星期。土沟里头坡度大,两边是峭壁,一条土路蜿蜒向上,仰着头看不到最上边。坡顶上相对平坦一些,不过也是高低不平,地形破碎,种粮食没啥收成,村子里让了出来,交给学校来管理。学校给起了一个有意义的名字:育苗沟。学生毕业前,都得来一次,来接受实践教育。我们班全都来了,男女生分开,各在坡顶一头,男生住窑洞,中间隔了一个缓坡,女生住平房。食堂在女生住的平房那边。我们上山的任务主要是种树,种的是松树苗。一些松树苗长高了,翠绿翠绿的,那是之前过来的学生种下的。来到这里,对我是新鲜的、高兴的。父亲一听要交钱,起先不同意,了解到没有商量余地,就只好让我妈准备铺盖和脸盆,准备吃饭用的碗筷。
在山里,清闲时间还是有的,已经读高中了,就有些不老实,对于住在平房的女生,我们是最关心的。她们晚上出来上厕所,会不会害怕?睡下后,她们很快就睡着了,还是跟我们一样,也要说一阵悄悄话?我们会说起女生,那么,女生会说起男生吗?也就这么想想,也就这么说说。那个年纪的意识,药水一样有点苦,有点甜。
我那个年纪,有一个严厉的父亲,能做出什么出格的行为呢?读课文觉得枯燥单调,迷恋上了小说。日子枯燥又单调,在文字的世界里,能结识和我一样不一样的人,我不那么心慌了。知道谁有书,送出去过一把小刀,一张下满蚕蛋的麻纸,书借来了得抓紧看,都是限定了时间的,看了还回去,下一次再借就容易了。可是,在父亲眼里,除了课本,别的书就是闲书,不属于正道。父亲认为,念书念书,就是把课本念好。看闲书,万一学坏了咋办。我估摸还有一个原因,父亲看我抱着小说看,还一个人傻笑,还使劲拍大腿,也担心我脑子出问题,会成为家里的负担。
父亲是木匠,父亲是文盲。一个文盲能不能成为一个木匠,这个其实已经有了答案。而且,还可以进一步证明,能够成为一个好木匠。家用的各种,用来制瓦制砖的模具,都得到了认可,有一定的名声。从我记事起,就有人从乡下进城,四处打听着,上门联系制瓦制砖模具的业务。记得有一次,一个穿黑棉袄的人,拿着用坏了的制瓦制砖模具找父亲,希望给修理一下。那副模具看着很有些年头了,颜色发黑,有些木条已经破损和残缺,我觉着扔了也不可惜。父亲拿手里端详了一番,还是答应了。那个年月,都困难,那个人又觉得求人不能空手,神情上是诚恳的,还从怀里掏出四颗水果硬糖,放到了椅子旁的柜面上。
木工活,一样一样,没有一样不过手的。选料,配料,加工,组装,上漆,都得从手底下出来。经常是,我半夜醒来,灯还亮着,父亲还在做活。钉钉子,合铆,父亲就像啄木鸟在敲打一棵树。天亮了,地上堆着一堆锯末,散落着一卷一卷蓬松的刨花。父亲白天还要出去,在白沙石滩的黑市上选木头,去城门坡的五金店买钉子,到新民路的寄卖店看制瓦制砖的模具卖出去没有。父亲像是不瞌睡,像是不用睡觉。可是,我眼看着父亲坐在椅子上说话,说着说着就坐着睡着了,一会儿,身子闪一下身子定一下,又醒来了。
木工活这么辛苦,父亲的手艺又有自己的特别之处,尤其是制瓦制砖模具的制作,不是所有木匠都能做,都能做到质量上乘,在小县城里,父亲是独一份。按照木匠这个行业的传统,也为了绝活不失传,把手艺传给几个儿子,父亲也能轻松,还能增加家里的收入。可是,从我哥,到我,到两个弟弟,我们兄弟四个,都没有把父亲的手艺继承下来。这也是我疑惑不解的:父亲出于什么考虑,不让我们成为木匠呢?
要说父亲心疼儿子,不让受这份苦,那是不确切的。不给我们教授,儿子能出力了,还是要当个人用的。一些没啥技术含量的工作,我们都没有少干。一个是给木板刨光,得用好几种刨子。第一步粗刨,我能承担。接下来的细刨,薄厚上不能差池,我完成不了,父亲自己上手。另一个是锯木头,把一根圆木,或者一块木方,固定在门框上,我和我哥,一人一头,对准父亲在上面画出来的墨线,锯子拉过来拉过去,锯齿吃掉一条线,再吃另一条线,整体的木头就分解成了一块一块的木板。这个要配合,用力得一致,锯上几次,也就熟练了。再一个是拧绳子,家里有一台拧绳子的简易机器,拧绳子要靠人力转动,才能把麻丝一股一股拧到一起,拧出松紧合适的绳子。我咯吱吱、咯吱吱转动一个手柄,让绳子一点一点吃上力气。这个要掌握力道,还得快慢有度,我不光能领会,还能操作到位。
即便如此,也只是在放学后,在星期天,像是帮忙那样,干上几样子。如果我写作业,背课文,父亲就自己在忙活。
父亲在劳动,我在一边看小说,父亲看不顺眼,那是合乎情理的。把一本小说扔进河里算什么,我的理由再有理,也大不过父亲的理由。我对父亲有意见,那也只能藏在心里,不能流露出来。我就盼望自己早些长大,有一份工作,能给家里挣钱,那我就硬气了。买猪肉一买半扇子,买西瓜买整个的,还要叫上一家人出去吃饭,去吃春华楼的泡馍。到了那一天,父亲就不会干涉我看书了。
那一天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对于自己的未来,我其实也是懵懂的、不踏实的。
除了借书,县城的新华书店我经常去,营业员都认识我了,知道我每次都是只看不买。有的书我想拥有,又没有钱,我就想办法。这个办法,现在想起来我都脸红、愧疚。过去人得病哪里不舒服了,轻易不上医院。家里常备的药有四环素和安乃近,吃完了父亲会给钱叫我去买。我偷着把这两种药藏起来,一次藏一点,藏到一定的量,父亲再叫我去买。我假装从药店买回来了,担心父亲发现,父亲没有发现。我用买药的钱,买了一本《安徒生童话》,那是我读了许多遍的一本书。
我喜欢看书,在那个岁月,那可是奢侈的。家里吃饭都紧张,哪来的宽裕满足我的愿望,有一就有二,这个头不能开。除了看书,我竟然喜欢上了画画,这一下又惹上麻烦了。置办颜料、画笔和画板,我知道是不可能的。我只是照着报纸上的,画片上的,用铅笔在纸上画素描,画了许多人头、树木、牛羊、房子。我姐已经出嫁,回来看到我画的画,给予了肯定,还把一个绘画老师带到家里,希望父亲同意,指导我画画。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老师来了,让座,倒茶,坐下说话。一开始,气氛还是融洽的,我坐在一旁,默默听大人说话。那位老师,对我画下的画,做了点评,认为缺少基础训练,画得随意,不过能看出一些苗头,有培养的潜力。这就得家里给创造一些条件,好好画上几年,说不准会有出息的。老师说到这里,父亲说,念书都念不好,倒想着画画,能当饭吃吗?父亲这么一说,我学画画是没指望了。
有饭吃,在任何时代,在所有领域,都是绝对真理。在我们家,父亲让我们有饭吃,父亲说了算。
我们在成长,父亲的腰弯下去了,额头上堆满皱纹,尤其是那双手,显得很大,指关节很粗,手掌粗砂纸一样。我的印象里,父亲一辈子都在劳动,都闲不下来。父亲是为儿女活着,为这个家活着。我没有听到父亲说过一句抱怨,就是背着大石头,也要一直背在脊背上。
让几个儿子成为木匠,父亲没有这样计划,没有这样安排我们的未来。父亲教,我们学,尽早成器,给家里也是一份贡献。都是吃饭的嘴,一个月下来,得消耗多少粮食啊。可是,父亲连提也没有提过。
难道念书能让我们走出另一条路,而改变人生吗?那时候高考还没有恢复,我的哥哥、姐姐,高中毕业,都是下乡插队,在知青点熬日子,盼着早点回城,能安排一个工作。我念到高中,能参加高考了,可是,我数理化一样都不过关,就是作文写得流畅。第一次上考场,自我感觉就不佳,自然败下阵来。我的弟弟也是没考上。那时候,家里出一个大学生,该有多荣耀啊。
我姐我哥回城后,左等右等不见安排工作,还是父亲找关系,得以在县城最好的工厂上班。那时,我也即将高中毕业,很羡慕。我高考没考上,自己不死心,父亲支持我复读,等于在家里多吃了一年饭。第二次落榜,我彻底放弃努力,反而又得到解脱的轻松。当时的形势,在县城找工作已经没有可能,只得选择在外地上技校,毕业后在大山里搬铁疙瘩。吃下的苦,遭下的罪,说不成,不能说。我那时给自己定了一条,给家里写信,只说好的,遇到任何挫折,都只字不提,不让父母为我担忧。发了工资,一定给家里寄钱。月月上邮局,一月一张汇款单,我未曾中断过,直到父母去世才停止。
谁又会想到,我姐我哥那么红火的厂子,20世纪90年代,一天天沦落,常常几个月不发工资。而我喜爱文学,工余写点小文章,竟然被单位重视,进入机关,后来又跟随总部搬迁,进入大城市生活。这算不算造化弄人,这是不是命运的翻转?但这绝不是个人能够预测和规划的。我在野外队的时候,自己都看低自己,探亲假回家,不愿意出门,怕遇见同学,问起来不知道咋说,说了担心被笑话。等到我的日子过得好了一些,父亲高兴,坐长途班车,到我这里来过几次。有一年要来,我安顿妻子,也学习单位上接待重要客人的做法,列出了菜单,每顿几个菜,什么菜,都写在纸上,提前念给父亲听,一一征求父亲意见。让父亲觉得,不光在心意上,在仪式上,我也是重视的。
看着父亲的模样,我有些酸楚。父亲老了,也慈祥了。吃吃不动,跟我说话也客客气气的。在我小时候,父亲难得有好脸色,发起火来没有人敢靠前。人老了,怎么就变了呢?
20世纪40年代,父亲在老家当学徒。出师后,只身来到这个小城。先是给老板打工,挣一份工钱。舍不得花用,有了积累,开了一间自己的铺子。木盆、木桶、搓板、风箱、案板、大小家具,价格低还耐用,渐渐打开局面,还收了三个学徒。得空抱茶壶喝茶,皮袍子都置办下了。经人介绍,成了家,住在中山桥,也是县城的繁华地段。那是父亲最风光的岁月。母亲说过,刚结婚那阵子,父亲给她买过金手镯、金项链、金耳环好几对。后来日子难过,都要回去,换成钱,换成粮食了。原来居住在城中心的房子,也承担不起上涨的租金,搬到了偏远的八盘磨。父亲的铺子,本来还能够再扩大,却在后来的公私合营中失去了主导,一气之下退出,放弃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我分析原因,父亲不识字,适应不了那样的环境,应该是重要因素。由此我认为,父亲供我们念书不中断,与这个经历也有一定关系。
父亲曾是单干户,这在当时是有风险的。有一天,街上的一面墙上,不知谁贴了一张举报信,姐姐看了一眼,吓得跑回家报信。举报信的内容,竟然是揭露父亲在家干私活。在第三天还是第四天,那张举报信被风吹开一角,哗哗响着,有可能掉落,要是被怀疑是我们家里人撕开的,肯定会招惹麻烦,父亲趁夜里没有人,提着平时黏合木头的胶罐,拿着刷子,把揭露自己的举报信,给仔细粘贴好,才松了一口气。城里头被盯着无法揽活,就拿着家当,出城到偏远的山区上门加工,一出去几个月,一出去半年。自己干,由于限制多,手脚施展不开,收入抵不上支出,眼看维持不下去了,父亲另想门路,在一个厂子里,应聘为八级工。工资高,一个人顶几个人的,却一直是临时工身份。早先倒是能转正,不过级别就下来了。人不可能两头都占,权衡利弊,父亲又不愿意放弃,就一年年维持着。许多年过去,年纪大了,遇到清退,父亲的学徒都当厂长了,也是帮不上忙。父亲净身回家,这下啥都没有了,没有医保,没有退休金,彻底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
磕磕绊绊,上面又允许个体户存在了,靠劳动挣钱,也没有人来干涉了,有一阶段好像还大力提倡,父亲却干不动了。塑料制品、铝制品大量出现,许多沿用多年的器物,渐渐失去了市场。本来大受欢迎的纯木家具,也由于三合板的应用、贴纸的组合家具的流行,而变得无人问津。制瓦制砖的模具,有了替代的机器,也卖不出去了。只是儿女在长大,参加工作的收入微薄,在家里的啥都不会,饭量增加了,却不能创造财富,家里的日子变得更加艰难。
世上的路,咋走都走不通是不可能的。不过,在有的人那里,不能走的,能走的都走了一遍,除了感叹和认命,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兄弟几个长大,面对社会变化,也曾埋怨过父亲。埋怨什么呢?在个体户发财的时候,埋怨父亲不让我们学木匠手艺;能自主发展了,没办法自己干,埋怨父亲离开公私合营的企业,失去了一份产业;在工作难找,没有出路的时候,埋怨父亲在一个厂子里干了那么多年,为什么不转正,导致我们无法享受内部政策招工或者顶替。父亲只是默默看着我们,不知道咋说,就啥也不说。
记得有一年,父亲叫上我,去城外要账,我才知道,父亲许多年前在这些地方给人家做木工活,许多都没有收到工钱,一直欠着。一次是夏天,坐班车去土谷堆,下车后走山路,在一个分布着四五户人家的山谷,一户一户走动,听见声音出来查看,见了父亲都很吃惊。水喝了,也不说不给,每一家都是说手头紧巴,一时拿不出来。一次去四十里铺,大冬天,刚下过雪,大清早出发,路上有冰溜子,天色蓝得吓人。我骑自行车,父亲坐后座,骑了有一个钟头还是两个钟头,到一个村庄,拐进一个庄院,到了一个老头家里。老头正在洗脸,丢下毛巾,互相问候着,在炕上就坐下了。也是话少,客气,也是讲日子不宽展。两次出去要账,一分钱也没有要上。在一个地方,得到了半口袋玉米;一个地方,得到了半口袋豆面。
父亲上了年纪,儿女长大了。一大家子人光是吃穿的开支,就是一大项,电费都交不起了,晚上又点起了煤油灯。父亲承受着压力,动辄就发脾气。我哥上班的厂子,生产电子管,那年月电视刚兴起,厂子也生产组装,还折价给职工卖。我哥抱回来一台,全家高兴,父亲不高兴。开电视,嫌费电,这是其一,我哥手里在削木头,眼睛在瞄电视,出活慢,也显得不用心。父亲竟然把电视插销拔了,把电视机搬出来,丢到了柴火堆。一连许多天,电视没人敢开,成了摆设。
父亲吃过没文化的亏,我知道的有两件事情。一个是父亲干不动木工活,有人介绍在一个单位看大门,但有一个工作内容,要收发报纸。这个父亲无法完成,只好放弃。一个是最小的弟弟没考上高中,牵扯到就业,那时候找工作已经找不下了,不过初中毕业的还能当兵。父亲为了保险,竟然听别人鼓动,花了许多钱,把弟弟的初中毕业证拿去叫人涂改成高中毕业证,结果报名时被识破,取消了资格。弟弟只能外出打工,去银川,去深圳,晃荡了许多年回来,除了个子又长高了一些,啥都没有落下。弟弟抱怨,酗酒,似乎是父亲害了他。其实,就是当上兵,回来安排工作,也没有像样的单位,那些和弟弟同一年当了兵的,后来都下岗了。也正是这个原因,虽然不明说,父亲也后悔,觉得亏欠弟弟。父亲得大病,咽气的时候,弟弟跑得不见个人影,父亲不停叫着的,是弟弟的小名。
许多年后,父亲为什么没有让我们当木匠,没有走他的路,我似乎找到了答案。我猜测,父亲没文化,并不意味着没见识,他是从自己早先的经历中,获得了一个重要启示:有时候,一个人本事再大,即便折腾出一份产业,也是白忙一场。另外,父亲也从自己后来的不容易中,进一步坚定了想法,那就是不让儿子困于一门手艺,不光不稳定,还会陷入绝境。必须换一种方式生存,那就是走向社会,在更大的天地寻找生路,起码也是融入一个集体之中,过得好过不好,也比一个人挣扎,一个人四处碰壁强。把父亲的经历和时代联系起来看,我只能说,父亲是对的。
几十年过去了,二道渠早就被填平,毛纺厂也不知是倒闭了还是转产了。唯有我们家的房子还在原地,原来是公家的,也是兄弟几个都出力,按照政策买了下来,又进行了翻修,比以前宽敞,比以前结实牢固了。门前以前是土路,也硬化成了水泥路,周边盖起了高楼,火车站修建在更远的泾河滩。我回老家坐火车,一路哐当,省了不少时间。我严厉的父亲,去世几十年了,埋在南山的坟地里,母亲没有享多少儿女的福,也病故了。我每年回去,兄弟几个一起去给父母上坟。南山也有了变化,一条高速路横穿过去,原来的庄稼地,有一大块流转给了一个老板,种植了药材。站在南山上望过去,县城的景象,像是老样子,又认不出来了。
责任编辑:卢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