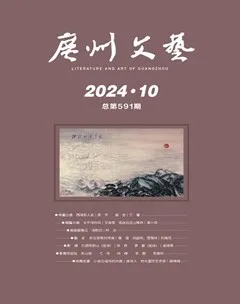时光里的艺术馆
鸽群轻盈掠过红砂岩围墙,在微凉的秋意中,划出一片怡然自得……
自白云山葱郁林海深处悠然南行,步至麓湖滨畔,红白辉映的建筑巍然矗立于碧水一侧。1995年,这里还是一片空地,没人能想到它将来的辉煌,即便是设计师——莫伯治院士也未曾预见。
在广东,人们习惯地称呼莫院士为莫伯,说他的作品是“岭南建筑之光”。当他带领事务所在六个方案中杀出重围,着手设计这座场馆时,已是耄耋。
当时,这个场馆的建设地块凹凸不平还有不少的落差,上方还计划建设高架路。这就相当于,要在一块坑坑洼洼的地面上与一条高架路底下建一处艺术场馆。向外要具备全球化的格局,向里需寻得岭南的地方特色,最后还要以良好的交通环境适应大众所需。面对这个情况,莫伯想出一个几近完美的方案:略调用地避开高架,舍弃惯用的中轴线设计,用连廊连接各个风格迥异的展馆,建造中庭和前庭,打造一个开放、自然的空间系列。
于是,这栋建筑有了一个宽阔的前庭。“湖光山色入画来”,麓湖公园的青青草坪与场馆门前的广场连成一片,绿色蔓延的尽头绽放出一朵红白相间的花,绚丽多彩,宁静明快。它一面融入北边的绿水青山,一面紧贴南边的烟火高楼。既有新兴的艺术形态,又有古意的文化传承。
站在广场上远观,场馆左侧的文塔像一个“羊”字,又像是“丰”字,应是作为羊城的点题。由文塔向南看去,一整面巨大高耸的红砂岩墙上,刻着各种浮雕文图,那是几千年前最古老的岭南先民们的图腾。是海洋文化,还是鸟神传说,不得而知。但在这奇异的共振中,千年沧桑轮换中不变的底蕴由此荡漾开来。从文塔向北,来到场馆的入口。庄重气派的三对华贵硬木雕花门扇,巍然敞开,典雅端正。
步入厅堂,门厅高旷而明亮,光线自四面八方洒落。大厅中间耸立着高大的红砂岩质地的柱子,柱顶细部雕琢着祥云图案。头顶的半圆形玻璃天棚上,蓝天白云如画。
步入典藏作品展馆,众多文艺大家的珍贵墨宝映入眼帘,它们讲述着中国历史发展的往事,一笔一画仿佛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不朽的精神气。“为国难写真”的口号从宗师高剑父呼起,赓续数代。他的高徒众多,关山月就是其中一位。关老创作的抗战画作以笔代伐,《从城市撤退》《三灶岛外所见》唤醒英雄沉梦。逾半个世纪,关山月都执教于广州,培养出了陈金章、林墉、史正学、吴泽浩等三代岭南画派传人。赵朴初圆融佛教于爱国救济,廖冰兄用漫画宣传抗日工作,还有钱君匋的篆刻、王肇民的水彩、黎雄才的“黎家山水”……数不尽的名人,看不尽的华美大作。大师们以薪火相传的热情和执着,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倾注了心血。
世纪之交,这座艺术殿堂带着融入世界格局的决心,从大地上生长起来。这座不规则的场馆突破了正统的建筑形式,不拘一格。各场馆及连廊多种多样,周围的建筑物高度不一,屋顶及檐口也是各式各样、层次分明,不论横看侧看,都别具视觉上的落差之美。在这里,远古岩画、彩色琉璃、荷兰抽象画、山墙、中式山水和罗马宫廷,众多艺术与文化元素相遇交织,令人目不暇接,沉醉其中。现代的、民族的、传统的、地域的,多样文化风貌交会于此,碰撞出奇异而绚丽的花火,点亮了每一个角落。
穿过连廊来到内庭,阳光哗的一声倾泻在我的身上,恍惚间我在和煦的阳光下穿越风格特异的园林。假山雕塑奇石罗列,赵朴初先生题写的“艺苑”二字篆刻在一块巨石上。一旁的横石上刻着一句诗:“坐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I still quietly and become a beautiful scenery)”。漫步在绿荫花径之间,只听得流水潺潺。庭院的地面上蜿蜒着“八”字形水面,一位美丽的女子含笑坐卧于水景中央,身上的披帛高扬飘荡,在微波荡漾中,我好似感到一阵风拂过。“自在”!——名如其是,梁明诚先生应该是感受到了这里开放的文艺气息,于是有了这座铸铜的《自在》。围绕水塘一圈的是十二根红砂岩廊柱,上面镶嵌着十二个既古典又现代的少女雕像。少女们面容姣好,婀娜多姿,被称为“十二花神”,据说是象征着一年中的十二番风信。水池中倒映着花神们美好的身影。花神、水池和倒影,构成一幅和谐匀称的画面。这个设计似乎受了罗马宫廷建筑的启发。我身边两位来自上海的游客轻声交流:“看看看,连着那尊雕塑和它背后的白色雕塑一起看,像不像古罗马建筑?”
走到庭院中间,一圈灌木掩盖之中,有一条石头阶梯直通而下,原来花园下面还沉陷了一个庭院。拾级而下,来到了假山瀑布庭院。这是内庭中心利用原有地形高差形成的一个秘密花园,并由此通向设于地面下层的综合展厅。花园的池塘里,肥盈的锦鲤自在潜游。峭岩上茂密的藤蔓舒展下垂,形成了立体的、多层次的、深浅不一的绿。想起黄永玉老先生在他的《南华叠翠》中写到的画面:“绿得那么啰嗦,绿得那么重复,绿得喘不过气,绿得让人像喝醉了酒。”地面的十二花神主景与沉陷的庭园,组合成了交叠错落、园中有园的景致,人在景中,动静相生。
“一座与岭南园林融为一体的当代建筑”,这像是艺术中心的广告语,不过这句“广告”的确货真价实。围绕内庭的四层场馆透过连廊的大扇玻璃,处处可俯视高低错落的内庭。走在长廊上,层层叠叠的圆形拱窗让自然光尽可能地进入建筑内部。空间交叠,色块交织,相映相生,人也变得无拘无束起来。在这个时空里,山林,碧湖,庭院,楼台,室内室外互相延展,从视觉到精神,有一种徜徉的自由散发出来。
一步一景,充满惊喜。复兴之路、民间艺术、粤剧面谱、“故宫”数字展、雕塑展、动漫展、国潮展、陈金章美术展、魔术展……若是看得再细致点,一整天肯定逛不完。走进“复兴之路”展馆,一部波澜壮阔的广州文艺长卷缓缓展开。在文学创作、摄影记录、电影制作等领域,广州的文艺家们领风气之先,以独具意义的作品,打开大国之路。岭南画派折衷中西,广东音乐创新发展,粤剧走向海外,《虾球传》《三家巷》出版。思想先声,推动时代的变革;文艺实践,通达古今之变化。一帧帧一幅幅一章章,我看到了大师风采里信念的传承。
拐进“故宫”数字展,便进入了无限延伸的空间,突破时间的桎梏,与古人梦幻联动,每一处都让我深深体验着“虚静”与“空灵”的意境,肆意抒情,悠然写意。
沉浸于一砖一故事、一瓦一传奇,感受着缤纷与鲜活。
成群的白鸽从中庭上空的夕阳里掠过,像一串跳动的音符,拨动了暮色诗意的乐章。场馆在夕阳下氤氲着暖调的线条与色块,微风过处,水塘散落一地碎金。时间徐徐地走着,淡墨色就一点点追着金色的余晖晕染开来。可就在这荏苒的须臾间,似乎又漫长得仿佛跨越了永恒。这浪漫的错觉,是红白间藏着的数不尽的岭南韵味和千年的底蕴。
责任编辑:梁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