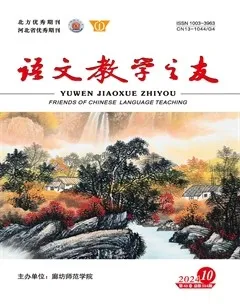“挑战性教学”:语文师范生如何学习和讲授现代诗
摘要:长期以来,很多师范生虽然热爱诗歌,却不喜欢学习和讲授诗歌,尤其是现代诗。诗歌学习误区使师范生无法准确理解诗歌的主旨,无法感受诗歌的意境美、文字美,更难以用专业的语言传达诗歌之美。将“挑战性教学”引入现当代文学课堂,教师适度介入,将自由思考时间还给学生,最大程度激发学生作为诗歌赏析主体的身份,祛除“诗歌恐惧”,让诗歌学习真正发生。
关键词:诗歌教学;语文师范生;美育
在追踪语文师范生顶岗实习过程中,笔者发现有很多学生会直接从网上拷贝现成的教学案例,从教学构思到课堂实践皆如此。其中,尤以现代诗教学的“复制”现象最突出。这些师范生其实在学习阶段就已普遍呈现对现代诗的无感、排斥甚至是恐惧情绪。出现上述现象当然与抒情性文学作品自身的理解难度有关。诗歌赏析本来就是小众且有门槛的,即使在高校,诗歌研究者占比也相对较低。但对于作为中小学语文教师储备力量的师范生来说,这一问题必须被正视且应谋划解决。在倡导构建大中小幼衔接的美育课程体系视域中,现代诗教学是与文学美育和汉字美育相关的重要部分。关注语文师范生的诗歌学习,最终导向的是对储备语文教师美学核心素养的培育。
与此同时,尝试纠正师范生实习过程中的“复制”现象,是对强调传承、创新与发展的新文科建设路径的遵循。守成固然重要,但失去创新、走向模式化的人文社科教育教学,最终收获的将是千篇一律的师范生和千篇一律的语文思维,无“创”可言,何以谈“新”。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把教育分为师徒制、课程制(经院式)和苏格拉底式三类,当下的语文教学已将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式、讨论式课堂广泛引入师徒制和课程制教学中。对于文科教育中一度强调接受性学习而提出的“挑战性学习”来说,其本质与“苏格拉底式”课堂相通的地方是通过挑战性任务的设定,激发学生主动求学和提问,引导学生寻找方法自主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真正占据中心,成为学习主体,教师也并未舍弃主导地位,在兴奋活跃、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中,学生心智被充分调动,无论是理解、记忆、运用,都会事半功倍。鉴于语文师范生作为学习者和教育者的“双主体”身份,这里将“挑战性学习”置换为“挑战性教学”,尝试在耳濡目染中使未来的语文教师习得一种可能更有成效的现代诗教学方法。
一、“学生讲”与“教师讲”
为突出师范类院校文学课堂的“师范”属性,笔者制定《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大纲时,有意识地将教学内容向中小学语文教材选篇倾斜,尤其在关于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等诗人诗作的讲授过程中,采用同课异构的方式,尝试探索不同学段诗歌学习的有效衔接。基于师范生培养目标,笔者坚持将课堂分为“学生讲”和“教师讲”两部分,即先由学生自行讲解自己熟悉的作家作品后,教师补充该作家其他代表作品,并设置相关问题,由学生自主分析解决。如在讲授戴望舒时,学生讲解完熟悉的《雨巷》一诗后,教师再介绍戴望舒的另一首代表作《我的记忆》,引导学生比较作者在两首诗作中对“大革命”失败后彷徨情绪的不同表达。多数师范生更喜欢“雨巷”和“丁香”所传递的意境美,而当阅读到如下诗句时:“我的记忆是忠实于我的/忠实甚于我最好的友人//它生存在燃着的烟卷上/它生存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它生存在破旧的粉盒上/它生存在颓垣的木莓上/它生存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在撕碎的往日的诗稿上,在压干的花片上/在凄暗的灯上,在平静的水上/在一切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东西上/它在到处生存着,像我在这世界一样”,不少师范生表示非常喜欢。这样的联排诗句细碎又极富召唤感的物象书写很有“诗感”。于是教师鼓励学生用相似的方式来书写自己的记忆,并使其凝结在物象、声响或气味中,帮助学生体会何谓现代主义的“隐喻式”和“转喻式”表达。作为诗歌赏析的主体,师范生若能在高校文学课堂切身感受过、领悟到甚至自行总结出诗歌之美的独特性,在其日后成为语文教师时,才有机会真正转变为诗歌赏析的主导者,从而引领学生同样去发现、理解这种表达的美好之所在。
二、即时性考查与质化考核
需要指出的是“挑战性教学”和“探讨式教学”并不意味着对“接受性教学”和“模仿性教学”的完全摒弃。模仿和灌输本是为了弥补人类的天生弱点,例如遗忘和懒惰,也需以大分值体现在考核中。对于顺应人类求知本性的“苏格拉底式”教学方法,其考核方式很难量化,但却可以“质化”,将考查重点从背诵倾斜至理解和运用。具体到诗歌而言,如何用精准的语词表达所思,用合适的文体传递情绪,用妥帖的意象塑造意境,应当与准确背诵诗作原文、概括其主题思想等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为实现“质化考核”,笔者加大了学生成绩中“平时成绩”的占分比重,依据学情即时展开课堂考查,让学生现场演练对诗歌从“赏”到“析”的进阶式学习。如在艾青章节,学生讲完《我爱这土地》后,教师给出艾青同样创作于1938年的诗作《北方》,让学生自行思考:“为何前一首诗作的流传度更广?诗歌的感染力究竟凝结于意境还是意象?”同时,笔者给出戴望舒1942年从日本人的监狱死里逃生后所创作的《我用残损的手掌》一诗,让学生自行比较“面对沦陷的江山,艾青和戴望舒两位诗人的悲怆表达有何不同?”鼓励学生自行总结戴望舒从雨巷的彷徨中走出后,其诗境从幽深婉约到宏壮阔大的转变。通过这样的兼具横向(不同诗人)与纵向的(同一诗人不同时期)诗作比较,学生会发现:就像爱国的方式有很多种一样,爱国情感的文字表达方式也是极其丰富的。而这种坚持比较视野的讲述思路,亦是对整体性美育思路的贯彻。
三、问题设置与课堂翻转
在挑战性教学的课堂中,师生都处在一种紧张、兴奋的状态。教师需花费很多精力在预学导学环节,要密切关注学生状态与情绪,适时调整学习任务的设置。学生则须紧跟教师步伐,逐步完成阅读、欣赏、体悟、总结、比较等任务,落下任何环节都很难跟上教师的节奏。对于教师而言,这种即时考查的重难点在于问题的设置。譬如,讲授郭沫若的《女神》时,教师将“这些诗句表现了诗人怎样的情绪”,替换为“从这些诗句中你感受到怎样的情绪”,将“通过这些意象诗人想要表达什么样的主题”,替换为“这些意象的组合给你什么感受,你会组合什么样的故事”——看起来不过是所提问题的微小变化,但对于学生而言,替换后的提问方式悄然将课堂翻转,学生无法从教师那里直接获得答案,必须调动阅读感受、诗歌直觉和已有知识去整理出属于自己的答案。对于成功完成任务链的学生,该过程是由浅入深、由赏到析、渐入佳境的过程,既充满挑战,又饱含成就感。即使是课堂参与度不高的学生,也能逐渐被身边人的参与热情感染,从而有可能成为下一次学习的挑战者。
若干次这样的现代诗讲授与考核尝试之后,学生给笔者带来了巨大惊喜:学生赏析诗歌不再离题千里,对诗作情绪的把握、意境的概括、主题的提炼大都接近所谓的标准答案,同时又能给出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的理解。不可否认,有些游离于标准之外的理解一直存在,学生即使不写在试卷上,也不意味着不会这样去想,教师所要做的是允许并鼓励这些飞扬想法的存在,这些宝贵的想象力终将会以别样的方式在未来绽放。在挑战性教学中,作为主导者的教师始终引领师范生作为课堂主体,无论是恰当语言的使用和灵活思维的涵养,还是基于鉴赏与再创造的审美能力的提升,都会在日复一日的“从赏到析”的挑战中缓慢习得。只有真正热爱诗歌且能够理解、感悟诗歌的语文师范生(未来的语文教师)才可以说是具备了文化传承者的核心素养。当我们回归文学本体时会发现,作为中文最古老的文学样式,诗歌是最接近国人深层情感的表达方式,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对美的天然感悟、对情的自然表达。因此,无论是赏析现代诗还是古典诗,本质上是一场情感和情感的相遇。诗歌是美的,诗歌赏析应当也是美的。
“一体化”美育课程体系的建构意味着培养学生拥有感悟文学美与文字美的能力,这是一个长时段、跨学段、梯度进阶的过程。语文师范生既是高校文学类课程的学习主体,也是中小学语文课程的讲授主体。就职业延续而言,唯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就职业素养而言,热爱诗歌、不排斥诗歌的教师才可能把诗歌之美传递给学生。通过诗歌课堂的挑战性教学,还学习主体的身份给学生,还自由思考的时间给学生,少一点功利阅读,少一点“深刻”讲解,允许一定程度的“放肆”阅读、“开放”理解,或许可以让师范生爱上诗歌,爱上赏析诗歌。虽然说“诗无达诂”,但这从来不是摒弃诗歌丰富性阐释的借口,而是鼓励我们接受“诗歌赏析是有难度的”这一事实。某种程度上“无达诂”者,正是想象力绽放之地,是诗性美、文学美的蕴含之所。
【基金项目:本文系唐山师范学院2023年度协同提质计划对接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师德的内在规律与实践路径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D2023XTTZ018】
作者简介:汪贻菡(1982— ),女,博士,唐山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研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马小会(1986— ),女,博士,唐山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研方向为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