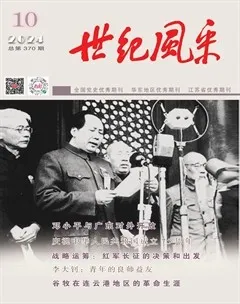陈望道与科学的因缘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复旦大学玖园爱国主义教育建筑群落成。这里曾是陈望道、苏步青、陈建功、谈家桢的旧居。苏步青、陈建功是著名数学家,谈家桢是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三人一生心系祖国和人民,为科学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改善、中华民族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以《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著名语言学家的身份为人们熟知的陈望道,同样一生与科学结缘。从独立发表数学论文、首创“科学小品”新文体,到办学治校中有计划地开展科研工作,“科学”同样是陈望道一生中绕不开的关键词。
汲取科学知识
青少年时期是尚学求知的黄金时期,陈望道对科学的兴趣也是在这时形成的。16岁那年,不满足于旧式私塾教育、渴望新知的他,在父母的支持下离开分水塘村,前往义乌县城求学。在义乌第一所官办西式学堂——绣湖学堂,陈望道除了完成修身、读经等课程外,还第一次接触到数学、博物等现代科学知识。这里便成了陈望道的科学启蒙之地。
后来,在“兴实业,重科学”的时代风气熏染下,陈望道开始思考如何通过振兴实业,改变近代中国贫弱局面,以达民族御辱自救的目的。为了接受更全面的新式教育,他选择前往金华府立中学堂求学。期间,陈望道日夜沉浸在知识的海洋,如饥似渴地汲取现代科学知识。比如,陈望道对实业兴起的重要标志——铁路事业发展产生了浓厚兴趣,十分关心铁路建设情况。他曾回忆,当时一听到哪里有开办铁路的消息,总是会心潮澎湃。
随着知识的积累和视野的拓宽,陈望道深知要想真正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将中国的实业发展推向新的高度,就必须走出国门,到科技发达的国家留学深造。陈望道曾说:“欧美的科学发达,要兴办实业,富国强民,不得不借重欧美科学。”1913年,陈望道考入钱塘江畔的之江大学。这里自然风光奇美,学术氛围浓厚,为陈望道提供了极佳的学习环境。他专注于英语和数学的学习,在《教育周报》《教育杂志》发表了《层行等和排列法》《数学答问一则》《圈为偶数之证明》《劈质数通法》等多篇文章,充分展示了其在数学领域的良好天赋和独到见解。这段文理兼修、中西融合的学习经历,为陈望道日后治学奠定了重要基础。
首创“科学小品”新文体
科学小品是一种以小品文的笔调和形式表现艰深、抽象的科学理论,实现科学大众化普及化的新体裁。科学小品的首次亮相就是在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半月刊上。
1934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化界展开猛烈进攻。在党的领导下,左翼文化界人士通过创办《太白》给反动派以牙还牙的猛烈反击。《太白》从1934年9月出版创刊号至1935年9月被迫停刊,前后整整一年。尽管办刊时间不长,但是《太白》办得别开生面,以鲜明的立场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文化专制的黑暗腐朽,有力支持了左翼文化运动向前发展。罗竹风高度评价说:“《太白》半月刊的出现,一新读者耳目:清新、刚健、泼辣、浑厚,可谓独树一帜”,故一经出版便广受欢迎。
《太白》的定位是以发表小品文、杂文为主的文学半月刊,辟有十多个栏目。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创新性的要数“科学小品”。据统计,《太白》先后刊发66篇科学小品。例如在创刊号的这一专栏中,就发表了克士(即周作人)的《白果树》、贾祖璋的《萤火虫》、刘薰宇的《半间楼闲话》、顾均正的《昨天在那里》等四篇科学小品。这一系列科学小品内容涵盖了动物、植物、天文、物理、数学、逻辑等诸多领域,既有用通俗易懂语言进行知识科普的文章,又有介绍自然科学领域最新前沿成果的文章。文章大都采用短小精悍的篇幅,生动活泼的语言,来剖析物象,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战斗性。这对于推动科学文化在中国的普及和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科学小品也由此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并随之开始不断在杂志上涌现。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也曾表示,正是在《太白》科学小品的影响下,他才走上了科普创作的道路。1962年陈望道在给叶永烈的回信中证实:“我国刊物上登载科学小品确是从《太白》半月刊开始。《太白》半月刊自始就以刊行科学性进步性的小品文为自己的任务,以与当时的论语派、以所谓幽默小品为反动派服务的邪气抗衡的。”
重视科学研究
陈望道是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首任校长,重视科学研究是他办学治校过程中始终秉持的核心理念和基本方针。1952年,陈望道刚上任不久,面向全校师生作报告时强调,复旦大学已经由旧式英美体系的大学彻底转变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新复旦,新复旦必须贯彻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方针,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
陈望道曾把高等学校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办校务的阶段、教务的阶段、科学研究的阶段。他认为:“如果一所学校只停留在办校务和教务的阶段,不进一步向科学研究阶段发展,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肯定不能提高。”他还指出,“综合大学负有两个重要的任务:一个是教学任务,要为国家大量地培养从事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的专门人才;还有一个是科学研究任务,对于国家负有发展基础科学、提高文化科学水平的责任。”为此,他经常鼓励教师“脱离教书匠的称号”,一定要从事科学研究,要进行创造性劳动,否则文化事业就不能发展,教育事业也不能发展。
1953年9月综合大学会议后,复旦大学在陈望道的领导下开始有计划、全校性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教师们的科学研究热情高涨。特别是1954年庆祝建校49周年之际,在陈望道的提议下,学校举办了首届科学报告讨论会。根据现存资料显示,这届科学报告讨论会分成中文、外文、历史、新闻、经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9个小组,数十位名家教授作专题报告。陈望道专门为会议的召开写下一段祝贺词:“综合大学应当广泛地经常地结合教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为祖国建设服务。今年校庆的种种活动,如举行科学讨论会、著译展览会等,就以促进科学研究为中心。这是一个创举,希望大家合力完成这个创举。希望大家踊跃发表现有的成就,争取更大的胜利。”
时至今日,“学术校庆”已成为复旦大学惯例,既是对全校师生一年来科研成果的大检阅,也是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生态的有效途径。在陈望道的领导下,复旦大学作育国士,恢廓学风,面貌焕然一新,开启了学校办学历史上的第一次腾飞。
讲求科学方法
科学不仅是一种学问,更是一种方法。作为一名学者,陈望道治学严谨,坚持运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探究真理、发现新知。他反复告诫学生,从事学术研究“没有什么捷径可走,靠的是对大量事实也就是材料的掌握,靠的是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靠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成果是要从科学态度得到的。”
《修辞学发凡》是陈望道从事修辞学研究的代表力作。他积十年之功,凭一己之力,“将修辞学的经界略略画清,又将若干不切合实际的古来定见带便指破”。当时,修辞学刚刚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相关研究仍然薄弱而杂乱,处于一个“中外修辞学说竞争时期”。有的学者“据外论中”,直接照搬外国同类书籍的理论;有的则是“据古论今”,墨守古人陈言,忽视修辞学的发展。陈望道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反对机械模仿,又反对抱残守缺,主张“应当切实负责地寻求各种眼见耳闻的修辞事实来逐一加以观察分析”。他曾形象生动地说要做“新的古今中外派”,要融合中外、贯通古今,“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正是在科学方法的指引下,《修辞学发凡》的出版,完成了中国传统修辞学向现代修辞学的转变,历经岁月淘洗,仍堪称现代修辞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在文法研究上,陈望道曾“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鉴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就,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文法革新讨论。在此之前,中国的文法研究几乎都以《马氏文通》的体系为准绳,偶尔“只在不很重要处加了一点改革,并不更动马氏的格局”。陈望道十分肯定《马氏文通》的历史价值,但对其照搬西方文法来讨论中国古文的做法不以为然。为此,他“以事实验证学说,从事实缔造学说”,以《语文周刊》为阵地,围绕文法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词类区分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改革观点。这些研究成果不因袭成见,“从事实里面探求改革的方案”,推动了中国文法研究迈入新的“缔造时期”。
陈望道曾任《辞海》主编,同样为后人留下了一部皇皇巨著。他曾语重心长地说:“辞典应当是典范,百人编,千人看,万人查,因而必须严肃认真,毫不马虎。必须给人以全面而又正确的知识,如果提供片面、错误的知识,那将贻患无穷,就不能称作‘典范’了。”为了提高编纂质量,确保条目释文符合“科学性第一”的要求,陈望道立下了“没有外行话”和“没有外行完全看不懂的话”两条经典原则。他改变过去人海战术的编写理念,提议建立“分科主编负责制”,避免因条目繁多、所涉学科领域广泛而造成的编辑错误和硬伤,促成《辞海》实现脱胎换骨的蜕变。
责任编辑:侍晓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