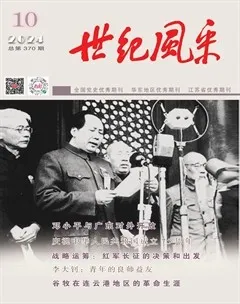白驹会师:华中抗日斗争的关键落子


1940年10月10日,陈毅、粟裕领导的新四军和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西南部的白驹镇狮子口胜利会师。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的重大会师之一,白驹会师不仅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把八路军封锁在华北、新四军封锁在江南,最终分化消灭的阴谋,而且为壮大华中抗日力量,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打开华中敌后抗战新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全民族抗战事业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杰出贡献。
党中央运筹帷幄:开辟苏北,发展华中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陕北的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分别开赴华北、华中抗日前线。1937年至1938年5月间,随着上海、南京、徐州等大城市的相继陷落,日本侵略军又把目光瞄准了当时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武汉。1938年6月,日军调集两个军,共9个师团,在航空兵团和第三舰队的掩护下突袭武汉。为了避免多线作战兵力不足的窘境,日军不得不将苏北阜宁、东台等地的军队撤走,苏北中北部地区暂时成为“真空”地带。
华中地区滨江临海,津浦、陇海铁路大动脉贯穿其间,是坚持持久抗战的纵深后方,也是发展壮大我军力量的重要区域。早在1937年8月下旬,八路军便开始向华北挺进。1938年2月15日,关于新四军的行动原则问题的电报中,中共中央复电项英、陈毅,指出:“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地。”这也成为中共中央最早关于新四军行动方向的战略部署。5月4日,中共中央给时任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发出《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中再次强调:“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这也标志着中共中央正式选取苏北作为发展华中的重要突破口。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反共摩擦日益加剧。为了凝聚最广泛的抗战力量,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针对抗日战争的新形势,进一步明确了“巩固华北和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与方针”。1939年2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阐明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并与新四军领导商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具体方针。1939年4月至5月间,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1940年以后,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把八路军、新四军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毛泽东给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发出《发展华中根据地的部署》,明确指示:“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为打破封锁,求得最基本的生存空间,进而在复杂战局中占据主动地位,中共中央于1940年5月4日向东南局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要求在“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6月1日,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发出《对华北华中的战略部署》,要求“彭朱支队即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及黄克诚纵队应立即出发。黄应亲率全部或至少两个旅南下”。
中共中央对于华中地区的战略地位有着清醒的认知,从最开始“挺进华北”坚决抗日,到为应对摩擦决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再到“发展华中”战略中的“向北发展”,将苏北确定为发展华中敌后抗战最有利的地区,最终促成新四军北上和八路军南下,挺进苏北,填补华中的真空。在瞬息万变的斗争形势中不断调整华中的战略部署,显示出中共中央运筹帷幄的战略思维和果敢决断的应对策略。
指战员坚决执行:挺进苏北,创建华中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新四军军部部署,1938年4月起,陈毅、张鼎丞率领新四军第1、2支队向苏南敌后进军,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9月,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率先渡江,控制了江都县境内的嘶马、大桥地区,为后期迎接主力部队渡江建立了桥头阵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来到华中,并于1939年12月19日向中共中央提出我党在华中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意见,即“江苏北部我们都没有正规部队及党的机关去活动,亦无地方党,而这又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因此,这是我们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1939年12月至翌年2月,刘少奇在皖东北地区连续主持召开三次中原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以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为突围方向,逐步发展华中的方针,即将苏北作为华中的突围方向,调江南新四军主力渡江北上,同时派八路军一部迅速南下,共同完成开辟华中敌后根据地的重任。
1940年7月8日,陈毅、粟裕率领江南指挥部机关及老2团、新6团等主力经扬中县北渡长江,到达江都县吴家桥,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等部会合。随后部队在塘头整编,部队整编为3个纵队9个团,共7000余人。经中共中央批准,7月下旬将江南指挥部改称江北指挥部。7月25日,陈毅率部东进,建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
为配合新四军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194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黄克诚率八路军主力一部南下,开赴华中,与彭雪枫部会合,组建八路军第4纵队。1940年8月7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苏皖豫支队、新2旅陇海南进支队和新四军第6支队第4总队,统一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任命黄克诚为司令员兼政委,全纵队辖3个支队9个团,2万余人。部队整编结束后即刻擎旗南下,东进至淮(阴)海(州)地区,配合已经渡江北上的陈毅、粟裕等部东进,进行“坚决争取控制全苏北”的斗争。
当时苏北各方势力错综复杂,不仅日、伪军长期盘踞,还有韩德勤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李明扬、李长江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斗争形势异常复杂严峻。陈毅冷静分析苏北地区军事态势,提出“击敌、联李、孤韩”的战略方针,并三次冒险,亲赴泰州与李明扬、李长江谈判,达成共同抗日的协议。但是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自恃军事占优,狂妄叫嚣要先消灭北上的新四军,再消灭南下的八路军。1940年10月4日,韩德勤调集3.5万人,兵分三路悍然向我新四军驻地黄桥大举进攻,新四军奋起反击。为了支援黄桥决战,中共中央发出指示,韩德勤又大举压迫我军,八路军不能坐视。并提出:“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黄克诚命令八路军第5纵队1支队和2支队一部奋力南下支援新四军,分路向盐城、阜宁进发,先后突破盐河、废黄河防线,连克东沟、阜宁等城镇,直逼苏北重镇盐城。在八路军的战略配合下,10月6日,陈毅、粟裕指挥新四军约7000人在黄桥迎战来犯顽军,共歼灭韩德勤部1.1万余人,俘获3800余人。黄桥战役的胜利,成为开辟苏北的奠基礼,为发展和坚持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扫除了障碍。
黄桥决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新四军乘胜向北追击溃逃的韩军残部,势如破竹。10月10日,新四军1支队2纵队6团的先头部队与八路军5纵队1支队的先头部队在盐城大丰白驹镇狮子口胜利会师。
根据地抗日反顽:经略苏北,问鼎华中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胜利会师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两军胜利会师从根本上扭转了苏北地区敌我斗争形势。此后,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新四军开始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先后开辟形成江南、苏中、盐阜、淮海、皖东、豫皖苏边等总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500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华中局、华中党校、鲁艺华中分院、抗大五分校、江淮日报社、华中银行等政治、经济、文化机构陆续建立,著名人士、社会贤达纷纷来到苏北抗日根据地,苏北迅速成为华中抗战的军事、政治和文化中心,“陕北有个延安,苏北有个盐城”的美誉传遍大江南北。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胜利会师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两军胜利会师,标志着中共中央“发展华中”战略目标的基本实现,其中华南、山东、中原、华北等地多个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形成了一个整体,便于从战略上统一指挥、统一意志、统一行动。1940年11月1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海安成立,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1941年1月,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遭受严重损失,正是此前的两军会师,为保存和发展新四军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成为新四军浴火重生的转折点。1941年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新军部成立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部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全军扩军为7个师、1个独立旅,总兵力9万余人。完成整编的新四军立刻投入挽救民族危亡滚滚洪流之中。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胜利会师铸就了伟大的“铁军”革命精神。会师过程中,八路军、新四军生动诠释了坚决听党指挥、加强团结协作、连续英勇作战、坚定必胜信念的革命精神和顽强作风,形成了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的精神内核。跨越历史时空,新四军“铁军”革命精神在新时代依然熠熠生辉,成为引领我们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
责任编辑:侍晓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