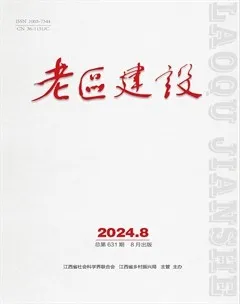相对贫困视阈下预防低收入家庭返贫问题研究


摘 要: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集中体现。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但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旧存在,需持续关注低收入家庭面临的返贫风险,特别是暂时性返贫风险和持续性返贫风险导致的返贫现象,应从动态识别治理对象、强化社会保障体系、构建有效的防返贫机制、鼓励社区参与、激活低收入家庭的内生发展动力等方面制定预防返贫的策略和措施,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关键词:相对贫困;低收入家庭;返贫;预防措施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7544(2024)08-0075-09
一、前言
(一)研究背景
1949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仅27美元,不到亚洲人均国民收入44美元的2/3,大多数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1981年,按照世界银行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线的标准,我国有8.8亿贫困人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2021年、2022年和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始终强调“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的要求。低收入家庭虽然已经脱离贫困,但受地理位置、人口资源、教育等多方面因素限制,尚处于相对落后状态,面对各类风险,仍处于脱贫标准的边缘,存在返贫的风险。如何促进低收入家庭收入的增长,降低脱贫后的返贫风险,是当前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础前提。
基于此,本研究首先分析了相对贫困背景下,导致低收入家庭返贫的各类风险,其次从动态识别治理对象、强化社会保障体系、构建有效的防返贫机制、鼓励社区参与、激活低收入家庭的内生发展动力等多方面入手,提出抑制低收入家庭返贫的治理措施,探讨共同富裕背景下的低收入群体常态化帮扶问题。
(二)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在绝对贫困被彻底消除以前,学界大多致力于分析我国贫困现状以及研究如何消除贫困,对于脱贫后返贫的现象关注较少,并且大多学者都是基于预防农村人口返贫进行分析,将低收入家庭脱贫后返贫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进行研究则比较少。本研究通过梳理返贫原因,针对当前帮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意见建议,以期增进我国防返贫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进一步拓宽相对贫困问题的研究视角,丰富相对贫困治理的研究内容。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低收入家庭相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国内外学者大量关注,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相对贫困的衡量、返贫成因分析以及防治返贫措施三个方面。
关于相对贫困,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由于收入低、健康状态差、文化水平低、劳动力素质低下等原因,导致“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使贫困状况恶化(缪尔达尔,1957)。相对贫困是缺乏维持一定生活水平的物质资源(Townsend,1979),但不仅仅是经济上收入低下,更体现为收入创造能力、社会参与能力与机会获取能力等方面的缺失(Sen,1999)。国内学者认为相较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具有多维性、精神性和隐蔽性,治理的难度更大、更复杂(唐任伍,2019)。从精神性角度而言,相对贫困者可能在长期贫困中逐渐衍生出“安贫乐道”“人穷志短”的精神贫困价值观,缺乏争取改变自身状况的志向,导致脱贫返贫循环发生(杭承政和胡鞍钢,2017),也有学者通过实证验证了相对贫困人口成为主要返贫群体(李倩和刘玉超,2023)。
关于低收入家庭返贫,学者普遍认为收入是相对贫困界定的核心标准,也是相对贫困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左停等,2023)。当前我国低收入家庭占全国家庭比重接近2/3,人口规模巨大,其收入来源主要为劳动报酬收入、务农收入和社保收入,缺乏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李炜等,2023),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总体上更为缓慢,收入差距正在扩大。有学者指出疾病、残疾和缺乏劳动力是造成返贫和致贫的直接原因(潘文轩,2020),而以受教育水平为代表的内部因素对脱贫返贫的影响程度远大于以自然灾害为代表的外部因素(孟婷,2023),因此,共同富裕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农村低收入家庭能否形成可持续的收入增长内生动力(罗楚亮和梁晓慧,2022)。在返贫类型方面,学者大致将返贫风险划分为政策性返贫、能力缺失返贫、环境返贫和发展型返贫四种类型(郑瑞强和曹国庆,2016)。
关于预防返贫,多数学者都认为通过预警防范和干预措施可以降低返贫风险发生的概率,并且其成本远低于事后的扶贫治理。从具体的防治方法来看,学者们则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应重点关注人力资本,认为农村贫困人口彻底脱贫和预防返贫的根本在于人力资本的提升(和立道等,2018),有些学者从脆弱性脱贫角度认为缺乏“安全网”的保障是家庭返贫的关键因素(周迪和王明哲,2019),也有学者从外部因素方面提出阻断农村脱贫人口返贫应该从加强党建引领、兴旺产业建设、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农村现代化建设出发(张开云等,2021),或从社会保障、监测监管等方面构建防范返贫发生的实践进路(吕灿等,2023)。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相对贫困以及返贫的类型、原因及治理方式都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基本形成以下共识:第一,虽然不同学者采用的参照标准不同,但结果均显示我国农村低收入人口规模庞大。第二,返贫是内外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第三,在返贫之前对返贫的风险进行根治更有利于返贫的防治。这些研究成果对相对贫困与反贫困理论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也为本研究探索如何有效预防返贫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但现有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例如,对返贫对象的识别标准和贫困状态的动态监测探讨相对缺乏,因此本研究针对相对贫困情况下,如何有效识别和监测返贫对象,以及如何建立预防机制有效守住返贫底线问题进行多角度讨论。
三、低收入家庭认定与返贫风险分析
(一)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不统一
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期间,我国所选取的贫困标准具有一维性,但在新发展阶段,贫困问题由显性绝对贫困转向隐性相对贫困,使得相对贫困标准制定更加复杂。城乡之间、不同地域之间,生存成本存在较大差异,认定标准的不统一导致难以确定相对贫困人口是否再次返贫。
由于低收入是一种对比下的产物,不同参照群体会形成不同的低收入标准,目前对低收入家庭的概念和界定标准研究较少,对于低收入家庭的认定标准界定不明。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划分标准大致有三种口径,第一种是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划分标准,并未考虑其他指标,但这种口径没有全国统一性的标准作为参考。第二种是采用民政部制定的低收入家庭标准,即低于国家低保标准的1.5倍,按这一标准,我国低收入家庭人数相对较少。第三种是采用人口比例为标准,将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中低收入家庭组和中低收入家庭组直接认定为低收入人口,按照这一标准比第二种方式认定的低收入家庭人数多出约800万。不同口径下的低收入人口的范围和规模差异相对较大,会增加扶贫工作开展的困难,并且这种差异还会影响扶贫工作的精准性和实施效果。因此,本研究在参考和借鉴了相关学者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基础上,选用第二种标准,即选用与低保标准直接挂钩的家庭人均收入作为低收入家庭的识别标准。由表1可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明显,如2016年农村居民收入仅为城镇居民收入的36.8%,2016年至2023年的8年间,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相对城镇居民的收入有所增长,但差距依然存在,平均年增长率仅为0.7%。同时低收入组的收入占高收入组收入的比例有所减少,反映出农村内部贫富差距有所扩大,过大的收入差距意味着相对贫困人口将长期存在。
(二)低收入家庭的返贫风险分析
本研究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归纳总结,将低收入家庭返贫风险分为两类,一类是暂时性返贫风险,一类是持续性返贫风险。
1.低收入家庭暂时性返贫风险
(1)灾害性返贫风险
从暂时性返贫的风险角度来看,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是导致大多数低收入家庭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这些事件的不可预测性使得它们构成了一种突发性的返贫风险,对低收入家庭的经济状况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许多低收入家庭的主要收入依赖于农业,但农业不仅周期较长,而且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也相当高。这意味着,一旦遇到不利的自然条件,如干旱、洪水或病虫害,这些家庭的农作物产量可能会大幅下降,从而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家庭收入。当这些家庭面临突发性风险时,可能会导致当年的收入急剧下降,这不仅会加剧其贫困程度,还可能迫使他们诉诸短期应急手段来缓解经济压力,如借债或出售资产。这些权宜之计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他们的财务危机,使他们陷入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恢复生产和生活所需的时间越长,这些家庭的返贫风险也随之上升。
(2)支出性返贫风险
部分刚刚迈过贫困线的低收入家庭常常面临资金储备不足的问题。在当前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中,普惠性保障仍然不足。因此,一旦这些家庭遭遇意外残疾、罹患重大疾病或其他突发健康问题,他们很可能陷入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困境。家庭成员的疾病或残疾不仅直接影响到患者本人,还可能波及家庭其他成员,尤其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进而影响到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和生活品质。这不仅可能消耗掉他们辛苦积累的有限资金,还可能迫使他们不得不借贷或出售资产以应对短期的医疗费用,从而增加他们再次陷入贫困的风险。
2.低收入家庭持续性返贫风险
持续性返贫风险是指会长期制约低收入家庭发展能力的一类风险,根据不同原因,可以分为思想性风险、政策性风险和结构性风险。
(1)思想性返贫风险
思想性返贫风险是指那些在精神层面缺乏进取心和自我提升动力的低收入家庭,这种风险的成因复杂,包括教育水平的限制、传统观念的束缚、信息闭塞以及缺乏成功脱贫的榜样等,导致他们在思想上缺乏勤劳致富的干劲和自我发展的意识。这部分人群往往满足于现状,缺乏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脱贫的能力和意愿,并且思想性返贫风险可能导致家庭世代贫困,因为他们缺乏打破现状、追求更好生活的动力和能力。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物质上实现快速脱贫,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策倾斜和帮扶,因此脱贫程度浅。随着大规模外源性帮扶的结束,这部分依赖政策的人群由于缺乏自我发展的能力,很难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再次陷入返贫风险的可能性较大。
(2)政策性返贫风险
传统帮扶政策较多关注物质资助,忽略了低收入家庭思想方面的问题,低收入家庭自我发展动力不足,造成自我脱贫缺乏主观能动性,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和降低低收入家庭的返贫风险。同时,一些基层组织在使用传统的扶贫模式时,可能过于追求短期效果,采取了所谓的“短平快”策略。这种做法虽然能够迅速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经济条件,但也可能导致这些家庭对政策扶持产生依赖性,一旦政策扶持减少或消失,他们面临的返贫风险将会增加。
(3)结构性返贫风险
在我国养老体系中,代际支持是低收入家庭重要的生活保障,但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大量中青年劳动力从相对贫困地区涌向城镇,留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导致当地劳动力短缺,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这种人口结构的失衡使代际支持在抑制低收入家庭返贫风险方面的作用逐渐减弱。另外,低收入家庭一般会通过削减教育开支来缓解多子女的生活压力,低收入家庭对待教育常常持消极态度,错误的教育观不仅导致父母要求子女尽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且子女本身也缺乏学习积极性。虽然家庭经济负担暂时减轻了,却直接降低了低收入人口综合就业能力,低收入家庭的致富能力不断弱化。
(三)低收入家庭返贫本质分析
由图1可知,低收入家庭的返贫是一个由贫困到脱贫再返贫的过程。返贫的本质,一方面体现了返贫人口自身发展能力的匮乏,这一点与致贫是相一致的,另一方面体现了返贫人口和环境的发展关系,即从脱贫状态倒退回返贫状态的过程,反映出低收入家庭在发展中抵御返贫的脆弱度高和社会适应性差等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虽然低收入家庭无论致贫还是返贫,其外在表现都是生活必需资料的短缺和匮乏,但从返贫过程可以看出,相对于暂时性风险,低收入家庭的持续性返贫风险不是单纯的收入问题,这类风险的防范不能仅仅依靠收入上的补缺,而需要明确更深层次的返贫风险诱发根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其抵御风险的能力,才能实现低收入家庭的可持续发展。
四、预防低收入家庭返贫的措施
所谓返贫预防,是通过对低收入家庭给予政策扶持和物质帮助、促使其技能提升和观念转变以及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等多种措施,增强低收入家庭抵御返贫风险的抗逆能力,增加其增收的机会和渠道,减少脱贫人口“饱而复饥”“暖而复寒”的可能性。
(一)构建低收入家庭相对贫困的动态识别和监测体系
低收入标准的可比较性较强,也相对容易测量相对贫困的深度,但如果将收入作为唯一衡量指标,则只能反映相对贫困状态的一个侧面,并且不同口径下的低收入人口范围和规模差异也会相对较大。因此,应当构建低收入家庭相对贫困群体的识别体系和认定标准。一方面,将不同地区、不同城镇、不同时期的多维度衡量标准纳入相对贫困的识别体系。高度关注易返贫的低收入家庭,如低保户、五保户、残疾户、家庭突发重大困难户,紧盯处于标准边缘的边缘户,重点关注潜在的低收入返贫家庭,如虽然拥有劳动力,但个人生活资本不足,或虽在城市打工却面临较高流动性风险的低收入人员,他们的住房条件、子女教育、就业机会以及医疗保障等问题,都是应关注的重点。这类家庭虽然已脱贫,但发展基础比较差,一旦遭受较大冲击,极易再度返贫。为此,需要通过前期摸底排查、实地入户调查、入库家庭互评互议以及持续重点监督检查等环节,为低收入家庭建立包含脱贫类别、脱贫原因、脱贫能力等信息在内的脱贫档案袋和信息卡,严格管理并定期更新建档立卡信息,确保建档立卡信息的精准性、动态性和长期性。
另一方面,要制定纳入低收入家庭相对贫困帮扶范围的限制性条件,除了采用入户调研的监测方式外,还要依托国家乡村振兴的数据,通过开发新型大数据服务平台,强化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间的信息共享与协作,对低收入家庭实时动态监测。创新识别工具,对低收入家庭中家庭成员的消费、投资、收入来源、储蓄、精神面貌等多个维度进行高效检测,对比分析脱贫户信息与返贫预警线,及时打通信息壁垒,精准识别相对贫困人群和低收入家庭的需求,提高帮扶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强化社会保障体系
在转变传统的扶持方式,引导低收入家庭通过自力更生实现彻底脱贫的过程中,政府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需要建立健全低收入家庭和欠发达地区帮扶机制。一是落实相关政策,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体系,形成政府、市场和扶贫主体之间的协同机制。在战略层面,继续推进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中部崛起等战略,多渠道统筹城乡发展,完成帮扶体系的转换。在政策层面,针对低收入家庭的持续性返贫风险,必须坚持需求导向原则,细致识别并理解每个家庭、每位个体的独特及个性化需求,通过实施定制化的救助策略,如“一户一策”和“一人一策”,确保援助措施既精准又高效,满足不同群体的具体需求,努力消除体制性障碍,吸引社会力量,扩大参与主体,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共治。二是加速完善普惠式社会保障体系,充分发挥二次分配的调节作用,间接提高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水平。提升资助参保政策的精准性,为因暂时性返贫而被纳入预防返贫监测对象的低收入家庭给予临时补助。
同时,完善应纳尽纳、应保尽保政策,积极扩大低收入地区的保险覆盖面,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帮扶、接受捐赠、利用村集体经济收入以及扶贫项目资产收益等多种途径,协助农村低收入人口参与保险计划并缴纳费用,提升家庭参保比例,并精准落实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为核心的三重保障制度,稳定基本医保水平,落实大病保险政策,针对低收入家庭养老功能逐渐退化的问题,加强相应的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对低收入家庭实施精准救助。
(三)增强思想教育,开展心理辅导
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思想意识支配着个体信念并影响个体的行为,因此要规避返贫风险也应从思想和观念入手,对低收入家庭加强精神建设,在意识层面做到扶志不懈。要培育低收入家庭正确的价值观,破除“等、靠、要”的消极思维,摆脱宿命论,为这部分人群提供心理辅导和咨询服务,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心态,克服心理障碍。优化宣传平台,通过公益广告的方式倡导树立勤劳致富意识,积极树立典型案例,强化低收入家庭的自我发展动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强低收入群体的内生动力,从而充分发挥其主体性。
(四Mzj7XMynh1gwtQyJcc497QH15VobqXCMn7xbdNdPgFY=)加强人力资本建设,推动内源式发展
相对贫困需要常态化治理,从宏观角度看,人是重要基础和保障,因此要从根源上降低低收入家庭的返贫风险,减少返贫风险的代际传递,首先应科学设计防返贫教育机制。
一方面,针对受教育水平整体较低的问题,在防止返贫治理时,政府应当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鼓励机构根据市场需要参与职业教育培训,为就业困难家庭提供全过程技术支持和职业指导,通过强化职业通用能力规避失业风险,增强社会竞争力,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地方政府要利用自身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发展新型业态,以产业带动就业,以就业保障收入,全面提升低收入地区和家庭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要重视乡村教育,提高低收入地区的基础教育普及程度,关注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教育,需要完善线下教育供给体系,增加教育资源投入,继续推动实施“特岗计划”,鼓励到“两基”攻坚地区任教,努力增加低收入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竞争力。制定长期的教育发展战略,通过与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和社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为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支持和资源,以助学金、奖学金等方式持续为低收入家庭学生创造接受高等教育的条件,缓解低收入家庭教育压力,对援助的教育项目定期跟踪和评估,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还要利用好互联网线上资源与线下体系,为已脱贫地区提供强大的智力引擎,让低收入家庭的下一代拥有改变生活的能力和眼界,摆脱因智返贫的困境。
其次,还应持续加强基层干部队伍的建设与发展,进一步完善大学生村官计划、西部志愿者计划、三支一扶等人才引进政策。同时,为有抱负的创业者营造一个有利的创业环境,提供包括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在内的一系列支持措施,以鼓励他们回归家乡创业。这些措施旨在赋予脱贫人口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和信心,激发他们致富的内在意识,从而带动整个社区的繁荣与发展。
(五)鼓励社区参与,建立激励机制
鼓励社区参与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对于支持低收入家庭至关重要。这些家庭常常面临着构建社会支持网络难的问题,难以从现有网络中获得必要的资源来解决他们的困境。根据贫困地理学中的反贫困研究相关理论,除了鼓励向外迁移,还应重视集群发展的效应。因此,社区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有着重要作用。应当鼓励社区和社会力量参与到这部分人群的帮扶工作中去,通过社区和专业社会工作者的支持或志愿服务,增强他们的社会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帮助其重建非正式支持系统。建立一个全面的激励和认可体系,通过社区活动和媒体报道,强化社区成员的参与感和荣誉感,鼓励企业通过社会责任项目参与到低收入家庭的支持中,并在社区公共场所、网络平台或媒体公布荣誉榜,展示获奖者的贡献和成就,还可以通过提供奖金、税收减免、优先权等多样化的奖励形式,激励更多人参与。对于激励机制,还要建立相应的反馈机制,收集低收入家庭和社区组织对奖励体系的意见和建议,不断优化和改进,共同促进低收入家庭的持续发展。
五、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其中包括“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近年来,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低收入家庭面临的返贫风险问题逐渐凸显,这不仅对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产生影响,而且可能加剧规模性返贫的风险,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条件不利的乡村地区,这种风险尤为突出。本研究锚定上述问题,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换的场景出发,系统阐释了低收入家庭返贫的发生机理,指明了相对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构建了“返贫风险识别—返贫风险应对”的分析框架,并根据风险分层分类、因户施策、长短结合、内外兼修的帮扶思路,提出防止低收入家庭返贫需要从个体、区域和制度角度出发,建立多元多层次帮扶体系,以期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可行的发展建议。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J].中国产经,2021,(17).
[2][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M].方福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21.
[3]杭承政,胡鞍钢.“精神贫困”现象的实质是个体失灵——来自行为科学的视角[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8).
[4]和立道,黄璐,刘晓彤.乡村振兴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融合的动力机制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22,(9).
[5]李倩,刘玉超.全面脱贫背景下贫困村返贫阻断长效发展路径探讨[J].农业与技术,2023,(23).
[6]李炜,王卡.共同富裕目标下的“提低”之道——低收入群体迈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途径研究[J].社会发展研究,2022,(4).
[7]廖冰.脱贫人口返贫风险“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防控研究脉络[J].农学学报,2021,(12).
[8]罗楚亮,梁晓慧.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与共同富裕[J].金融经济学研究,2022,(1).
[9]蒋和胜,田永,李小瑜.“绝对贫困终结”后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J].社会科学战线,2020,(9).
[10]潘文轩.贫困地区返贫与新增贫困的现状、成因及对策——基于扶贫对象动态管理数据的统计分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
[11]唐任伍.贫困文化韧性下的后小康时代相对贫困特征及其治理[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
[12]张开云,邓永超,魏璇.党建扶贫质量:内涵机理、评估及其提升路径——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分析[J].宏观质量研究,2021,(3).
[13]左停,李颖,李世雄.农村低收入人口识别问题探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3,(9).
[14]张开云,邓永超,魏璇.党建扶贫质量:内涵机理、评估及其提升路径——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分析[J].宏观质量研究,2021,(3).
[15]Sen A.Development as Freedom[M].New York: Alfred Knopf,1999.
Study on Preventing Re-poverty of Low-income Famil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ve Poverty
Li Chan Lan Yuting Cai Jingchen
Abstract: Eliminating poverty and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are the fundamental pursuit of socialism.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has achieved comprehensive victory, but the problems of imbalance and insufficiency in development still exist. We need to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isk of re-poverty faced by low-income families, especially the phenomenon of re-poverty caused by the temporary and persistent risk. This paper proposes a series of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to avoid re-poverty from dynamically identifying governance targets, strengthening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building effective mechanisms to prevent re-poverty, encourag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activating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low-income families, further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omoting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Key words: Relative poverty; Low-income families; Re-poverty; Preventive measures
责任编辑:程文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