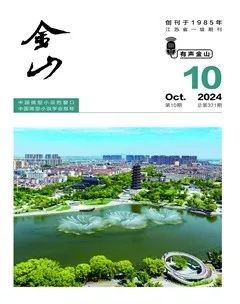雨中,米公祠的蛙声

丁祖荣, 散文作品刊发于《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周刊》《安徽文学》《清明》《作家天地》《金山》等。曾获“昭明文学奖·散文奖”,著有《民意社区》等。
宋朝的雨,淅淅沥沥到现下。米公的书迹,如墨池鱼龙,亦跃跃欲飞。
投砚止蛙
一池的残荷,在雨声里。荷深处,万般禅意,有清风,清风舞动,或舒缓,月影之下的低吟浅唱;或狂疾,有竹,如方戟,指天刺地。
一声清响,是投砚止蛙,还是叩石问天下。听闻人,似会意,不知归处。
临池,登阁,赏碑,拜石。苔痕古意,青藤缠绕岁月。四围烟火,米南宫书之如来,岂止投砚,定当拂袖废园而去。不过,拂不拂袖,岁月斑驳其园。
尔来多少年,江东古城大成殿,江北米公祠,走过看过又造过,难遂米公意。
一祠之长,清瘦,少语,号竹,有节,对米黄苏蔡有识见,对斋,对阁,对碑,对池,有难言之隐。
秋雨绵绵中造访。去不易,四围不只是烟火袅袅,且商业凌厉。祠,逼仄,破败,满是愁绪。
我有一种幻觉,蛙声阵阵如鼓。在韵律中把玩奇石,纵横笔墨,陶然沉醉,何来投砚止蛙?芭蕉有俳句:蛙跃古池内,静潴传清响。传达了生命的惊悟。米公纵逸,虽爱赏石玩砚,当豪情陡起时,在砚上纵笔,阁中逸情,怎比以池研墨,大地写书作画,淋漓酣畅。当投砚,当癫,当对明月泼洒心中快意,抑或愁绪。
蛙声穿越,似古意绵延。投砚,蛙从塘中跃出,是撕破时间之网,仿佛永世眺望。这是砚,蛙,人,天空,大地,昨夜,今晨,互为投射,构筑了一个书人的深沉意象。你还以为米公投砚是止蛙?一个更大的声响,止一时之蛙鼓,待投砚声响和涟漪渐息,蛙声又一片。明月下,清风拂动一池的荷,蛙鸣荷香。纵然时间流逝,今夕何夕?
米公祠多舛。千余年来,一直在毁与建中。相对于书写,求新建大,或如书法中的衰笔和败笔,米芾有知,不只是投砚。米公祠,并不需要多大,安放石碑,安放一段历史,就可以了。
天空阴郁,四围高楼,米公纵逸,祠也难语。不闻蛙声,唯是阴雨湿人。一池残荷,与谁说。怅然。归也无语。
生命的律音
蛙,看似古拙,但跳跃之姿完美。起势,伸展,入水,如一道优美弧线闪过。发出了声响,是生命的律音。
蛙,先于人类而存在。在漫长的演进中,我们无法想象它的卓绝历程。当人类谛听蛙声,发出会心一笑时,蛙连同蛙声入诗入画,历史进入了文明。
蛙,形制最古最异。最古是,蛙类似化石动物有两亿多年的演变。形制虽异,给人感觉却是天然的艺术臻品。
蛙,声音最古。声音的进化,透出生命的气息。它的发声是本能的生命气息,还是在呼唤人类,或是在建构世界。蛙鼓阵阵,群声起,从邈远而来,有破网时间之意趣。发声响,有低沉、有擂鼓、有欢畅。
人在蛙声中极易动情。春雨过后,夜色渐起,清风拂过,蛙拉开了表演的序幕。蛙成了田园池塘的主体。一阵蛙声一种情境,是人在听闻,还是蛙拟人声。蛙声里,人不作前思后想,只是沉浸其中。有思古,则从洪荒而来。思远,人类有蛙相伴,福泽绵绵。在蛙声里,人的情思弦动。
蛙与荷池,与田野最配。蛙,在惬意的时空里,有自主发声、动作。春末夏初,夜晚来临,有一场蛙的盛大表演。蛙,两眼睁圆,透出的光,射向生命深层。先是一蛙引领,咕咕有声,声音渐起,走向高亢,然后,引领群蛙齐声。星月之下,打破宁静,又最静美。人不是这个夜晚的主角,而是听颂者、旁观者、激赏者。
古人最能领会此中真谛。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蛙声里,稻花扬穗,清香飘远。蛙,从蝌蚪而来,抖落历史的尘埃,与人,与天地日月,与河湖大地,保持了最好的生态,形成一个有声、有色、有嗅觉和触角的时空情境。
蛙声一片,不是听取,而是自在。蛙声里,有静,有情。听者,听出了自然的鸣响,和历史的回响。
蛙,从远古来,浸润着日月光华。从蛰伏中醒在当下,创制生命。一只蝌蚪从卵中运化成蛙,跃然于田野池塘中。曾有那么一个时空,米公在池畔写书运思,闻蛙声或其他哪个虫儿声响,幻化成杂音,包括人的声音,投砚止蛙,抑或止人。
砚入水,止蛙,当下声响成了历史回响。米公投砚,是试图把自己的情绪抛水中。初夏,还伴看蝉鸣,连小虫唧唧,可能会扰得你恨不能遁入真空。
当下的蛙,历经万年、亿年。一直蛙鼓不止。跃入池中的声响,表达着诗画般的存在,和昂然生意。
天地间,蛙声,是清响,是生命的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