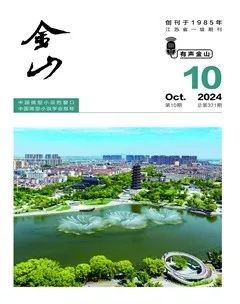一条驴腿的故事

俺老家是丘陵地,产玉米、小麦、豆子一类“旱粮”。要把这些五谷杂粮吃到嘴,少不了石磨,也少不了驴子。磨麦面、磨玉米糁子都是又脏又累的活,人懒得干,就得靠驴子拉磨。小时候俺那里不缺草也不缺驴。一大早,老汉、孩子牵着自家的牛驴上坡地放牧,傍晚归来时,道上牛嘶驴叫,尘土飞扬,算得上乡村一道景。
那年代驴比牛贱,但家境不济的农户驴也买不起。俺村共有十多户人家,单独养驴的只有四五户,其余的搭伙养驴。有两户合养的,也有三户合养的,最不济的四户合养一头驴,每户摊一条驴腿。少数穷得叮当响的户,买不起驴,就靠人力推磨。可推磨也得有石磨和磨房才行。缺驴少磨的人家求爹爹告奶奶受尽白眼。
俺家当属“四户型”,只占一条驴腿。后来有两户生活艰难自愿退养,他们占有的驴腿份子,由我家和戴家接手,两家各占两条驴腿,驴由俺两家轮流养。
俺家的老屋是土改时分老富农的“浮财”,土墙草房,小三间,住人都紧巴,找不到一块拴驴的地方。我哥就在进出大门的走道盖个简易“门楼”,半边走人,半边拴驴。有地方拴驴又没地方放石磨。石磨配上磨盘,占大半间屋,俺家实在腾不出地方装石磨,娘硬着头皮与戴家商议,买了他家石磨一半份子。然而到人家家里使牲口磨面,娘总觉得过意不去,每回就留下一捧半瓢麦麸子给人家喂鸡。
轮到我家养驴了,我就早早地牵驴上岗,把驴拴在水草丰盛的地方,任它尽情吃草,我和小伙伴满坡满岭地爬树摘果。傍晚时分该回家了,驴吃饱了人也吃饱了。夏秋季节还顺带割捆青草回去,晒干留作过冬的驴饲料。驴光喂草哪行,还要喂它瘪玉米和麦麸皮,给它加足营养。娘总是念叨:“牲口不会说话,俺要对得起它。”所以,轮到我家喂驴时,我就给它吃饱喝足,把驴养得油光水滑的。见到人来驴就冲地上打个响鼻,跟着便激起一股尘土和草屑,算是打招呼。晚霞从大门口映照过来,驴一身棕色的毛变得金光闪亮,可好看了。这驴性情温顺,小孩子走近摸摸它的背,甚至捋捋它的尾巴,它从不会乱踢人。驴粪蛋儿也好清扫,不像牛拉粪又多又臭。
每当使驴推磨,娘就忙活起来。娘要把待磨的小麦或玉米以及筛面的箩筛、罩驴嘴的笼头等家什准备停当,一趟趟往戴家磨房送,磨好面还得悉数往家搬。磨房粉尘飞扬,一晚上工夫磨下来,人也成了“白毛女”。有趣的是,磨面时,俺娘不光给驴头套上笼头,还要用块布把驴眼蒙上。我问娘:“为啥要蒙它眼睛呀?”娘答:“咳,见到又吃不到它能不急吗?俺不忍心哪。”有一回,我把“驴脸布”往下拉了拉,驴瞅见磨上的粮食,扭头就吃一口,再也不肯迈步。我赶紧把布拉严实,轻轻在驴屁股上打一巴掌,它又呱哒呱哒地围着石磨转起来。
其实,驴拉磨不光累驴子,人也陪着受累。要不间断地用瓢或手朝磨眼里添加粮食,添少了磨空转,添多了粮食来不及进磨眼,滚得满地都是。非要眼到脚到手到,才能精准不乱。
村西头陈家人口多,负担重,家有石磨却买不起驴,大人孩子轮流推磨。推磨时,磨棍拦腰放肚皮上,双手抓住磨棍,腿、肚、手一起发力,像驴一样转圈圈,磨好了也不知要转多少圈儿。大姑娘小媳妇开头转几圈还嘻嘻哈哈,再转下去就觉得天旋地转,紧抱磨棍不肯松手,一松手就瘫倒了。陈家大儿子的对象上门相亲,晚上两个人躲进磨房里谈。见人来了,两人就合抱一根磨棍低下头推磨,两片石磨吱吱呀呀地空转着,等别人一走,小情侣放下磨棍就香起嘴来,引得窗外的小伙伴嘎嘎地笑,齐声喊:“推呀,推呀,‘驴’咋不走啦?”那阵子,“二人转”就在磨房里上演,有情人终成誊属。
三年困难时期,没粮食磨面,石磨派不上用场。人吃不上好粮,驴也吃不上好料,瘦成皮包骨,走起路来直打晃。驴饿急了,就用蹄子不停地刨土,身下的土都被刨得稀碎,谁都不忍心多看它一眼。戴家无奈地提议:“给驴放放血分了吧!”但娘和我心里一百个不情愿。晚上看着驴倒在地上,连响鼻也打不动了。娘说,留着它,它到底也活不成。娘背过脸,拉扯大褂襟不住地抹眼泪。
驴宰后,娘说服戴家,连骨带皮分给原先合伙买驴的四户人家,一家一条驴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