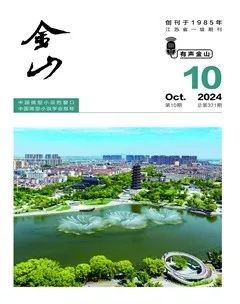渔歌互答

有个农民在基本农田自建了两间小屋,说是用来看鱼的。案件报我这来了,我的心情是复杂的。这个人,是我小叔。
那年我考上了大学,捧着通知书一筹莫展。母亲得病还在县医院里住着,拿父亲的话说,医院是个无底洞。父亲眉头紧锁,今天找舅家借,明日找姑家借。
眼看着入学报到的日期越来越近,我躺在床上,双脚使劲地互相搓着,埋怨着家里的贫穷和无助。
咣当一声,院门开了,进来的是小叔。我爷奶还在他家奉养着,负担花销根本不用说,我连嘴都羞于向他张啊。小叔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家里出个大学生,祖坟都冒青烟了,应该高兴才是,我来想想办法。”
第二天天刚亮,隔墙小叔家猪圈里传来猪叫声。
屠户说:“这猪正长膘,你好好养着,等过年我再来买,太小,太瘦,卖不上价。”
小叔说:“不是我侄子上大学,急等着交学费,打死我,也舍不得卖。你一斤再多出两毛,咋样?”
听着小叔近乎哀求的语气,我的眼泪哗啦哗啦地下来了。
我对小叔是问心有愧的,仅有一次,他到县医院做胆结石手术,我去陪过一次夜。他两个孩子,女儿考上了中师,在乡下当老师,儿子考上了大专,在县城里上班。有次拜年提及,小叔说:“这都是你这个大哥带的好头啊。”他把他在田间耕作,在建筑工地扎钢筋、扛水泥、搬砖头这些辛劳都隐藏起来,把这份荣耀安到了我的头上。
小叔年近七旬时,土地流转了,他闲不下来,主动承包了村里一段白露河故道,养上了鱼。等到年关,却没捕上来多少鱼。他怀疑有人偷他的鱼,在自家田头建了两间砖混结构的小屋,一间睡人一间做饭,他要住这儿看着他的鱼。
镇里排查发现了。小叔说:“我在这野外田边,盖两间看鱼棚,碍谁事误谁事了?什么这法那法的,我不懂。要拆,你让我大侄子来拆。”
镇里人很无奈,不管咋说,我是片长,这事就到我这儿来了。
我到超市买点东西,驱车赶往老家。看着淮南大湿地,水面平躺着绿宝石般的芡实,水上绽放的荷花犹如仙子舞蹈,满河滩落羽杉青翠欲滴,蓝天白云间鸟儿一排排飞过,我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把东西送到小婶手里,小婶要给小叔打电话,我没让,步行穿过河滩野径,到看鱼棚去找小叔。
“哟,你这个大官还真来了。”听锣听声,听话听音,小叔这话里带着刺儿呢。
“走,回家去。”小叔离开看鱼棚往家走,像小时候一样,我调转身跟在后面。
从哪说起呢?我在思考着。还是先让小叔发泄发泄再说吧。
“我那两间屋也就占了两三分地,能收多少庄稼?”小叔果然开腔了。
“小叔啊,我们国家十几亿人呢,种的粮食不够吃啊,还要从国外进口呢,中国是第一粮食进口大国。”
小叔愣怔了一下。
“我们中国人,不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凡事总想着依靠别人,靠谱吗?别说是两三分地,就是盆口那么一块耕地,也得保护啊。”
小叔点上了一支烟。
“这天上有天眼,你建的房子卫星都看到了。你以养鱼的名义建房子,别人也可以以养鸡、养鸭、养鹅等种种理由建房子,蚕吃桑叶,这种庄稼的地,是不是会一点点地被吃掉?”
小叔猛吸了一口。
“种庄稼的基本农田,那是红线,那是高压线,我们家里人都是遵纪守法的。小叔啊,你不是很在乎带好头吗?不好的头你也不会带,这也不是你的做派啊。”
“我快气炸了,下多少鱼,我心里有数,逮的时候少了,长翅膀飞了?今年我不看紧,咋办呢?”
“办法我给你想好了,我出钱给你安上监控,你坐在屋里看得一清二楚,也免得你风吹日晒虫叮蚊咬在河边受苦。”
“好好,这个好。”
我把镇里的同志喊来,把看鱼棚里的家当搬回小叔家里,现场调来机械,拆掉看鱼棚,运走砖渣水泥。挖机一翻,基本农田恢复了。
寒露过后,我接到了小叔的电话:“冤枉人了,冤枉人了,那鱼不是人偷的,来了一群野鱼鹰,天天捉我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