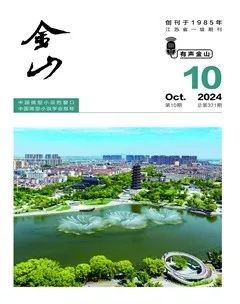三个时段与三篇小小说
附创作谈:
从出生到现在,我的人生大致经历了三段时光,即在故乡生活了19年,在小镇生活了6年,在如今落脚的小城生活了20多年。
生存辗转其间,我与众多熟悉的人、半生不熟的人、陌生的人或朝夕相处,或渐有交集,或擦肩而过,制造着身体与身体的物理接触距离,同时也感受着心灵与心灵碰撞所产生的化学反应,永无休止。
我是个业余作家,平常得撸起袖子加班加点地干活挣钱养家糊口。最近,我好不容易抽闲,利用一点儿碎片化的时间,将脑海里三段时光中长期折磨我的一些人、一些事和一些情写出来,才有了《到西杨岗去喝骨头汤》《钓友》《守望》这三篇小小说。
《到西杨岗去喝骨头汤》这篇小小说,烙有我少年时在故乡生活时的深深印记,以及我家族百年传承的厚重历史。正如文中所述,“听我父亲讲,我爷爷辈,有弟兄两个。我爷爷是老大,曾中过晚清举人,武昌首义后便流落到一个叫西杨岗的地方教蒙童为生,人称大先生。”后来,我也出生在这个名叫西杨岗的地方,从七八岁时开始放牛干农活儿,到十二三岁开始犁田耙地挑草头,深知乡下土里扒食的艰辛与不易。这些,在小说里得以真实体现,“正是犁耙水响的‘双抢’时节。二爷挑着草头往返打谷场已经好几趟了,再回到田头时,仍见大爷躬着身在围着草头打转儿,气就不打一处来”。再后来,我离开故乡参加了工作,不经意间看到了《澴川革命史志》上记载:“1942年6月17日,花园日伪驻军派出一个小分队蹿至西杨岗抢夏粮,当天屠杀群众36人。”我大爷便是其中一个。
今年清明节前,我回了趟老家,途经西杨岗时,但见昔日幽长狭窄破旧的街道,已蝶变成风景独好的美丽乡村,当年日军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的荒坡地,已变成繁华的农贸市场。真是时移世易,沧海桑田,这促使我敲起了键盘。
《钓友》和《守望》,也分别是我在小镇和小城生活两个阶段的一些感悟和心动。比如每天早上,我下楼上班时,最先见到的是小区的保洁员陈阿姨,她总在用扫帚清扫地面上的落叶、塑料袋、纸屑,然后装进手推车里拉走。陈阿姨在小区里干保洁员多年了,虽然薪水不高,但日复一日,风雨无阻,从不间断。那天,天气突然降温,她见我穿得比较单薄,就停下手中的活计对我说:“天凉了,可要多加件衣服哟!”一句话,顿时让我感到天不是那么的冷了。
城东菜市场里的胡屠户,是我很佩服的一个人。他不仅长得人高马大,而且颇有点儿《水浒传》里人物镇关西的手段,无论是切肉臊子还是剔排骨,但见他出手如风,刀光霍霍,砧板顿响,且你要割的猪肉几乎不用秤称——即便复秤,也是分毫不差。我多次亲眼所见,凡遇到老爹老妈来割肉时,他总会为他们额外添上一小块肉,或一截筒子骨。
一楼开小超市的平头儿,来自乡下,我家的油盐酱醋茶乃至手纸,差不多都来自他的店。记得第一次进到他的门店买烟时,他边拿烟边笑着劝我说:“大哥,知道你经常熬夜,可还是要少抽点儿烟,抽多了对身体不好哇!”说实话,我还从没见过如此开店做生意的人。自此,我就喜欢上了他的小店。今春,他还邀我到他乡下的家里做客。那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们并躺在河边的草地上,美美地睡了大半天。
那个河南来的在火车站旁边开拉面馆的张大胖儿,不仅做的拉面筋道,而且碗大,牛肉多。隔三岔五的,我会和爱人一起,步行三四里走到老城区,找到他的店面,大汗淋漓地吃上一大海碗热辣辣香喷喷的牛肉拉面。去年,到外地学习期间,梦中磨牙,饥肠辘辘,细思深想,原来竟是想念张大胖儿的牛肉拉面啊。
……
无论是我生活过的小镇,还是现如今生活的小城,都是我和他们共同生活、守望相助的美好家园。譬如哪天出门,你眼里突然不见了陈阿姨、胡屠户、小平头、张大胖他们,你心里肯定会发慌:他们都到哪儿去了?
普鲁斯特说,真正的旅行,并不是去往多么新奇的地方,而是拥有另一双眼睛,以别人、成百上千个别人的眼光,来观察这许许多多人看见的成百上千个世界。
这句话让我受益匪浅。我将会在今后的写作过程中,继续坚持从我熟悉和我擅长领域入手,在现实和历史题材方面继续深耕,在一些不起眼和不经意的地方着墨,拿放大镜深究细探,来发现世间万物固有的独特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