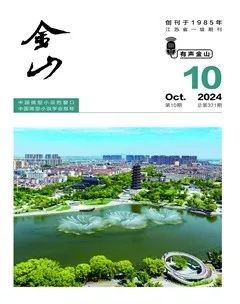麦浪闻莺微型小说三题
麦浪闻莺,本名谈旭华,中国作协会员。自2014年以来专注于微型小说创作,作品散见《小说月刊》《长江丛刊》《金山》《辽河》《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传奇·传记文学选刊》《微型小说月报》等,先后荣获第14届、第17届中国微型小说年度奖,出版微型小说作品集《梅姨的二十五里花园》《别人的阳光》。
到西杨岗去喝骨头汤
父亲说:“你爷爷辈,有弟兄两个。你爷爷是老大,曾中过晚清举人,武昌首义后便在乡下教蒙童为业,人称大先生。你二爷呢,人称二杠子,三十多了还没娶媳妇,一直帮你大爷勤扒苦做养活一家人。我那时也就十二三岁吧,也没钱去念书,只得到西杨岗地主老财杨百川家去放牛混口饭吃。”
其实,无论是我大爷还是二爷,我都没见过。因为他们去世时,我还没出生哩,什么事都是后来听我父亲讲的。
我这两位爷,身板都不算太高,也就一米六吧,容貌也相似,都是小头小脑的,但脾气不像。大爷性子温暾,做事慢条斯理,还张口“子曰”闭口“诗云”的;二爷肠子直心眼实,做事风风火火,说起话来像木杠两头一般粗。
大爷租了杨百川家的几亩田来种,立夏前种早稻,立秋抢插晚稻,秋收后还要赶播一季冬小麦,一年四季的农活儿多得像葡萄串一嘟噜一嘟噜的。大爷不擅干农活,也不屑做这累得血喷心的苦力,所以总变着法子耍奸偷懒。
正是犁耙水响的“双抢”时节。二爷挑着草头往返打谷场已经好几趟了,再回到田头时,仍见大爷躬着身围着草头打转儿,气就不打一处来。
二爷吼:“哎大先生,您做什么呢?拿着草腰子围着草头转圈,难道是要绑猪杀吗?”
大爷干咳说:“非也,非也。这一担草头有一百多斤重,我挑不动哩。哥拿草腰子匀一匀,好把一担分作两担挑。”
奶奶踮着小脚给大爷摇蒲扇,说:“就是,把一个草头杀成两个草头,你哥才挑得动。哎大先生,可别累着了。”
二爷的鼻子都气歪了:“嗬,小姐摇扇,先生做秀,这哪是干活儿的架势?都滚吧,别再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大爷立时羞愤难当,便一家伙扔了冲担说:“兄弟,好生无礼!好,我滚,就滚到西杨岗去喝骨头汤。二杠子,那这些草头,就拜托了!”说着还朝二爷作了一揖。
西杨岗街上有几家肉案子,其中一家黄姓的肉案除了卖肉外,但凡逢双日的大集,还免费赠送些骨头汤。骨头汤是用架起的大铁锅熬煮的,几根排骨、筒子骨在锅底劈柴的加持下不停地翻滚,诱人的肉香味就迷漫了整条街。大爷换上长布衫,步行大半个时辰后就来到了汤锅前,从怀里摸出十几个铜子,再打上二两吊酒切上二两烤馍,然后就着一碗骨头汤滋润地喝起来。末了,还不忘给二爷也拎上一瓦罐。
大爷租的地与杨百川的田紧挨着,中间仅隔道狭长的田埂。杨百川做事绝,暗地让长工在犁田时不断地削田埂,后来越削越细,硬是把大半个田埂给削到他家了。二爷看不过,便去找杨百川评理。
杨百川耍横说:“我削你的田埂?那泥埂上可有你的名字记号?别忘了,就连你家租的地,也是我杨家的!”
二爷被呛得面红耳赤,就冲上去想揍杨百川一顿,结果反倒让人家给打得半死。
大爷就请来镇上的郎中闵三先生,给二爷看伤。闵三先生看后直摇头,说这伤淤在心里,难治啊。
闵三先生是镇上的名医,说话向来一言九鼎,他说难治,就等于给人判了死刑。大爷一听便哭:“好你个二杠子呀,你跟杨百川杠什么呢?杠命吗?都怪哥无能,至今还没给你娶个媳妇哩!呜呜。”闵三先生不忍,又撂下几副草药说:“这些药吃吃看,好便好,不好便拉倒。如果他想吃什么,可别省,说不定以后就吃不成了啊。”
草药一天天在减少,二爷也一天天在消瘦。奶奶记起了闵三先生的话,含泪问:“二兄弟,你还想吃点啥?”二爷嘟噜着喉结,语焉不详。大爷坐到床沿,紧握住二爷爷的手说:“兄弟,你是说,明天是不是西杨岗的集?哦,你是想喝骨头汤吧?”
第二天一大早,大爷抱着瓦罐去了西杨岗。到了中午,大爷没回来,瓦罐却回来了,是邻居肖福清抱回来的——
据《澴川革命史志》记载:1942年6月17日,花园日伪驻军派出一个小分队蹿至西杨岗抢夏粮,屠杀群众36人。我大爷便是其中一个。
肖福清说:“大先生本来是跟我一起逃跑的,但他抱着罐子,怕洒了骨头汤,就落在了后面,被鬼子追上,一刺刀给挑了。等鬼子走远了,我才敢从田沟里爬出来,找到奄奄一息的大先生,他还抱着罐子不放。大先生说,这汤一定要带回去,给二爷喝。说完了,便断了气。”
土黄的瓦罐,已经染成血红色。奶奶掀开盖子时,骨头汤还有些热气,用筷子搅了搅,里面还漂着几片猪肉。
喝了骨头汤,再吃几副药,半月后,二爷竟神奇地下地了,又活了三十多个春秋。
是夜,杨百川家里突然失了火。
后来,我父亲投奔了在大悟山坚持抗战的新四军,直至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今年清明时节,已是95岁高龄的父亲要去再给二位爷上一回坟。
大爷和二爷的坟紧挨着。两堆纸钱刚烧着,风一吹,烟灰便合到了一起,飘上了天空。
父亲咧着干瘪的嘴巴笑:“肯定是你两位爷拿了钱,一起去街上喝骨头汤了。”
钓 友
三十年前,我在青山镇村镇建设办工作那会儿,月薪是135块钱。由于单位没房住,我便在街北头找了间小民房,月租是35块钱。这样,我就认识了房东周师傅,以及周师傅的钓友老宋老陈老李他们。
周师傅和他的钓友,都是镇上铁器厂、木工厂、拉管厂的职工,他们喜欢在周末搭伴去钓鱼。我没事儿时也会跟着去玩儿。
有一次,我、周师傅、宋师傅同行,每人骑一辆二八式载重自行车,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后不紧不慢地骑行。借着依稀月光,迎着微微细风,我静听他们闲聊。
周师傅:“今天的运气,看来还是不错的,是吧老宋?”
宋师傅:“是啊,没瞧见我们的网兜都装满了吗!”
周师傅:“哎,老陈咋样了?算日子,应该早回家了吧?”
宋师傅:“嗯,上个礼拜三出的院,是我和老李接回来的……”
然后是一路沉默。这种气氛,让我敏感地意识到,老陈应该是得了什么病,似乎是很严重的那种。也难怪最近一段时间,没见着老陈参加过一次钓鱼活动。
周师傅:“他本人晓得病情不?”
宋师傅:“唉,应该还不晓得吧,都瞒着他。现在,他可瘦了,瘦得不成个人形……”
之后,二人再无片言只语,猫着腰身奋力蹬车,似乎前方有天大的急事儿在等待他们一样。
事后我才知道,进入街北分手后,他俩再拐道一程,专门给老陈送鱼去了,想让没能参加野钓的老陈也分享一下钓鱼的喜悦,或者让老陈卖些鱼获换一点钱用。
后来,只要有鱼获,周师傅宋师傅他们准会给老陈送一份。
事情的转折,出现在第二年的夏末。
那时,周师傅只要有时间就会去看老陈,但回来后我总能感觉到他情绪低落。几个钓友跟我也慢慢地混熟了,他们有关老陈的话题,再也不避讳我。从他们的交谈中,我得知老陈又住院了,好像是癌细胞扩散了。
秋天来了,这是个钓鱼的好时节。没想到,周师傅宋师傅他们见面,现在交流探讨最多的倒不是去哪儿钓鱼,而是一有空就研究起沙子、水泥、砖头和木料的价格来,以及到哪儿去买能节省一点钱。因为,他们见老陈家的土坯房年久失修,想帮着老陈尽快完成修补翻新的心愿。大家都在镇办企业工作,工资不多,多是半边户,而且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本就过得紧巴巴的,能凑一两个子儿实属不易。这份心思,这种算计,我懂。
最终,在大家的集思广益和共同努力下,老陈家翻盖房子的物料终于备齐了,接下来就是施工了。这下,可就辛苦周师傅宋师傅他们了。他们白天要在厂里上班干活,下班后就得赶紧扒一口饭,或者饿着肚子直奔老陈家,搬砖的搬砖,砌墙的砌墙,抹灰的抹灰,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连续挑灯夜战,硬是把老陈家的破房子翻了个底朝天。
我最后一次见到老陈,是转年后的春末。
听说龙泉村的一个鱼塘周日将正式开竿迎宾,前两天上班时,周师傅曾特意嘱咐我提前去探探路,让我选一个好钓位,他们要好好地请老陈去钓一次鱼。我欣然领命,并在周日那天一大早就去占据了一个最平坦的位置。
都上午九点半了,周师傅他们还没到,我的那个心焦哇。那时候通信还不发达,连BP机都没有,更别说移动电话了,干着急也没用。好歹等到十点半,我才等来两辆出租车。出租车那时也是个新鲜事物,估计也要吃掉周师傅一个月的工资。第一个下车的是周师傅,然后是宋师傅他们。他们先摆了一张竹躺椅在第二辆车的门前,然后一边一个抬出了一个人。直到那人勉强冲我笑了一下时,我才认出那人是老陈。
老陈瘦得完全变了相,脸黑黄黑黄的,眼窝深陷,曾经铁塔般的身材只剩下一副骨架,衣服穿在身上显得空荡荡的。一路车程的颠簸,好似已耗尽了他的全部体力,只能靠在躺椅上微微喘气。
周师傅说:“你还愣着干吗?还不快把钓位让出来!”
我连忙说:“哦,我早已准备好了……”
宋师傅佯装微笑:“老陈哪,这个位置好哇,可以安心开钓吧?肯定能钓到大鱼的!”
老陈有气无力地拱了一下双手,表示同意。周师傅也嘎嘎大笑起来:“老陈哪,我先帮你盯着啊,关键时刻你还得亲自上手哦!”
一个月后,老陈安静地走了,同样是周师傅他们帮着料理的后事。
再后来,老陈家上初中的女儿陈楠成了大家的孩子。我不知道周师傅宋师傅李师傅他们背后具体做了些什么,但是在三年后,陈楠成了拉管厂里的一名正式职工。
现如今,陈楠的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了,她的周姥爷、宋姥爷也已经到了耄耋之年,李姥爷、余姥爷已经作古。我回镇上时听说,每逢节日假期,陈楠都会带着家人去看望她的几位姥爷。
至于周师傅和宋师傅他们,有时还会搭伴儿,骑上电驴子去钓钓鱼。有了鱼获,他们还会给陈楠送去些,好像他们已经习惯了像一家人一样的生活。
守 望
老余是我邻居,他在一楼开了个卖烟酒副食的便利店。
我住上面的五楼。这样,我就免不了隔三岔五地要到他的小店买包烟抽,拎两瓶啤酒喝,或者拿个快递什么的,一来二去便相互熟稔了,才知道老余是个退伍老兵。因为他儿子在德城安了家,所以他跟他老婆就迁过来了。
老余面相憨厚,常穿迷彩短袖,待谁都热情,大家都很喜欢他。
有一回,我跟老余喝酒喝高了,他就兴奋地讲起他老婆静静来。
静静以前是一家体校的老师。那年“八一”前夕,在参加军地联谊活动时,他遇到了跟他分在一个组的静静。老余是连队上有名的散打高手,面对娇柔可人的静静上场时,他不愿意比试,就想悄悄地溜掉。静静呢,好像也存了心,冲上来一把扣住他的手腕,再来一个漂亮的“过肩摔”,硬是将老余当场拿下。两年后,静静成功地转型为军嫂。
讲到这些过往时,老余的嘴巴咧到了耳朵根儿。
静静便蹙眉嗔怪:“哎,都这把年岁了,还提这个,羞不羞呀?”
老余的便利店不大,本来也没多少活计,由静静一个人打理就足够了。他便琢磨着,自己得找点事做,不然闲得慌。
起先,老余拿起扫帚,每天天不亮就开始在小区里帮保洁阿姨们扫地。这个活儿,他在部队可没少干。没想到几天后,几个保洁阿姨不高兴了,找到他说:“经理说了,如果我们再整天无所事事的,那我们就全得下岗……”
老余吓了一大跳,再也不敢拿扫帚扫地了。
小区是分期开发的,我们这一期已经交楼了,那边围墙里还在加紧建。老余七转八转,最终就在围墙边选了块还未绿化的空地,随即挥锄舞锹,开垦起菜园来。末了,他还大费周章地捡来一些废砖头和破板材,在菜园边盖起了一个简易的小木屋。用老余的话来说,就叫一搭两就、一举两得。
哪知后来,这事儿竟被人举报了。
那天,来了几名执法人员,围着菜地转了一圈后说,在公共空间开菜园盖木屋,肯定不合适。
于是,执法人员开始现场拍照取证,做询问笔录。
老余郁闷地蹲在地上,耷拉着脑袋,问一句答一句。最后轮到摁手印时,他把双手揣进裤兜里,死活不愿掏出来。
眼见双方僵住了,静静赶紧悄悄叫来社区的主任。以前,这里是城中村,这个主任实际上就是原来的村长,说话向来一言九鼎。主任就说:“地都征收完了,现在侍弄个劳动实践基地,好让孩子们知道蔬菜是怎么长出来的。这件事,老余跟社区汇报过,我看就算了吧。”
一大帮邻居也纷纷帮腔说:“开个小菜园,也不是什么大事。以后要搞绿化,把菜地铲了不就行了。”
这事儿,就这么囫囵过去了。
为这,我还专门去看了一回老余劫后余生的小菜园,但见平整的菜畦上,翠绿的空心菜正在拔节疯长,红绿相间的番茄一嘟噜一嘟噜地挂在藤蔓上,已经吐了穗的玉米棒像一杆杆红缨枪直指晚霞……
小木屋前,早聚拢了一大群纳凉的邻居和小孩。老余忙不迭地搬凳子请大家落座,为大家泡茶续水,还请大家品尝新摘的黄瓜。他乐呵呵地指着一大堆已经掐根、去叶、摆好的空心菜、红番茄、玉米棒说:“大伙儿可要常来喝茶乘凉啊,想吃啥蔬菜可以随便摘随手拿啊!”
我也拿了根黄瓜咬了一口,真是清脆爽口无比。
可能是天气太热的原因,老余把裤腿卷了起来,我便瞅到他右腿肚上有个凹陷的大伤疤。
我丢了根烟,问:“哎老余,你右腿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老余接过点上,云淡风轻地说:“嗨,不就是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一不小心让水底下的钢筋给穿了个大窟窿嘛。早没事了。”
还有一件事,是另一个单元的老陈讲的。老陈说,有个租六楼住的小姑娘,经常随手乱扔垃圾,有一回他还跟老余聊起过。老余摇头劝他说:“小姑娘还是个孩子嘛,一个人在外打拼也不容易,再大点就懂事了,你莫要见怪。”
一天深夜,老陈听到楼下那姑娘的哭泣声,还有老余的断喝声。
原来,是那个经常乱扔垃圾的小姑娘下晚班回家,发现身后有个醉汉一直尾随着。小姑娘吓得大哭,慌忙向前跑,正好遇到浇菜归来的老余。老余咣的一声扔了塑料桶,随即一声大喝,还举起大铁锹,那醉汉赶紧掉头跑了。
可以说,老余在我们小区里是攒足了人气。
后来,我们这幢楼选楼栋长,老余以满票当选。
今年开春后,因为工作忙,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见过老余,就想到菜园去会他一会。
老余不在,却见老陈、老李、小姑娘他们,都在菜园里忙活。
老陈说:“老余回河南老家处理事了,估计还得个把月才能回。”
我说:“那他的菜地呢,怎么办?”
老陈他们说:“我们一起帮老余种呀,而且还要确保种得比老余在家时还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