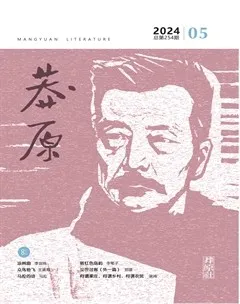呼吸之间
一
宋小梅刚把老父亲全身上下擦洗好,捂好被子,还来不及直腰,手机就响了,铃声催命似的一声紧过一声。
这个时候打电话来的,不是广告推销就是杨成波。宋小梅拢了一下散乱的头发,摁住心里的小火苗,拿起手机,果真是杨成波。“芮儿去年给我寄回来的那件羽绒服怎么找不到了?我今天要穿!”那边估计急着出去,找衣服找了好一阵了,没找着,再加上前些日子的冷战积怨,语气里的火药味儿已经透过手机传过来了,就等宋小梅点引线。
宋小梅正要让杨成波如愿以偿,床上的老父亲轻轻咳嗽了一声,艰难地翻了个身。宋小梅深吸一口气,轻轻说:“在衣柜的右边最顶上那层,用压缩包装着的几件羽绒服,都是你的。”
杨成波挂了电话。这个男人最近这些天跟她通话都跟被狗撵了似的,以前起码还有个开场白和结束语,比如“宋小梅,是我呀”,“好的,那我先挂了,你早点儿回来”等等,现在总是快速直接地表达完自己想要表达的,得到了答案,就匆匆收线,而她有些想说却来不及说的话就跟鸡骨头似的卡在喉咙中,下不去吐不出,差点儿被噎死。
噎多了也就习惯了。宋小梅转身把手机扔在父亲对面自己的陪护床上,去厨房帮老父亲准备午餐。父亲八十九岁了,四年前第二次中风,瘫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语言能力也退化成幼儿园小孩的水平,幸好还能吃能喝,生命暂且无忧。
“我怎么还不死呢,早就该死了……拖累了你们。”老父亲每天都要重复这句话。宋小梅知道老父亲心怀愧疚,四个儿女年纪都不小了,还要轮班来照顾他,他过意不去,每次儿女们帮他洗完澡或抠完大便后,他都要说谢谢。
“谢什么呀爸,我们小的时候你也是这样照顾我们的。”宋小梅总是如此宽慰父亲。有一次帮父亲剪指甲,她握着父亲的手,第一次翻来覆去细细地看,那双手皮包骨头,油纸一样的皮肤上面布满老人斑,青紫色的血管突出来,像是要顶破那层脆弱的纸。这双手,让她想到了冬天风干的树枝。当年的父亲,高大壮实,凭一双厚实的大手,在单位开大货车养活全家,是他们兄妹几个的天,现在的他却缩在被窝里,形容枯槁,靠他们几兄妹扶来抱去才得以存活。时间是个心术不正的魔术师啊,宋小梅想。
宋小梅有时也很不解,父亲的生命力怎么如此顽强。有几次,因为感冒和肺炎,医生都下了结论,老爷子这次是活不长了,但每次他都能奇迹般挺过来。邻居张大妈羡慕地说,还不得亏你们四兄妹服侍得好,这辈子我就没见过这么孝顺的子女。说完这话时,张大妈总是要叹口气,宋小梅明白这口气里含着未说出口的其他意味。七十有六的张大妈一个人独居,一个儿一个女,都住这个城市,但十天半月也不回来看她一次。
对于张大妈的羡慕,宋小梅是很受用的。除了父亲本身的顽强,他们兄妹几个的细心服侍当然功不可没,这一点一直让宋小梅引以为傲。四年来,父亲没长过褥疮,他的房间里更是没有异味,不吹牛地说,整个G城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家庭来。
一周七天,宋小梅两个姐姐轮头四天的班,周五大哥照看,周六周日轮到宋小梅。大家齐心协力,谁有事了就换换班,没有扯皮推搪的事情发生。所以,老父亲一边说着“我怎么还不死呢”,一边很配合地活着。
当然,也有人有怨言,那个人就是杨成波。
“把你妈伺候走没两年,又伺候你爸这么多年,你自己过几年都六十岁了,还这样熬更守夜,估计把你们都熬病了,你爸还死不了。这个家你到底还要不要了?”这两三年来,杨成波隔不久就要阴阳怪气地说这么一句,估计是忍无可忍了。
“你妈,你爸”,说得多生分。宋小梅心情好时不理他,说烦了就顶一句:“没让你伺候,也没对你的生活造成影响,你哪儿来那么多意见?”
“周末两天我总无人过问,你说影响到我了没有?”杨成波气鼓鼓地瞪着眼。
如果此时宋小梅识时务,闭嘴走开,杨成波一般再发泄两句就平息怒火了,要是宋小梅敢迎头再顶,那就捅了马蜂窝了。
宋小梅感觉杨成波自从做了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后,越来越不讲理,他身体里多个支架,就好像多了架机枪,谁不小心触痛了他哪根神经,那机枪就要朝对方扫一梭子子弹。
两年前,杨成波还是杨老板,手里有两家餐厅,每天忙得工蜂似的,早出晚归。一次应酬后回来,洗澡时晕倒了,幸好不是周末,宋小梅在家,赶紧打了120,检查后,医生说,是心脑血管出问题了,说通俗点儿,就是心脑血管堵了,多亏送得及时,无大碍。住了半个月院,出院时,身体里就多了个支架。医生说,戒烟戒酒戒激动戒夜生活,不然第二次发病就不是放个支架的问题了。
杨成波很受震动,跟宋小梅说,别到时钱在银行,人没了,辛苦大半辈子了,划不来。烟酒虽没戒彻底,偶尔还抽点儿喝点儿,但他再也不出去应酬了,隔了不到半年,把餐厅也转了出去,以五十六岁的“低龄”,退休了。
杨成波这几十年最大的爱好是挣钱,现在钱不能挣了,虽不愁吃喝,但受制于身体的毛病,不敢轻举妄动,终究觉得生活里少了点儿什么,日子过得很烦闷。周一到周五,宋小梅在家,早、晚他就让宋小梅陪他散步,宋小梅周末两天服侍老父亲,平时在家弄一日三餐做家务,体力透支,严重缺觉,这几天最大的愿望就是补觉。于是,就有了冲突。
“你眼里只有你那个家和你爸,让你陪我散个步,跟绑架你似的。老伴儿老伴儿,你伴我什么了?”杨成波很委屈。
宋小梅哭笑不得:“照顾我爸是我分内的事啊!散步这个东西又不是打羽毛球跳交谊舞,非要两个人才弄得起,一个人去不是照样看风景?”
“跟你讲不通,爱去不去。”杨成波气冲冲地自己出了门。
宋小梅也很无奈,谁不想过逍遥日子呢,劳累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挨到退休,她也想每天跳跳广场舞,两口子旅旅游,或者学点儿以前没时间学的技艺,比如插花、茶艺、水彩画之类的,让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有质量,可是现实不允许。
老父亲瘫在床上的第二年,恰逢大姐添孙子,二姐又查出糖尿病,大家各有各的忙,他们商量着为老父亲请了个保姆李大姐,轮流盯着试用了一个星期,觉得四十来岁的李大姐做事细致到位,大家很满意,便不再排班,谁有空就去瞅老爷子一眼。宋小梅难得清闲一点儿,跟杨成波去澳大利亚看望女儿小芮,前后十来天的时间,回来后,去父亲家,发现父亲瘦了一圈儿。
宋小梅以为父亲受保姆虐待了,网络上不是经常有这样的新闻吗,保姆不给吃不给喝,还大耳光扇老人。她背着保姆悄悄问父亲,父亲摇头不说话,只抓着她的手定定地望着她,孩子似的掉眼泪。
“不哭不哭,哪里不舒服你就告诉我嘛!”宋小梅被哭得心里熬药一样难受,她边帮父亲擦泪边哄。
“你不来……看我,丢下我。”父亲抽泣着说。
宋小梅自责不已。她压住心里的火问李大姐,父亲这些天的情况怎么样,李大姐说,她尽心尽力了,是老人自己吃得少。“你没过来,你哥你姐也来得少,他天天哭,搞得我也很担心,好像我虐待了他似的。”李大姐一肚子委屈。
那天,宋小梅住在家里,跟着李大姐一起照料老父亲,彻底领教了老爷子的孩子气。有宋小梅在旁边,保姆喂饭他不张嘴,宋小梅接过碗来喂,他就大口大口吞。也不让保姆帮他擦身子,非得宋小梅亲自动手。做完这些后,老爷子眼含热泪说,小梅,谢谢你。
第二天,李大姐就提出不做了。她说得也有道理,她说,老爷子生怕你们不管他,你们不来嘛,他难受他折腾;你们天天来嘛,请保姆的意义又不大了,花费还不少。不如你们自己照顾算了。
跟哥哥姐姐们商量后,大家征求老爷子的意见,听说保姆要走,老爷子什么也没说,只是咧开没几颗牙的嘴笑了,口水趁机从嘴角滑出来。
兄妹几个只得又开始排班。开家庭会议那天,杨成波提议说,要不送养老院得了,大家都轻松点儿。以后养老院养老是大趋势,你我将来都得去,不能光指望子女。
宋小梅首先表示反对。老爷子同小区有个患直肠癌的老人,手术本来很成功,家里人照顾了几个月,眼见一天天好起来,子女松了口气,送老人去了养老院,半年不到,老人走了。宋小梅想,以父亲这种依赖子女的程度,你送他去养老院,就跟送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去幼儿园一个道理,唯一的不同是,孩子送过去是成长,老人送过去是加速衰亡。宋小梅是家里最小的女儿,父亲当年最疼她,她对父亲的感情更胜过死去的母亲,一想到老父亲在养老院床上无助地等护工来喂饭和换尿不湿的样子,心就揪扯着痛。
宋小梅说:“我们将来上养老院,那是大势所趋,以后再说。我爸跟我们不同,他有四个子女,大家辛苦一点儿,还是能照顾得来。养老院再好也无法完全替代儿女,你没法苛求他们像家人那样一对一地尽心陪护吧?一个护工管几个老人,顾得了这个顾不了那个,更别谈情感和心理上的宽慰和疏导,本来就都是身体有恙的人,积郁多了,自然垮得快。我想尽力让爸活得久一点儿,他在,我们这个大家庭就在。”
大哥和两个姐姐若有所思地点头。杨成波讨了个没趣,不说话了,面露不悦,起身去阳台抽烟了。
杨成波的父母走得早,杨成波没怎么伺候过老人,他偶尔跟宋小梅回去看望老岳父,回家的路上就边开车边摇头感叹,说:“我将来要活成这样,我自己吃安眠药死了算了。”
刚开始两次,宋小梅由着杨成波感叹,没接话,最近这次没忍住,顶了他:“话别说得太早,人到了这一步,由不得自己。想吃安眠药,那你也要能爬起来拿到药瓶和水才行。”
“想死总有办法。”杨成波很笃定地说。
各人有各人的活法,真到那步,你想死,我不拦你,但人家未必要跟你一样。宋小梅把头扭到一边看车窗外的风景,在心里嘀咕。
这两三年,因为老父亲,宋小梅越发觉得她和杨成波心思不在一个频道上,生活习性也不在一个频道上。这一点,杨成波也觉察到了,他常说宋小梅不像前些年那样温柔体贴听话了,总是跟他对着干。年轻时各忙各的工作,主要是杨成波忙得在家的时间太有限,倒没有发现彼此这么不同步,现在发觉了,双方都感觉受了生活的欺骗似的,满肚子的不得劲。
来来回回摩擦久了,两人都有点儿心灰意冷。周一至周五,杨成波就在家喝茶刷抖音,学年轻人网购,等着收快递;周末,就组几个爱打麻将的老同学,男男女女,来自己家聚会打牌。如果不是前几天碰到以前的同事,宋小梅以为她和杨成波都已经适应两人目前的相处模式了,后半辈子就可以这样相安无事地走下去了。
二
那天是个节令,大雪。虽然南方已久不见雪,但冷是实实在在的。上午,帮老父亲洗好喂好,宋小梅累得腰酸背疼,衣服也懒得换,穿着厚厚的棉质家居服就去菜市场买菜了。逛了半个多小时,买了父亲爱吃的水豆腐和大胖鱼头,准备中午给他做鱼头豆腐汤。在选青菜时,意外碰到退休前的同事安姐也蹲在菜摊儿前。
两人各选了把青菜,出了菜市,找了个宽敞的地方亲热地聊上了。
“小梅,你看你现在多幸福,听说你家老杨也退休了,难怪昨天晚上看到你和老杨在南门广场散步,我远远看着,也没敢上前去打扰你们。不过,老杨倒是胖了不少。”安姐说。
宋小梅一脸蒙,昨天是周六,晚上她在东门父亲家轮班呢,哪时分身去南门跟老杨散步了?老杨胖了不少倒是真的。她脑子里快速转着,脸上的笑意不敢掉落下去。
见宋小梅微笑着没接话,安姐又说:“昨天晚上那身大衣蛮配你,今天怎么就穿成这样逛菜市了?我们女人啊,走哪儿都得打扮,把自己最美的那面亮出去,你看我,逛菜市还化妆的。”安姐边说边凑近,让宋小梅看她那闪光的大耳环。
宋小梅被安姐身上的香水味儿呛了一下,打了个喷嚏,她尴尬地用手捂着,揉着鼻子说:“安姐,我家灶上还炖着排骨,改天我打电话给你,请你出来喝油茶。”安姐高兴地答应着,她挥挥手匆匆走了。
炖鱼头时,宋小梅有些失神。安姐能看错她,说不定也会认错杨成波,毕竟大家上次见面是在另一个同事孩子的喜宴上,这都隔了大半年了,认错也有可能。但是,杨成波这大半年来确实胖了近十斤,也确实爱去离家不远的南门广场一带散步。
莫非杨成波以前那些拈花惹草的老毛病又犯了?三十来岁时,杨成波下海做生意赚了点儿钱后,有阵子跟他生意场上的某个女人传过风言风语,宋小梅质问过他,他死不承认,只说是他的一个供应商,来往频繁了些,被人开玩笑传瞎话。宋小梅半信半疑,为了试探他,也为了表明她的婚姻领土神圣不可侵犯,她用离婚相威胁,杨成波这才慌了,写了保证书,答应再不与女供应商往来。那时,宋小梅还年轻漂亮,走在街上回头率不比二十来岁的小姑娘低,工作也过得去,是本市一家国企的后勤人员,在杨成波面前,她是有底气捍卫主权的。再加上杨成波对她也不错,挣了钱上交,唯一的房产署她一个人的名,过年过节都送小礼物,对她父母兄姐也还算关心,这些,都是宋小梅的定心丸。最重要的是,宋小梅没抓到确切证据,此事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四十来岁时,又有过一次。据说是他餐厅的楼面经理。宋小梅为此专门去餐厅查过岗,那个经理长得有点儿妖气,不到三十岁的样子,妆化得浓,上班时间穿旗袍,说是工作服,走路一摇一摆的,屁股扭得很是夸张,见到宋小梅,也不知收敛。她不像别的员工那样叫宋姐,她好像要显得与众不同,她叫宋小梅嫂子。她说,嫂子,你找杨哥吗,他刚出去办事了。工作场合,杨哥都叫上了?宋小梅冷笑,小妖精到底还年轻,肤浅又嚣张。
当天晚上问杨成波,他还是死不承认,说她疑神疑鬼,心眼儿没有屁眼儿大:“你别听外人瞎说,人家那是嫉妒我们,一心想要搞散我们这个家!你想想啊,女儿都成年了,我能做出这种事?我在她心中的形象还要不要了?”他说得正气凛然,仿佛受了天大的冤屈。宋小梅不哭不闹,冷眼看他演,说:“做没做,你自己心里有数。”
杨成波到底没扛住,冷战两天后,他主动告诉宋小梅,他把那经理开了。“不信你去查实。为了消除你的疑心病,我牺牲了一个得力员工。”
宋小梅知道杨成波心里有鬼,以她对他的了解,他要是心里不虚,是不会为她的“无理取闹”让步的,他这是不打自招,只是招完以后,他还要虚张声势地掩盖一下,以彰显自己的大度和清白。看透杨成波的花花肠子后,宋小梅再一次想到了离婚。她考虑了一晚上,天明时又放弃了这种想法,女儿小芮正在读高三,正是全力以赴的时候,她不敢拿女儿的前途来换自己的骄傲和尊严。
这些破事儿,她从来不敢跟父母讲。在父母眼里,杨成波能挣钱,对她和孩子好,就是有点儿大男子主义,脾气差了点儿,但哪个在外面做大事的男人没点儿脾气呢,忍忍就过去了。她不想让上了年纪的父母焦虑,幸福婚姻这个表象是个滤镜,她想让父母看到他们乐意看到的美好。
或许是年岁渐长,后来,倒是再也没听说过他在外面有什么动静了。
心里有事,周日这天就过得特别慢,宋小梅有点儿坐立不安。老父亲好像有所察觉,在宋小梅喂他吃晚饭时,边大口吞边含糊不清地说:“小杨是不是有事烦你?晚上就回去吧……我一个人在家……行的。”
宋小梅摇头,把饭碗放下,给他倒水喝,让他放宽心,慢慢吃。父亲身体瘫了,但心没瘫,甚至比一般老人思维更清楚,很多事都瞒不了他,只是他没办法像以前那样自如地表达。他只用关切的眼神追随着宋小梅的一举一动,比以往更努力地配合小女儿的服侍。
周一一大早,宋小梅还是有点儿按捺不住了,等大姐来接好班,她没像往常坐公交车回家,而是打了出租车。
杨成波正准备出门,说出去吃早餐。
“家里有面条,我也没吃,我做好一起吃吧。”宋小梅放下包就扎上围裙去了厨房。杨成波迟疑了一下,说算了,在外面吃完顺带去散散步,消化消化。
宋小梅看了他一眼,没强求。他平时出门吃早餐都是随便抓一件衣服就行,灰白的头发乱得跟鸟窝似的,也是随便用手抄一抄;这天早上他穿的是皮衣,头发明显梳洗过。
门被杨成波以及风一起带上,“砰”的一声,宋小梅的心便沉了一沉。
晚上,宋小梅特意做了个杨成波爱吃的鲜菌肉丸小火锅,吃完后准备主动提出陪他去散步,刚洗完碗还没收拾好厨房,杨成波没吭一声,就下楼了。
很明显,是跟宋小梅扛上了。宋小梅也不喊他,以最快的速度拖完地,然后穿上羽绒大衣出门,还顺手拿了顶平时不大戴的毛线帽。
快步走,十几分钟就到了南门广场。可能是天太冷了,南门广场人不多,平时各自霸占着一块区域跳广场舞的小分队没出来活动,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练气功和太极的老人还在寒风中认真比画着,两个遛狗的年轻人,穿着单薄,但活力四射地在跟自己的宠物嬉戏追逐。
不知是因为冷还是什么缘故,广场四周的灯都比夏天时暗一些。宋小梅睁大眼睛四处看,终于在广场另一处入口的音乐池边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他好像在等什么人,一边踱步一边张望。
宋小梅把自己隐藏在暗处,又戴着毛线帽和口罩,不仔细看,就算走近,杨成波也认不出她。等了几分钟,果然有个穿大衣的女人朝杨成波走了过去。两人站着聊了几句,很默契地围着广场散起步来。
宋小梅做贼似的看了一阵,那两人倒没有进一步的举动,比如挽胳膊牵手之类的。没看到预期的结果,宋小梅倒没觉得多开心,她愣愣地待在原地,任凭北风见缝插针地钻进她没系严实的领口里,思维像是被风吹僵了,不知是该迎上去质问他们,还是装成无意中碰到他们,然后一起散个步。做什么都好像不对。结婚三十余年了,许多时候明明是杨成波做得不对,但到最后总是变成她的不对。宋小梅用力吸一口气,冷风顺着鼻腔长驱直入,心就像被风拧了一下似的抖了抖,她只觉得喉头发痒,用力一咳,咳出一口老痰来。举目四望,偌大的广场,竟然看不到一个吐痰的地方,虽有夜色遮掩,宋小梅也不想逆了自己的习惯,只得含着它往回走。小区入口有一个垃圾桶,可以解决她从胃里不断涌上来的恶心。
将近十点,杨成波才回来。宋小梅在自己的房里假寐,听他倒了热水出来泡脚,边泡边刷抖音,半小时后,他回到他们的大卧房,接着是关门声。
大约一年前,宋小梅就和杨成波分房睡了。是宋小梅主动提的,她的理由是,他现在身体有恙,而她睡眠不好,晚上一丁点儿响动就惊醒,翻来翻去睡不着,这样互相影响,对两人的身体都不利。其实,宋小梅是嫌他的呼噜声太响,忍了他许多年了,本来可以继续忍下去的,但杨成波有点儿得寸进尺了,他自退休后,睡得早醒得也早,经常凌晨三四点钟就醒了,醒了就醒了吧,他偏赖在床上不起来,靠在床头刷抖音,也不戴耳机,抖音里各种搞怪的笑声和音乐吵得宋小梅快要疯了,抗议过几回,无效。年龄大了,她不想忍了,也忍不下去了。
杨成波起初不同意,说他现在是个病人,万一哪天夜里发病了,身边没个人及时发现。宋小梅想了想说,就在隔壁,又没有隔山隔海,哪里就那么危险了。“这样吧,我给你手机上设两个快捷键,你如果半夜觉得哪里不舒服了,按‘1’就可以打我电话,我立马跑过来,按‘2’就是打120急救。”
看她态度坚决,杨成波阴着脸说,我知道,你是嫌弃我了。
“老杨,你想多了,我是为了我们两个的身体着想。小芮不在身边,我们现在谁也不能垮,不然就是给她添麻烦。”宋小梅耐心跟他解释,心里头说,是的,就是嫌弃了,嫌弃你数十年如一日的自私。
看宋小梅把远在澳大利亚的小芮都抬出来了,杨成波只好不做声,算是同意了。
杨成波给他们立了个分房规矩,各自睡可以,但大家都不要关房门,哪天谁想上谁的房里去睡,就直接进去,不用敲门那么生分。宋小梅虽然有睡觉一定要关门的习惯,但想着总还是要顾及一下杨成波的感受,也就答应了。
刚开始分房睡那个把月,宋小梅每次起夜,如果没听到杨成波的呼噜声,都要站在他房门处凝神听一会儿,直到他房里有了动静才回房继续睡。有一次,她听了差不多十分钟都没听到任何声音,有点儿慌,又有点儿好奇,她摸黑走进他睡的大卧房,站在他床边,他还是没动静,宋小梅就试探着伸出食指放在他的鼻子下。有均匀的呼吸。她悄悄退了出去。
这件事,她没有跟杨成波说,杨成波也没跟她提起过,她就当他不知道好了。
现在,杨成波居然主动破了他自己立的规矩,关门睡觉了。可以嘛,很好。宋小梅起身下床,也把自己的房门关了。
第二天吃中午饭时,宋小梅才逮到机会跟杨成波说话。“老杨,昨晚在南门广场看到你和哪个女人一起散步来嘛。”宋小梅舀起一碗西红柿蛋花汤,边喝边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问。
杨成波愣了一下,淡定地夹菜,说,是的。
“是谁呀,我不认识吧?”
“我老同学,来过家里打麻将。”
“就散步这么简单?”
“不然你以为呢?一个人散步没滋没味的,你又不陪,我找个有共同爱好的一起散个步,聊聊天,舒缓一下心情,怎么了?”
宋小梅没想到杨成波能这么理直气壮,她被噎了一下,放下碗反问说:“你的意思是,我如果也找一个老头子天天约着散步,你也认为是正常的?”
“你找呗,我又没拦着你。”杨成波没看她,继续埋头夹菜,嘴角还带着一抹笑意。
宋小梅盯着杨成波看了一会儿,对方正专注地嚼一块炒牛肉,两腮因为用力过猛,扯得面部有点儿扭曲。这个年近六十岁的男人这两年老了许多,眼里没有做生意时那种精明的光了,眼白便显得混浊起来,像一对许久没擦的灯泡,原本大大的鱼泡一样的眼袋也下垂得越发厉害,看久了就有动手帮他割掉的冲动。她站起来叹了口气说,今天的蛋花腥味儿太重,有点儿犯恶心,然后扭头离开了餐厅。
三
宋小梅想跟女儿小芮谈谈杨成波的问题,谈谈自己对她父亲以及对这份婚姻的失望。她在微信上组织了几次语言,每次临到要按发送键时,又删除了。
说了又有什么用呢?宋小梅心里明镜似的,她和杨成波之间隔着一条宽广的河,靠女儿这条船来回载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们需要的是一座牢固的桥,心与心搭建的那种。现在,他们都无力于这项艰巨的工程。
小芮在澳大利亚快十年了,回国总共没超过五次。她独立得很,没怎么让她和杨成波操心,当然也没怎么操他们的心,总在学习、打工和做实验中来回转,从大学到研究生再到现在的博士生。每一次宋小梅主动找她聊天,她都是三言两语就打发了她。“妈妈,我太忙啦,导师找我开会了。”或者,“老妈,我在打工,不能多聊哦,等我空了回复你哈。”然后,几个小时才有一条微信过来:“我很好,老妈,你和老爸多保重,空了我就回来看你们。”宋小梅只能苦笑,女儿太独立了,都有点儿刀枪不入了,自从读研以后,她既不需要父母提供金钱方面的资助,也不需要他们提供情绪上的安抚。那个喜欢趴在她的背上耍嗲的小女孩,已经成长为一个孤勇坚韧的女战士,在外面冲锋陷阵闯天下,她怎么能随便拿自己的情绪问题去烦扰她呢?
宋小梅有时很羡慕女儿,有朋友来家做客,提起女儿,她总是有些神往地说,作为新时代的独立女性,一门心思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为生活中的俗事烦忧,真好。有一次被杨成波听到了,他接话说,好个屁,真后悔送她去国外留学,一年到头见不到,快三十了也不嫁人生子,学人家国外的人崇尚自由,自由到现在,除了一个澳大利亚的绿卡,啥也没有。
“女人不一定非得属于家庭和厨房,现在的时代,不像我们那个时代了,除了老公和孩子,女人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宋小梅反驳他。
“哟,看不出来,你这个围着家庭转了一辈子的女人,思想还蛮新潮蛮激进的嘛。遗憾的是,你这辈子怎么没弄出更多的可能性呢?”杨成波笑着挖苦她。
女儿是女儿,我是我。我不想让她跟我一样。宋小梅在心里说。她不能跟他继续理论,她知道杨成波的脾性,你要当着外人的面跟他争,他能让你下不来台。
宋小梅原指望她挑明了杨成波与女同学散步这件事后,他会有所顾忌,知道收敛,但他没有,他还是吃了晚饭后一个人下去散步,散两三个小时才回来。
宋小梅知道杨成波在赌气,他是想让她妥协,主动陪他去散步,主动减少陪护父亲的时间,多留在家里。其实宋小梅如果跟大哥开口,大哥是会多承担一天的值班责任的,但宋小梅开不了这个口。大哥六十六岁了,心脏也不好,家里还有孙子孙女要管,而她是四兄妹当中最年轻的,又没有小辈在身边,理应承担最多。
最主要的是,她也不想妥协了,妥协了大半辈子,累了。以前,杨成波说要为了家庭努力挣钱,家务百事不问,她念他在外打拼辛苦,所有的事都自己扛,惯得他以为她所有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现在他闲在家里,依然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从不为她考虑,稍没让他称心如意便要肆意妄为,像个任性的孩子,这太没道理。
这之前,她人在父亲家,心里还是挂着杨成波的,每天总要打一两个电话给他,嘱咐这交代那,发生“散步”事件后,她再也没主动打过电话给他。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吧,看谁坚持到最后。有时,手机没电了,她也不急着充电,就让它死寂着。没有手机打扰的世界真清静,她偶尔需要这样的清静。
日子就在这样的僵持中走过,转眼过完春节,G城最冷的倒春寒来临。G城的冷,是那种深入骨髓的冷,寒风见着毛孔和缝隙就钻,钻进去就扎根了。为了不冻着父亲,当然也为了自己,宋小梅给父亲的卧房装了个大号暖气片,二十四小时开着,周末两天,把父亲伺候好了后,宋小梅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窝在这间暖气开得很足的房里打瞌睡。这是真正属于她的时间,尽管很有限。
又是一个周一,快十点了,宋小梅交完班回家。坐上公交车,缩着脖子无聊地看着窗外两旁的商铺,看到移动营业厅的牌子时,她想起前两天收到短信提示,手机话费余额快不足了,掏出手机想把话费交上,但手机黑屏了,不知哪时又没电了。
打开家门,屋里冷飕飕静悄悄的,估计杨成波又出去散步了。她倒了杯热水喝了,找出充电器把手机插上,等充了一阵电后,开了机。有一个十来分钟前杨成波打来的未接来电,那会儿,估计她刚走进小区里准备上楼。她看了一眼大卧室的房门,紧关着。有一丝不祥的预感蚂蚁一样爬上宋小梅的心头。
宋小梅拧开房门。屋内的暖气开得很足,给人一种污浊的憋闷感,昏黄的床头小灯暧昧不明,但看得清楚杨成波穿着睡衣趴在被子上面,一只手压在身下,一只手握着手机。她连忙打开大灯,一边叫着“老杨,老杨”,一边艰难地将他翻过来。杨成波的左手摁在胸口,脸呈紫红色,牙关紧咬,头发和衣服有汗湿味。
该来的到底来了。宋小梅忙去探杨成波的鼻息,还好,还有微弱的呼吸。她抖着手,用力掐他的人中,想把他掐醒,但他只是呻吟了一声,一动不动。还有什么急救方法?宋小梅脑子一片混乱,没招了,只得去抠杨成波右手紧握的手机,准备打120急救。
杨成波的大拇指死死摁在“1”上,仿佛那是个生门。只可惜,关键时刻她偏偏手机没电了。宋小梅有点儿自责,跟他怄什么气呢,跟一个病人怄气做什么呢?她的眼泪涌出来。手机拿下来了,但是因为慌乱,没抓紧,跟着她的眼泪一起滑落在被子上。
捡手机时,宋小梅才发现,刚才杨成波身子下压着一条陌生的色彩鲜艳的布,拿起来一看,是一条崭新的女式围巾。这不是她的。那么是谁的?怎么出现在杨成波的床上?猝不及防,这条外来物件像一条花斑蛇一样,狠狠地咬了一口她的心。
宋小梅脑袋“嗡嗡”的,盯着那条围巾,目光又游移到杨成波的脸上。杨成波的眉头拧紧,闭着的眼睛下那两个大眼袋耷拉着,像两条死去多时的大肉虫。打什么急救电话,让他去死吧!宋小梅咬着牙,过往几十年发生的事像倒带一样,快速闪现在眼前。他的花花草草,他的自私和坏脾气,还有他每次看完父亲后的那句感叹,“我将来要活成这样,我自己吃安眠药死了算了”……既然如此,那么就让所有的一切,随着他一起结束吧!
脑中正激战,外面传来刺耳的铃声。宋小梅吓了一跳,茫然四顾,想了一下,是自己放在客厅充电的手机铃声。她冲出去,接通电话。
“您好,我是XX商城的,我们商城正在搞特价促销……”电话那边传来甜美的女声。推销,又是推销!也不知这帮人是怎么拿到她的电话号码的,有时一天接两三个推销电话,理财的,装修的,干啥的都有。宋小梅心头的怒气海啸般直冲天灵盖,她对着电话歇斯底里地哭骂:“王八蛋,以后不要再给我打这类电话,你们凭什么这样骚扰别人,谁给你们的权力?”
电话那头的人估计是个新手,被骂蒙了,不知道怎么回话,愣了愣,挂了电话。
宋小梅捏着手机,无力地瘫坐在沙发上。
到底要不要报急救呢?救回来后,无外乎床上又多一个瘫痪者,自己未来的人生大概率就是奔波在老父亲与杨成波这两张病床之间,真正是疲于奔命了;不救,自己与杨成波这一世的情分就完全断了,难保她以后不后悔,最重要的是,她怎么向女儿交代?宋小梅闭上眼睛,想着隔壁房里的杨成波那似有若无的呼吸,心如死灰。为什么呢,人生为什么总像在考试啊,每个时段都要被迫做一些选择题!做了一辈子,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已经累坏了。
眼泪像暴涨的河流。宋小梅抬起握着手机的手,怔怔地看着。她想起杨成波那死死摁住“1”的大拇指。那个大拇指此刻像是一根杵,一下一下地戳她的心,戳得她胸口胀胀地疼。她咬了咬牙,像要把后半生可以想见的辛苦都咬碎了咽下,然后抹干眼泪,狠狠地按下那三个数字。
挂完电话,宋小梅晃悠悠地站起来,挪到杨成波的房间。这个与她生活了三十余年的男人依然悄无声息地躺在床上,在灯光的照射下,像一具上了色釉的蜡像。她游魂似的走到他面前,又一次颤抖地伸出右手食指探他的鼻息,停留良久,她确信,她没感觉到手指有被暖风吹过的温度。
宋小梅的心一紧,片刻过后,又松弛地落下来,像被剪断线的风筝从空中坠下,飘飘荡荡地落在柔软的草地上。
责任编辑 刘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