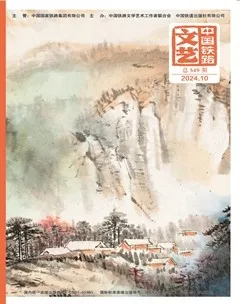父亲的药箱
作者简介:陈国庆,供职于广州局集团公司株洲机务段。作品散见于《工人日报》《人民铁道》《广州铁道》等报刊。
父亲有一个药箱,那是他巡回出诊时随身携带的诊疗箱。
父亲曾经是湘桂铁路线上的一名巡回医生。他不在医院坐诊,而是常年背着药箱,去铁路沿线小站巡回出诊。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小城镇医疗水平不完善,加上交通不便利,地处小城镇的铁路沿线小站的职工家属就医很不方便,所以铁路医院就抽调医生组成巡回医疗队,分区段在铁路沿线小站巡回出诊,解决沿线小站铁路职工家属看病难的问题。我的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在距离居住地约60公里范围内的沿线小站之间巡回出诊。
记忆中,天还没亮,父亲就起床,用开水泡一碗隔夜冷饭,就着剩菜或是咸菜,匆匆吃完早饭,就去赶早班火车。那时候,火车开行不多,每天只有几趟客车,而且很多小站每天只有一对慢车经过,这对慢车站站停靠。早班慢车的开点是六点多钟,父亲必须赶上这趟慢车去往沿线第一个小站出诊。如果这个小站当天看病的人少,他还得走到另一个小站出诊,直到下午赶上返程的慢车回家。如果赶不上返程慢车,就得在小站过夜。
从记事开始,我就知道药箱是父亲的宝贝。出门,便斜挎在身上,随时问诊;下班,就放在床头的立柜上。那个放在卧室床头旁的立柜,大概有一米高、一尺来宽,是药品的储藏室。每天下班回到家,父亲顾不上休息,第一件事情就是擦拭药箱、盘点药品、整理用药记录,然后从立柜里拿出药品补充到药箱里,以便第二天一早出诊。每隔10天左右的时间,下班回家的父亲,就会去一趟铁路卫生所,领取一些药品回来存放到立柜里备用。我的爷爷是一名老中医,父亲从小耳濡目染,学得一些中医,后来当兵时在部队又学了西医,退伍后到铁路做了一名医生。
有时候做完功课,我会待在父亲身边,看他整理药箱药柜。父亲的记性很好,哪些药品是常用药需要多带一些,哪个职工预约了什么药,哪个家属治病的药品快用完了,都在他的脑子里记着。父亲做事很细致,他从药柜里依次取出需要补充的药品,在笔记本上认真记录好,然后放入药箱整齐码好。在父亲的手里,药品医械像是一群听话的孩子,被排列得整整齐齐。这个药箱看似不大,却是一个百宝箱,常用、急用的药品和医械基本齐全。药箱里面有上下两层,每层又有大小不等的小格子,每个小格子里都挤满了药品。父亲告诉我,每天最多也只能去一至两个小站,一个小站一周也就去一至两次,去一次就要尽力满足职工家属的就医需要。如果缺药,就要等到下一周,有些人的病情虽然不是危重,但也是耽搁不得的,必须及时得到药物治疗。所以每天出诊,他都要把药箱塞得满满当当。我尝试背过一次,很沉,背一会儿都勒得肩膀和胯骨痛。
有时候因为某个小站的职工家属急病或者急需用药,父亲就得从一个小站步行赶到另一个小站出诊送药。要知道,两个小站之间一般都有5公里以上的距离,没有现成的大路可走,要沿着路基旁的便道步行,路基周围就是杂草丛生的荒郊野岭,很多路段就连通行的便道都没有,只能绕道走附近的田埂路。夏日炎炎,父亲头戴草帽仍然大汗淋漓;寒风凛冽,父亲顶风冒雪艰难前行;春秋两个季节,经常都是那个药箱和一把雨伞伴随父亲踽踽独行。工作虽然艰苦,父亲总还是乐观的。有一年夏日的一个傍晚,父亲又是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手上居然还提了一个大西瓜,他说在一个小站出诊时,见到车站旁售卖的西瓜又大又圆,想着我们的一脸馋劲,他硬是从10公里外的小站背回来了。可惜我们那时候年纪小,只顾着吃西瓜,没有理会父亲连晚饭都没吃就呼呼大睡了。很多次晚饭后,父亲也会给我们说些外面的事情,分享他在工作中的趣事。比如,那个小站的周伯伯家娶儿媳妇了,儿媳妇的娘家就是周伯伯家的邻居;这个小站的吴叔叔家孩子考上重点学校了,孩子舍不得铁路家属院的小伙伴们,死活不肯去大城市里上学。当然,还有父亲在铁路边上遇到的各种趣事,让我们很向往那种新奇的境遇。比如,那个炎夏酷暑的傍晚,铁路边的便道上趴了两条乘凉的蛇,好在他反应快,一大步跨过去避开了;那个草长莺飞的午后,田埂上惊飞了一只斑鸠,他一不小心摔下了田埂。这些事情,父亲娓娓道来,那么生动有趣,丝毫感受不到父亲的艰辛。直到后来一次亲身经历,让我对父亲的那些经历有了全新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末,我入路工作成了一名蒸汽机车司炉。有一段时间我执乘的线路,就是父亲巡回出诊的区段。我清楚地记得那个烈日炎炎的下午,我们回乘途中,室外接近40摄氏度的气温,蒸汽机车驾驶室内至少有六七十摄氏度。我往火红的炉膛里投放了十几锹黑煤,赶紧站到机车驾驶室右侧门口透风。我的视线投向铁路旁边的原野,阳光普照,很多植物都被晒得无精打采。火车经过一处弯道时减速运行,大概也就是20公里的时速,我收回视线,不经意间瞄了一下近处,突然有个熟悉的背影映入了我的眼帘。前面不远处的路基便道上,一个头戴草帽、身挎药箱的身影正在疾步前行,我一眼就认出来那是我的父亲。火车经过他身边的一瞬间,我脱口大喊了一声:“爸——”眼泪随即夺眶而出。那一刻,我真想叫司机停车捎上父亲,让他少走几公里路,但我明白不可能那样做也不会去做。烈日当空的午后,我的父亲一个人独自走在出诊的路上,虽然我不知道他在烈日下走了多长时间,但他的脚步却坚定有力。我在那一刻,真真切切体会到了父亲坚韧乐观背后的艰辛!
那天父亲下班回到家已是晚上七点多钟,吃完饭他照例整理第二天出诊的药箱,我知道他很疲惫,但他为我们呈现出来的依然是平静而乐观的状态。我告诉父亲,我看见他在烈日下独行,父亲淡淡地说:“又不是第一次走,早就习惯了。”此后,我在执乘途中又遇到过父亲几次,每次经过父亲身旁的时候,我都会大喊一声:“爸——”因为车轮轰鸣的声音,他听不到我的呼唤,也从来没有抬起头来看过我,但我知道,他对工作和家庭的热爱一直都寄托在那个药箱里。只要那个沉甸甸的药箱还在紧紧贴着他,他就要心无旁骛,执着前行!
多年过去,干了一辈子铁路巡回医生的父亲早已作古,而那条铁路线依然存在,只不过已改为货物列车专用线路。很多铁路小站也完成了历史使命,已经关闭。随着铁路的改革发展和医疗条件的极大改善,小站巡回医生也完成了使命。如今,在这条铁路线旁边的高铁线上,一列列高铁列车飞驰而过。在那些见证了铁路发展历史变迁的旅客当中,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几个旅客,还能够想起这条铁路线。会不会有人还记得多年前,在列车上看到过铁路旁一个头戴草帽、身背药箱的行人。如果有人还记得或者问我,我会自豪地告诉他,那个人就是我的父亲,他肩膀上的药箱就是他一生的使命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