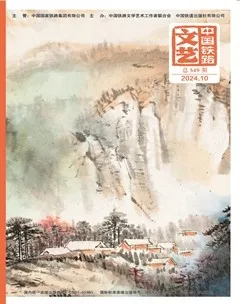大庆路今昔
作者简介:王锡美,中国铁路文联作家分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供职于西安局集团公司宝鸡机车检修厂。作品散见于《中国铁路文艺》《人民铁道》《陕西日报》《西安新闻》等报刊。
1988年,我从郑州铁路机械学校(现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被分到西安铁路分局宝鸡东机务段,也就是现在的宝鸡机车检修厂。
22岁的我,揣着青春梦想,背上简单的行囊,踏上西行的列车。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宝鸡。
绿皮车不紧不慢地在关中平原奔跑着,有节奏地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坐在车厢一隅的我望着窗外掠过的田园风景,独自想着临行前曾在宝鸡工作过的陈老师告诉我的话:“如同电气化是中国铁路新的发展,宝鸡是因铁路新兴起的、陕西省第二大城市,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个城市有三条公交线路,你要乘的是从西关至油毡厂的1路公交车,但只能坐到半路下车,剩下的路就没有公交车,要自己步行了。”
那时候,电气化铁路刚刚在全国普及,各铁路局大量需要电气化人员,作为距离火车站十多里地、位于大庆路上的东机务段,是当时西安铁路局唯一专业检修电力机车的单位。在这蓬勃兴起发展腾飞的行业,适逢国家改革开放伊始,正遇青春的自己,我充满激情与渴望。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到了宝鸡站。下了车,向北,穿过外表似山形的候车室东边的过道,上一小段坡,就出了宝鸡站。站口摆着烩面片、擀面皮等各种小吃摊,叫卖声尖而悠长,热气腾腾,人声嘈杂,非常热闹。在车站口的解放路(现在叫中山路)乘上了1路公交车,售票员面对我的询问,热情简洁地回答道:“车票一毛,到三医院站下车,向前就是。”
公交车顺着解放路、东风路一路向东,很快就到了三医院站(即现在的987医院),1路车拐向北,朝宏文路继续行驶。下了车的我,站稳身子,整了整理衣服,便向前望去。街道变成两车道的公路,是用沥青简单铺就的路面,和现在的乡村公路差不多宽,笔直得一眼望不到头。车道和人行道不分,界线是沥青路与沙土路的接壤,公路上行驶的多是解放牌的卡车和农用拖拉机,偶尔有两轮拉着蔬菜瓜果的人驾马车慢悠悠走来,马蹄声清脆利索。路沿是一尺多宽的沙土,坑坑洼洼,是雨水冲刷公路的结果。路下则是堆了杂物的沟渠,有树枝落叶、破瓦烂砖,还有泛着阳光的水洼。路两边是种着各种蔬菜的成片田地。
我的心一下子有点凉。我渴望城市生活,努力学习是想改变面朝黄土的命运:这不是又回到了农村吗?
路南是一条通往河滩的土路,我向一个自行车修理摊的师傅打听,老师傅抬起油污的手,头都未扬,向前一指:“那就是大庆路。”
阳光灿烂,洒满大地,而脚下的道路却像一条无尽的长河,蜿蜒曲折,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尽头。我在路边停下了疲惫的步伐,静静地驻足。路南还是菜地,一望无际,搭架的西红柿结果丰硕,红彤彤的很是诱人;绿油油的黄瓜鲜嫩垂落,掩映在藤叶之间。北边,路旁伫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金台区体育场”。顺着菜地中一条砂石路看去,一溜红砖围墙,那儿就是金台区体育场,后来我还到里面的水池游过泳,清凌凌的水一眼见底。毗邻的好像是一家工厂,砖墙内矗立着一座20多米高的烟囱,过了一段时间后,我知道它是曾红火一时的宝鸡叉车三厂。当时,烈日如火,炙烤着苍茫大地,路上行人稀少,仿佛都躲避着这炽热的阳光。而我,孤独地行走在这无尽的旅途中,内心却没有丝毫动摇,只有那坚定向前的信念,如同不灭的明灯,照亮着我前行的道路。
我不再歇息,加快步伐,拖着行李向前疾走。
大概20分钟后,看到路北边有几棵腰粗的河柳和榆钱树,树后面是一排红砖垒的院墙,里面有几幢厂房,两行高大的梧桐树插进厂区。路南边则有一处简易棚搭就的菜市场,有零散的几个人在卖菜。旁边不远处是两排三层的楼房,能看到木制窗户里绰动的人影。再向东望去,已看不到什么工厂模样的房屋,满目都是农田菜地的景象。我转身走到一个卖肉夹馍的摊前,问道:“乡党,这儿是不是东机务段?”摊主扬起西北人特有的黝黑的脸庞,疑惑地看着我说:“是啊!”
…………
30多年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沧桑沙哑的声音:“是锡美吗?”
这声音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那么亲切,好像从心底唤起的回音;陌生的是好久好久未曾听到,犹如隔着一层薄薄的丝纱。
我试探着回答道:“我是,您是?”
“我是陈老师。”
电话里的声音明显变得轻松欢快。
我一下子想起了当年离开学校时特意叮嘱我的陈老师,心情竟有些潮涌。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记得宝鸡有个他的学生。
从他的叙说中,得知已经近八旬的陈老师是在家人的陪同下,乘坐火车到宝鸡看看他工作过的地方,马上就要到宝鸡南站了。
我立马停下手头工作,驱车去接他。
拄着拐杖的陈老师在家人的搀扶下,缓缓走出了宝鸡南站的出站口。
岁月无情,已经染白了陈老师的头发。世事沧桑,也催弯了他曾笔直的身腰,但我仍在如织的人流中一眼就认出了他。
来不及寻住宿,也拒绝找地方先吃饭,陈老师让我载他们先到宝鸡火车站看看,再到大庆路上看看,再到原先的单位看看……他要看的地方太多太多了。
“自离开宝鸡,四十年没来过!”
陈老师脸上泛起晕红,眼里泛着泪光,激动又感慨地说。
于是,我们一行人沿着高新大道,过胜利桥,走经二路,到了宝鸡火车站。我刻意开车很慢,边开车边向陈老师介绍沿途的变化。
当我们驶过周围都是云楼高耸的987医院时,我说:“老师,这就到了大庆路。”
陈老师执意要下车走走,只好寻一处停车,陪他步行。
向东望去,八车道的大庆路,中间还有一条宽5米的绿化带,路肩则是十米、二十米不等的人行道和数不清的商贾,高耸的云楼如森林里的树木一样繁多。老师睁大眼睛,嘴巴半张,惊愕得竟不知身在何处。
陈老师的家人不无感慨地说:“和郑州一样,都是火车拉来的城市,宝鸡发展真的快!”
我搀扶着老师的臂弯,一边慢慢走,一边向他介绍:“原先那几个厂已搬到宝鸡高新区去了,只剩下一家您之前工作过,前几年扩能改造焕然一新的宝鸡机车检修厂,路两边广阔的田地已不见稼穑蔬菜的踪迹,都盖成商楼和居民的楼房了。大庆路如今已是宝鸡市最繁华地段之一,也是宝鸡市区东出的主干道。”
对多年生活在宝鸡的我来说,对大庆路的变化,当时没多少感觉,就像自己工作三十多年的宝鸡机车检修厂,回头看时,想起刚来厂时的情景,才觉得宝鸡机车检修厂内外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陪着陈老师一行人漫步大庆路,回想着三十多年前它的旧貌,再看它现在的模样,相继建起的“泰森生活广场”“恒源酒店”“西建康城”等一大批高楼云集的现代建筑,我也震惊和激动。
原来,我们身边许多事在不经意间发生着一点一滴的变化,多年后,蓦然回首,却发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和陈老师缓缓走着,相互回忆着曾经的风霜岁月,诉说着离别的伤感,也感叹着如今沧海桑田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