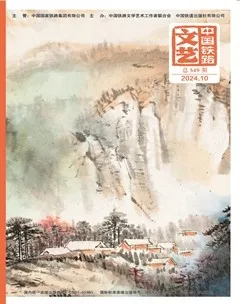阳南溪畔听风响
作者简介:北雁,本名王灿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中国铁路文艺》《延河》《滇池》《海燕》《阳光》《鹿鸣》《边疆文学》《黄河文学》《大地文学》《短篇小说》《散文选刊》《作品与争鸣》等报刊。曾获第九届云南文学奖小说奖、云南好书佳作奖等。出版《洱海笔记》等长篇作品4部。
一
阳南溪,这真是一个极好的名字。当然,这名字的来历,或许是因为它发源于苍山第十九峰斜阳峰和马耳峰之间。斜阳峰是苍山自南向北的第一峰,山前是开阔的平地,四周没有更高的山峰遮挡,于是我想这条溪,包括这座宏伟的山峰,有可能是绵延百里苍山,每天最早被太阳照到的地方。生活在山脚下的这个城市,特别是到了寒冷的冬日早晨,在密集的高楼下来回劳碌,感觉天色还是一片黯淡,蓦地抬头一看,斜阳峰上早已经落满了一丛暖暖的阳光,一颗心也会突然变得温暖透亮起来。
这就是我生活的城市下关,一个因为山和水而著名的地方。从苍山发源的十八条溪流沿岸,村镇密布,大理、喜洲、湾桥、周城、古生、龙龛、太和、凤阳邑……有的古朴如旧,有的历久弥新,有的闻名遐迩,让这溪水如同一根根金线,串联起了一排排闪亮的珍珠,无不与世界文明发展规律相契。而我今天要说的这条溪,它最终的流向却是高原明珠洱海,洱海的流向却是澜沧江,蜿蜒多国后最终汇入太平洋。我生活的这个城市不仅有雄伟的苍山,还有碧波荡漾的洱海以及源远流长的澜沧江。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自豪地说,得天独厚的大理风光和四千年文明,就是这一山一湖一江共同孕育和缔造的。
二
我生活在这个城市,感激洱海的博大历练了我开阔的胸襟。我同时迷醉于苍山的壮美,让我无时无刻不充满向往。于是,在2023年的冬季来临之前,我决定走出陋室去走访苍山。当然我也知道苍山海拔奇高,攀越苍山是件艰难的事情,神秘莫测的苍山气候更是让我一直望而却步。但我却可以用脚步去陪伴从苍山发源的每一条溪流,因为溪流同样是苍山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溪流哺育的城市、乡镇和村落,说到底就是苍山带来的文明,我可以在水的流淌中体察这座雄伟的大山。
阳南溪其实是从城市边缘流过。环城路边的阳南溪大桥一过,就出了城。而这条以太阳命名的溪流,让它沿岸的村落,也都带上了暖暖的太阳色。一桥之隔,河北的村落称之为阳南,河南的村落被唤作阳平村。
来到桥上,看到哗哗流动的溪水,我更愿相信那是一位智者的低语。十八溪发源于苍山之巅,从诞生之日起,这微小的水滴就尽揽日月精华,尽情地呼吸着海拔3500米以上最纯洁的空气,从半空之中欢流而下,沿途流经的山脉、沟渠、深涧、高崖、箐谷、岩石、土壤、泥沙、落叶、林木、花草,给它带来了丰富多元的内涵。沿途之中,它经风历雨,在酷暑中蒸发,在严寒中冻结,有时还得随着河道的变化挤压收放,甚至改变流向。溪流沿岸,无法计数的庞杂根系的吸附、飞禽走兽的畅饮,还有沿岸居民的饮用、灌溉和其他用途的损耗,使之随时都有断流的风险。然而让人钦佩的正是它的包容与接纳,匆匆一场雨雪,又使之汪然充沛,在山头岭脚和沟壑渠潭间欣然畅流,并随着地理状况的变化改变形态,流泉飞瀑、散花泻玉、静水深流、细流涓涓、奔流不止……我一时还找不出那么多可以修饰它的词语,但我却感叹它走山过道,一路欢歌,到了此地,却突然放慢了脚步,俨然一个见识广博的长者。我情愿陪伴它一路行走,细细聆听它源自苍山内腹的心语。
三
位于立交桥头的阳平村,掩映在绿荫深处。一块高大的村碑上大书“阳平村”三个大字,我记得有些文献也将之称为“羊坪村”,也有的称为“羊皮村”,从字面上可以隐见昔日的边贫与寡苦。如今一个名字的演变,像是有一只大手,把一个遥远的乡野村落,瞬间拉到了城市边缘,并且更频增了几分诗性想象。地名和地名学,就是这样一种有意思的学问。
当然这个村落的闻名,乃是村子边缘一个著名的古建筑——建于唐朝南诏劝丰祐年间的佛图寺塔。但在大理人民的口中,佛图寺塔更多地被称作是“蛇骨塔”,并且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英雄斩蟒的传说:古时苍山有巨蟒作乱,害得当地民不聊生。顽童段赤城长大后练就一身本艺,便勇敢地站出来与蟒作斗,不想却被巨蟒一口吞下,段赤城就在蟒腹中一阵砍杀,最终蟒蛇被杀,自己亦窒息而死。后人感念之,乃剖开蛇腹,取出段赤城尸骨葬之,同时焚蟒之皮骨血肉为灰,和土煅烧为砖,在赤城塚上建塔以标之,名曰“灵塔”,俗称“蛇骨塔”。
类似这种道德与正义相辅的传说,在苍山洱海之间比比皆是,从而可见这块土地的价值。而段赤城身上,还更多了一种凛然慷慨、向死而生的正气。
但我却从中知道,当时的阳平村一带必定有大量的砖瓦窑。考古资料显示,当年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南诏国初立,为满足都城宫殿与各种佛寺的建设之需,苍山脚下,曾有大量的村落承担了煅砖烧瓦之责。而有的村落就以其当日职责命名,譬如“五里桥”“七里桥”“南五里桥”,在当时是专门负责架桥造路的村落;而“塔村”则就承担了造塔之责。转眼千年时光逝如流水,许多古旧村落传承至今,好似一颗颗耀眼的珍珠散布于苍山脚下,让人时时刻刻充满向往。
我从阳平村密集的出租房群落走过,村中心的一棵大青树高大挺拔、遮天蔽日,苍劲的枝叶似在无声地诉说着一段久远的历史。树下一个简易的小集市,让各种腔调的语言在这里交汇,热气腾腾的熟食带来了浓浓的烟火气息,各种滋味的混合让人馋涎不已。
集市背后的小广场畔种有三株老槐树,在大理地方习俗中,槐树就是王姓人家的象征。果然晚上回到家中翻开《大理市白族村名考》,阳平村居民多为王姓。在姓氏文化故事中说:北宋名臣王祜,气节奇高,并以文章、清廉、忠厚著称,在家门前种三棵槐树教习子弟,果然多年后子孙兴旺、后世昌达,三个儿子都是北宋名臣,其中次子王旦官至当朝丞相。
在时光流转之中,照壁姓氏文化在大理地区一直盛行,许多知书达理的人家遵循古训,秉承家风家道,形成了一种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让苍山洱海之间的大理充满了浓浓的书香气息和道德内核。槐树下面有一方照壁,同时还有许多老旧的古房,沧桑毕显,斑驳的诗书文墨,透示着村落的古老与渊深。细细读罢其中一些诗文,我顿时不敢骄傲了。
穿越一条狭窄的村道来到佛图寺塔前,挺拔的塔身在明朗的苍穹之下傲然屹立。正是午时,天朗气清,阳光明媚,只觉古塔更有一分历史的厚度。轻风袭来,时不时会有清脆的铃声响起,便让这气氛变得更加悠远庄重。据塔下的碑文介绍,塔通高30.07米,为13级方形密檐式空心砖塔。塔因寺而名,塔基对面,就是佛图寺,两者相依为伴,同样跨越千年历史。
我用虔诚的目光久久仰视,似乎还觉察到塔身向东北方向微微倾斜。果然在手机百度里找到了确切的答案。一下子让我更加肃然起敬,因为这样一种倾斜,似乎更加验证了那一段久远的千年时光。大理历史上也发生过几次较强的地震,但许多跨越千年的伟大的建筑,至今依旧在苍洱之间巍然耸立。包括我眼前所见的佛图寺塔,让你景仰的不仅仅是建造者精湛的技艺,还有在缺乏大型机械和运输工具的艰苦条件下,他们始终有种做千年工程的信仰。2006年,佛图寺塔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渊远的历史和唯美的建造工艺,使之与苍山洱海一样,成为这块土地上著名的建筑地标。与阳平村近邻的寺脚村,就以其命名。
四
佛图寺北面是一块菜地。其间树木成荫,多为核桃,当然也有梨、桃等一些果树。因这树木的遮挡,我无法看到远处山谷,但我相信阳南溪就在菜园的边缘。沿着一条田埂继续向北,林木深处,那是荒草与攀缘类植物的世界,而大大小小的菜地却在这起伏的谷地上错落散布,恍若碎屑,新嫩可人的菜苗在阳光下尽情生长。“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想象那些忘情耕耘种地者,竟然在这巴掌般大小的土地上找到了心灵的慰藉,每天晨兴而起,日暮而归,如若当年结庐而居的陶彭泽,远离尘世喧嚣,却在这耕种之间品悟田园之乐,独享山水怡趣。
弯曲的小道还在脚下伸延,溪流依旧不见踪影,道路两侧的田块还在延续,有些精细的种地者在田边设置了栅栏,将田与道路分开。有的做了木栅,有的种了荆条,有的就地取材,选用田头地脚的大小石块,垒得像是墙体一般厚实。终于来到溪流边上,再跨过一座木桥,来到河的对岸。一条开阔的水泥路位于阳南溪北,我想这应该是我在阳南溪大桥上看到的道路,显然这还是苍山的防火通道。两岸的河堤被修成了石堤,包括河床也被铺上了较为匀净的石头,并用铁网固定了下来。水流不算多,却足够覆盖平缓的河床,随着溪流的落差,可以清楚地听到哗哗的水响,也可以看到太阳底下略带浑浊的溪水,反射出耀眼的亮光。
其实不然,因为我们对自然的各种开发、攫取、利用,包括各种或大或小的滋扰、改变、掠夺、侵害和破坏,同样会清楚地刻印在大自然的山川河流上。
记得多年前,我曾前往一个水源缺乏的山村,村民将唯一的一口井焊上铁门、锁上铁锁,每天早晨村主任按人头分水,旱时每家两瓢,雨时每人半桶。联想到眼前所见的阳南溪,我就觉得先前看到的那把大锁着实要紧得很。否则以现在的交通,特别是人们对野境世界的向往,一条孱弱的溪流旁边,必定会有趋之若鹜的人流,随之而来的污染和破坏,对苍山洱海的生态何不是一种空前的劫难?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如今这洁净的水源和那空气一样,我们实在是没有太多可以挥霍的资本了。
五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对于十八溪的寻访,这将是一种多么富有情趣的旅行。雨季刚过,路的一侧还留有丰茂的野草,时下已经入冬,各种花草都着上了成熟的颜色。而有许多我还是叫得出名字的:芦苇、白茅、黄茅、水蔗草、细柄草、狗尾草、马鞭草、仙鹤草、蒲公英、穿前草、野蕨、母草、白蒿、黑蒿、藜蒿……在离得不远的洱源老家,山体植被与苍山颇为相近。当然这些野草还是小时候离之不得的玩物,有的甚至还可以入药,或是充入我们的食谱。来自苍山西坡的好友阿畅,有一天把我约到他的陋室,女主人在厨房里忙碌半天后摆出一桌子好菜,其中一盘野菜,竟是我沿途看到最多的鬼针草,伴着腊肉丝烩炒的滋味,微涩伴苦,细细咀嚼,又有几分淡淡的回甜,让我一直难忘。
在草木之间行走,不知不觉,路就到了尽头。我知道水源还在不知尽头的苍山深腹,但这已经是我所能到达的终点。这样最好,对于源头深处的念想,可以让苍山在我心中持有更多的神秘。
返回的路上,我还不时地回望苍山。夕阳西下,我能清楚地看到一道道有形的光在山顶上折射和倾斜,让一座雄伟的高峰如同笼罩在庄严的佛光之下。起伏的苍山是有轮廓的,光的折射让那一道道轮廓像是打上了金色的光边,在这时候就更是清晰惹眼,包括隐在光亮后面的褶皱,同样变得清晰无比。让我迷醉的是近处的一排白杨,时令的变换使之灿若金黄,此时一阵风响,万千片落叶一时腾空而起,宛如漫天飞蝗,光彩夺目。我突然又想到,阳南溪以南就是著名的风城下关。每天风起云落,不正是我每天重复的生活节奏?但这座城市,至今早已历过上千年历史,西洱河畔的金戈铁马和佛图寺塔的风雨沧桑,就是这段历史的最佳明证。这每一天的风吹云涌,都隐藏着无尽的历史盛衰和人情冷暖,又何不像我们每日面对的苍山起伏?
寻访苍山十八溪,途中的所见和精妙,恰似苍山的起伏绵延,足够我用一生阅读和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