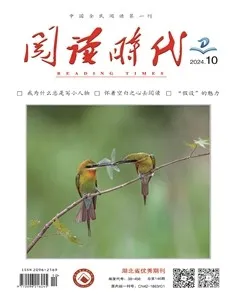一只鸵鸟在想什么
这个暑假回国待在家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状态很像一只鸵鸟。外界纷纷扰扰,我只顾把头扎进名为家的草堆,只要五官被幸福团团包围,我就能说我脱离了生活虎口的危险。
但当我坐上飞往纽约的航班,拿着两个行李箱来到空空的屋子里时,我又不得不把我的头拔出来,面对屁股后头的洪水猛兽。
我很焦虑,也不止一次听到有朋友说自己很焦虑,打开微博发现所有人都在和你一起焦虑,甚至开始发疯。在这样的环境里很难有人还是铁板一块,大家尝试着重建自我,一个一个迷失在“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里面。
我也是其中之一。进入大学的最后一年了,我发现自己的大学生活和我高中时设想的天差地别。那时候,我想要去户外攀岩,野外徒步,一个人坐火车环游美洲大陆。我要在纽约这个文化熔炉里把自己炼成一颗仙丹,在美术馆与电影展的熏陶下变成一位谈吐不凡的人物,大家看见我的名字就像看见了我的风骨。最后要与各行各业的人们觥筹交错,争取在毕业一年后实现财富自由,毕业七十年后实现风光下葬。
我没有成为我愿望清单里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些愿望在我眼里变得与我毫无瓜葛,只是成了一种中产趣味和精英主义,让狭隘的我本人感到十分不适。想到那些生活安逸的人,如何在冲浪板上寻求刺激以拓宽自己人生的边界我就愤慨,因为我觉得我一整个人生都在这个浪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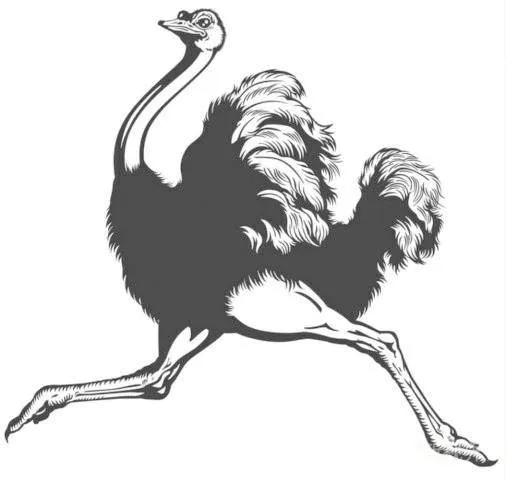
我只是成为了一个很宅的人,成绩没人高,实习背景没人硬,每天就窝在床上看电视。爱好是煮东西写东西织东西,特长也是煮东西写东西织东西。大多数时候我都不干实事,只是在自吹自擂和自轻自贱两个状态里摇摆。一些时候我只想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日出东方唯我不败,另一些时候我觉得自己不用爱一个人都可以低进尘埃里。我对自己没什么要求,更不要说什么人生目标。我就是能从很简单的事里得到满足,可以一直一直退出去。你从我的舒适圈里逼我一步,我就能划拉一个新的舒适圈。
我从小都在和一群优秀的同学竞争,在大学之前我能确保自己永远在第一梯队里,而大学之后大家超过我的速度已经相当的迅速。我发现很多人都是搞清楚了在这个阶段自己想要什么,于是一下子就能跑在前面。
而我不知道我的跑道在哪里。我有时候也很好奇,我的落后到底是因为我没有执行力,还是因为我没有办法为一个不知道的东西而奋斗。上大学之前,我的人生目标都非常明晰,上好的大学,出国留学看看世界,学一开始就喜欢的传媒。但当我真的上大学了,我只觉得自己一年比一年迷糊。我的人生选择题再也不是一目了然的了,没有哪个答案有扑面而来的正确气息,只能用排除法来做。
我最后只能跟随灵感蒙一个答案,拿自己的人生碰运气,并祈祷这最好不是以卵击石。万一行差踏错就一步错步步错,最后我大概可以成功做到在毕业四十年后饿死街头。有的人会说你这么想太极端了,选错了也不至于有多大问题。我说你这么讲就是幸存者偏差,因为大多数选错的人都没有机会张嘴跟我讲话了。
可对我而言,就连“躺平”也是一个艰难选择。家人在我的教育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而我一直也被身边的人期望着能做出点什么成绩。我也没有办法从这种期待里脱离出来,一想到在哪位同学家里的饭桌上提起我当年成绩挺好怎么毕业之后回家啃老,我就打怵。我也不能保证自己能有杨紫琼在《瞬息全宇宙》里的心态,回顾人生所有失之交臂的可能之后,还有本事告诉自己当初的决定没有错。
前两天做家务的时候,我听了《问题青年》的第58期节目。袁长庚老师认为,很多上一辈的人根本没有认真思考过在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下的这一辈的处境,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多和足够实际的资源帮助他们渡过这个建立自我的难关,所以他们寻找自我的过程才会如此艰难。我拄着拖把使劲点头。
点完头之后我又反思:为什么要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呢?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还是有人比你做得好呢?为什么你就不能自己帮助自己呢?这就是我,一个吾日三省吾身的人。
这几天里我反复琢磨自己的焦虑,愤懑地发现从小到大没有人告诉我好好做个普通人也很了不起。
在这个激烈且压抑的环境里,很多时候你要做一个不普通的人才能过上所谓的普通的生活,拥有基本的保障。
如果你想保持一个健康的向上心态,你就得有个能在你掉下来的时候接住你的东西。但事实是人生就像是《男生女生向前冲》这个节目,你停下来就会被一锤子抡进水里,无路可退。
没有人为普通平凡之辈撑腰,他们只是说你不努力以后就在路边卖凉粉吧。为什么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和努力不努力挂钩?最后只有我自己为自己兜底,苦中作乐,给我铺上一块儿满当当的草堆。进去一瞅,里头有《我爱我家》,还有达美乐的美式风情培根土豆披萨。
“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自我的价值”,这套说辞有着虚伪的一面,说这句话的人很多时候潜移默化地把自己那套胜者为王的价值观灌输给听的人。但自我的价值,就是只有自我才能决定的。我现在就要举手发言,站起来抢答,我认为我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就是嗑瓜子儿怎么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评价我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定义我选择的好坏。人不应该站在上的角度,去轻视下的人生,判定往下就是胆怯,就是平庸。
以前的我相信,我可以成为我想成为的人,但现在的我相信,我可以不用成为任何人。在回纽约的飞机上,我重看了一遍《大内密探零零发》。零零发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后才获得了皇上的青睐,但他最后抛弃了大内密探的名头,只因妻子嘴角的一滴血。零零发抱着妻子飞向太阳,机舱里昏昏沉沉的我差点掉眼泪,我看到一只自由的鸵鸟,飞向了他的草堆。
责编:方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