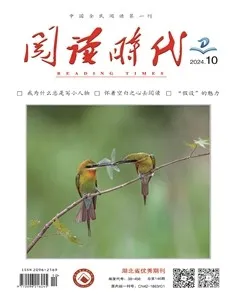经济学家如何理解《春江花月夜》

在人们对祥瑞的期盼中,《春江花月夜》的场景重现。不同的人对场景、对作品有不同的体验和理解,但读到这首伟大诗篇,人们会不约而同地心旷神怡,可能又有些“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知止”。那么,在物质化和经济主义盛行的当下,经济学家会如何或应如何理解这首颇有超尘脱俗意韵的诗篇?
时间之困窘
《春江花月夜》最打动人们的也许是其时间思绪。江流不息,无疑使人想到时间流逝。哲人孔子就曾临川浩叹,“逝者如斯夫”!王羲之在暮春之时与群贤会于兰亭,即便列座于细小的流觞曲水边,然而仰观宇宙之大,也慨叹许多事物俯仰之间即为陈迹。李白何等豪放飘逸,在春夜宴桃李园时,不禁生出“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的感伤。但是张若虚不一样,他在“滟滟随波千万里”的长江边,在“皎皎空中孤月轮”的花夜里,面对神奇的永恒,他思维所向,是“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是“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是“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张若虚的时间,其实就是世人的时间,他以诗化的流川孤月,将时间永刻于不息的水流与月光,塑造出诗词学家叶嘉莹所说的文化“语码”。而以世人的营生为研究对象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却陷入了时间之困窘而难以自拔。
经济学在其萌芽阶段,就隐藏了时间意识淡漠的内在缺陷,斯密仅仅在论及物品积蓄和资本积累等少数议题时,简略地提到了时间因素。马歇尔的确指出过,由于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所以必须考虑人的生命时间,但他作为经济学的真正奠基人,并没能完成这个理论任务。米塞斯对经济学中的时间也高度重视,提出了“时间的经济”这个概念,强调了人类行为中,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凯恩斯曾精辟指出了时间的不可逆性,新剑桥学派的罗宾逊就对凯恩斯的“历史时间”赞不绝口,正因为此,凯恩斯强调短期经济景气是重要的,政府短期干预政策是必须的;而且我们应该理解,他本人并不会执着于什么宏观均衡理论,因为在“历史时间”中,哪有什么均衡。许多当代经济学家,如戴蒙德等人,也曾致力于给时间建模,但可惜的是,经济学成型之后,时间的轴线也只能算是聊胜于无。
至今,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模型层出不穷,但对时间的考虑,主要还是以贴现率、变化的速率等方式来处理,生命周期动态分析、世代交叠模型已经是很先进的分析方法了。这些处理方式顶多只是给予时间一个线性的、可逆的地位,把经济活动中的时间流逝进行了匀质化处理,假定了每一个时段、每一个时点的价值完全一样,假定了这个人的时间跟那个人的时间可以相互替代。这完全不符合真实世界的情况。现代经济学的重大困窘之一,就是如何把非匀质、非可逆的时间找回来,带回到分析框架中,整合到模型中。如果经济学能够走出时间困窘,也许经济学著作可以像诗歌名篇那样熠熠生辉。
有限之约束
经济学的本意,就是认为资源是稀缺的、有限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非常“硬核”。而诗人却可以奇妙地兼有“硬核”和“软核”。晏殊不是吟咏“一向年光有限身”吗?但他也有“无穷无尽是离愁”的句子。苏子呢?在长江里,赤壁下,羡长江之无穷,耳得江上清风而为声,目遇山间明月而成色,故曰“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但他对水与月也会作如此辩证的理解:逝者如水未尝往,盈虚如月莫消长,自其变者而观之,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而张若虚则是把有限和无限融合得最为天衣无缝的诗人。他的思绪,飞向明月共潮升处的浩渺沧海,飞向江天一色无尘的无垠苍穹,飞向白云悠然而去的乌有远乡,顷刻之际,又栖落到凡尘的青枫浦、妆镜台、捣衣砧;由无限路的碣石与潇湘,到有限春的可怜不还家;从无尽流的江水,到去欲尽的春天,有限与无限交织在一起,使人难以分辨。
当经济学家看到他描述的这一切,禁不住也要拍案叫绝。因为张若虚在他的《春江花月夜》中,写得分明,“不知乘月几人归”;在他的另一首诗《代答闺梦还》中,也写得晓畅,“风花暝不归”。他仅存的这两首诗,都以“归”收尾,是否因为,曰归曰归,却少有同路人,从而令他们如此寂寞,恰如范仲淹所喟然感叹:微斯人,吾谁与归?
经济学家不可能以诗人手法将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张力进行缓和,但的确已经引入了越来越多的有限性分析。随着学科的发展,斯蒂格勒、斯蒂格利茨以及菲尔普斯等人,认识到了信息的有限、不完整、不对称,认识到获取更真实更完整信息需要高昂成本,从而与其他经济学家一道,开创了信息经济学。更新近一些,哈特分析了合约的不完全性,泰勒等行为经济学家还强调人的自制力的有限性。这些关于“有限”和“不完全”的分析,不但丰富了经济学的内容,也使得经济学与现实世界更加贴近,使得人们从中能够感觉到尘世凡人的脉搏和体温,使得这门“硬核”学科增添了人的灵性和诗情的“软性”。
通过这些理论上的努力,经济学似乎可以处理更多的有限约束。但是,现在经济学家们又开始畅游于信息资料和大数据的海洋之中,却对其所置身之处的无限性缺乏清醒认识。经济学许多模型依赖大量的数据采集作支撑,超级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又给了经济学家处理海量数据的可能。不知道是否有足够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在宇宙运动面前,在人间经济面前,现在所有的海量数据,以及未来所有的海量N次方数据,永远都是有限的数据。
如果我们看到一些模型尽管有着数以百计的参数,有着数以百万级的数据输入,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形,并不要感到吃惊。因为无论发掘出多少数据和信息,都不过是沧海一浪而已,它可能告诉了我们这是一滴水,但并不一定能告诉我们这是哪片海。哲人庄子曾经看似无奈实则沉静的说过:知也无涯。无论科技如何发达,数据如何丰富,都无法改变这一点。
判断之迷离
经济学家应该从《春江花月夜》之中理解到一种难以判断、欲此却彼的迷离,并引起共鸣。这种迷离感可能是杰出诗人的普遍营造,特别是置身于浩瀚而朦胧的场景之时。张若虚在他构建的空前绝后的诗人宇宙意识里,以寥廓、清旷的境界为场景,恰如闻一多所说,仿佛有一个神秘的渊默微笑,但更迷惘,也更满足。月光看似皎洁明亮,但汀上白沙看不见;游子与家人同望月轮,但此时相望不相闻;鱼雁据说可以传书,但鸿雁长飞光不度。远耶,近耶,非耶,是耶,都在《春江花月夜》当中。
月夜的张若虚,似乎与造物主有直接的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所以才有渊默微笑和心满意足。这与瓦尔登湖月夜的梭罗,是一样的极天极地皆忘机的超验情怀。当梭罗泛舟于瓦尔登湖面上,看见孤月悬于浩瀚无垠的天穹,亦游于波光树影的湖底,遂独自吹笛,让思绪把人类和宇宙联结起来,难道没有那种会意吗?这也与湘江月夜的旷敏本,是一样的出世入世皆悠悠的非凡情愫。当旷敏本登山于月色中,吟咏“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难道没有那种会意吗?而笼罩张若虚和梭罗、旷敏本的“月华如练”,是否仿佛罗尔斯所述的无知之幕,笼罩处于原初状态之人?或许罗尔斯自己也在晚年岁月,陷入了判断的迷离之中,从而又对他一生钻研的正义和自由的理论,作出了修订。这些诗人和哲人,是否因欲挣脱时间之困窘、有限之约束、判断之迷离,才与宇宙直接对话,与自然直接交流,从而获得超验启发?
经济学家同样如此。经济学家有高谈阔论之潇洒,也有判断迷离之落寞。既然经济学的核心主题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那么,这门学问能够以纯粹理论的范式来证明:凡尘俗世中何样的资源配置方式会更有效率?如果深入了解经济学理论范式,就难逃一张判断迷离之网。这张恢恢天网,还可能把人带入对世界秩序、人类秩序的迷思。因为本质上,经济学也隐含了对宇宙秩序的探寻和理解,这种理解至少可以上溯到阿奎那,他是中世纪的哲学家和神学家,《经济学说史》也把他当成经济学鼻祖之一。阿奎那对私人财产、公平价格和公正交换的论证,实际上包括了他对秩序和正义的理解,这种理解是一种不证自明,是一种永恒。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兰格也使用一般均衡论的数学处理方法,证明了计划经济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到了20世纪60年代,兰格用一组非常完整严密的模型进一步证明,使用计算能力强大的计算机,计划经济更容易实现完美秩序。但是,上述两种完美,都建立在各自的诸多假设之上,由于这些假设在现实世界并不存在,所以令人不胜迷惘,也不胜唏嘘。
现今的经济学分析工具比百十年前更加丰富和缜密,各种动态模型有着精巧设计和众多变量,体现了逻辑之美和数理之严。但是,许多参数的取值仍然依赖经济学家的个人选择,需要他们对未来趋势进行判断。正如奈特所说,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而经济学家需要在不确定当中给参数取确定值。所以,经济学家有时需要在模棱两可和朦胧迷离中,寻找方向,选择泊位。
(源自“经济学家圈”,叶子荐稿,有删节)
责编:小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