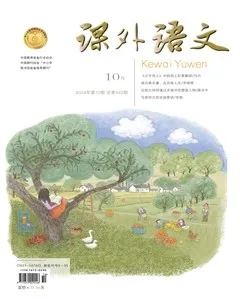《琵琶行》中的『跨文化﹄交融与和解
很多文学作品都深刻描绘了当时的时代文化背景,比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文章中写生活日常,融情于景、情景动人。所以,文章看似在写具体的情景,本质上还是在写文化。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可以很好地借鉴这种写作方式,让我们的写作更具内涵和深意。
对于很多人来说,文化似乎是一种高屋建瓴、虚无缥缈的事物,但实际上,我们身边处处都是文化的影子。文化本质上是一个民族历史、传统、宗教、价值观念、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综合体。而“跨文化”交流也随时都在发生,每一次“跨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都是一次深刻的身心理解与融合。比如当我们转换地域,用一种异质的视角来看待全新的地方,就是一种“跨文化”的解读,而这种从不了解到了解的过程,就成为很多名人常常提及的内容。
地域变化给人带来的改变是深刻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白居易的作品《琵琶行》中品味一二。从《琵琶行》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原本意气风发的诗人被贬黜到边陲之地后内心的迷茫和忧愤。白居易借着琵琶女的感情经历映射出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无助,表达他对繁华如花易逝的种种无奈。
白居易的《琵琶行》是长篇叙事诗的名作,《琵琶行》主要讲述的是诗人因送别朋友,而偶然遇到来自京都的琵琶女,进而邀请至送别船上弹奏。在弹奏中,作者感怀琵琶女的遭遇,也感怀自己遭遇的故事。下面,我们从“跨文化”的视角,来解读这篇作品。
一、独在异乡的身份认同危机
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看,《琵琶行》中,最大的文化差异体现在地域文化上的不适应。这一点我们需要结合白居易的生平来进行解读,这也是《琵琶行》写作的背景。唐宪宗元和十年(815),白居易遭到诽谤,说他的母亲看花时坠井去世,而白居易却写过有关“赏花”和“新井”的诗,有伤教化,因为这个不成理由的理由遭到了贬黜。白居易不得不从京都千里迢迢来到江州成为一名司马。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生活在不同价值观、规范等差异很大的文化背景中时,个体文化认同的建构和发展会遇到很大的阻碍。如果积极融入文化,建立一种认同感,就会实现身心和谐,反之,就会出现烦闷和阴郁的情绪。所谓诗人不幸诗文幸,很多诗作文章,也都产生于诗人的人生经历的巨大变化时期。白居易也不例外,这篇《琵琶行》就是其在身心备受折磨的时候写下的。
在《琵琶行》中,我们可以轻易看到作者对江州文化的种种不适应。“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司马是一个闲职,过去的白居易身居高位,在皇帝身边运筹帷幄,指点江山,但如今骤然变成了小小司马,身无要职,其中的冷落凄苦,着实让人难以承受。他对江州地区也充满了怨念,进而还出现了身体上的疾病。身处偏僻之地,没有美妙的音乐聊以慰藉,让作者内心更加生出一种巨大的割裂和不适应感。“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这句话以景写情,通过对一系列凄苦意象的描写,来展现作者的难过。最后,“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即使是美好的季节,也只能自己默默独酌。身处偏远,没有了故交旧友的陪伴,身边没有倾诉的对象,作者的一腔愁绪无处抒发,加上作者并不认同自己是江州的文化成员。文化认同是一种价值选择,认同某种文化就意味着选择了一种存在方式。作者在其中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感,形成了身份认同的危机。
二、远离主流文化的认同危机
除了地域文化上的认同危机,作者还存在一种远离主流文化的认同危机。原来身在京都,作者身居庙堂之高,身处京都文化圈,必然是“忧其民”,人人都有一腔报国情怀,朋友之间讲述的也都是国家大事、政治要事。在惊心动魄的政治角斗场上,白居易想来经历了很多激流险滩,但他始终坚持着自己“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但是身处江州之后,白居易的忧国忧民似乎变成了笑话,自己的影响力消失了,没有人再去听他讲话。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虽然白居易被迫离开京都,身体上离开了这片文化故土,但是精神上仍然将自己视作京都文化圈中的一员,因为听到琵琶女弹奏有京都声,就邀来一曲,可见一斑。这些都使得白居易在面对异质性文化时必然产生强烈的冲突。在此之前他以“兼济天下”为志,但如今却似乎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作者实际上也经历了一场文化认同的危机,在江州,他找不到自己的知心之人,没人理解自己的心境,这让作者内心的愁苦不断升级。
在《琵琶行》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有着很高的音乐造诣,其对于音乐意象的表现,古往今来人人称颂。但是作者关闭了自己,认为浔阳地区没有丝竹管弦之乐,“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展现了作者对于江州本地音乐的理解。以至于在听到琵琶女的弹奏之后,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美好音乐感受,“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也可以使用这种对比手法,给读者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进而更好地展现内心情感。在写到来自京都文化圈的琵琶女弹奏时,作者描写得极尽华丽,从“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小试牛刀,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的形象刻画,我们从作者的笔端,仿佛身临其境听了一场美妙的音乐盛宴。
三、镜像互文下文化交融与和解
在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看来,任何人都是通过与他人的交往来认识自己的,而他人身上和自己相似的残影,形成了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从这个理论来看,白居易和琵琶女,实际上形成了一种镜像。白居易看似写的是琵琶女,但实际上处处写的都是自己,通过展现琵琶女的悲惨遭遇,来实现对自己当下处境的一种倾诉,也在反观琵琶女的人生选择中,展现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实现与自我的和解。在这个过程中,白居易实际上无意之中打开了自己封闭已久的内心,将自己与江州这个文化圈实现了一次短暂的共鸣,从“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来展现这种融合和和解。通过写艺术境界之上的共鸣,实际上写出了作者如何实现自我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危机的和解,所以这也是为何作者最后会“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在《琵琶行》中,琵琶女演奏了三次。第一曲,琵琶女的弹奏主要是排解自身,有着天涯无处觅知音的孤独寂寥。文中写到“忽闻水上琵琶声”“寻声暗问弹者谁”,也因为“铮铮然有京都声”,打开了作者的心防。第二曲,琵琶女大展身手,用娴熟的技术为作者弹了一曲美妙音乐。是“大弦嘈嘈”“小弦切切”,是“间关莺语”“幽咽泉流”,这是琵琶女长久压抑的情感喷薄。琵琶女的第三次弹奏,作者没有直接描写,而是转而写她的身世,来侧面展示,最后“凄凄不似向前声”的琵琶曲,弹者与听者心灵相通。琵琶女是白居易塑造的琵琶女,在白居易眼中的琵琶女是经过了白居易意识选择和语言改造的。通过对琵琶女的描写,我们可以对比看到白居易的人生写照。年轻时的白居易得到皇帝的重用,奋发有为,报效朝廷,甚至还做着宰相梦,如同琵琶女“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结果却卷入党争,遭受排挤,被贬到蛮荒之地。 这一遭遇和琵琶女何其相似,琵琶女因为“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而不得不转变了人生道路。但其中和琵琶女悲惨命运相对的是,白居易虽然境遇和琵琶女相似,但是白居易显然想写出自己的选择。“弟走从军阿姨死”展现了白居易的反战意识,“暮去朝来颜色故”展现了白居易一定的自省意识。也正因为看清了自己已过气,“暮去朝来颜色故”,白居易后来对待官场慎之又慎,远离是非旋涡。与后来白居易选择“独善其身”的人生选择形成了一定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