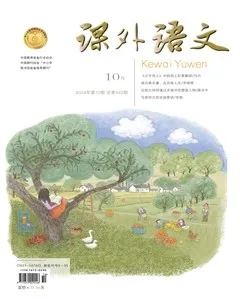从《驿路梨花》中探索一波三折的写作技法
彭荆风,我国当代军旅作家。《驿路梨花》作为他的经典短篇小说,以“我”的视角,讲述了“我”和同行老余借宿哀牢山深处一小屋时的经历,抒发了作者历经磨难重拾安宁后,对美好未来的呼唤和对少数民族人民诚挚纯善的怀念。“我”作为指路人,以“我”的视角指引读者在线性叙事中体验了一次空房子借宿的经历,看到了每一个“房子的主人”和“想要知道房子主人是谁的人”身上质朴、高尚且助人为乐的品性。而“我”不知且不懂之事,便是读者不知不懂之事。这篇小说的写作技法一波三折,既以悬念之法布满全局,又以误会之法推进叙事,再辅以烘托、描写、象征、衬托、倒叙、矛盾、先扬后抑等丰富的写作手法,让作品犹如文字插上翅膀,传递出小说独特的审美和意蕴,也让读者犹如置身故事中,心绪跌宕,意趣无穷。
一“悬”再“悬”,一波三折
所谓悬念之法,即文学、影视作品中借以激发矛盾的疑团设置,旨在引发读者联想,吊足读者胃口,推进剧情叙事,待得悬念解开时,横生波澜,增强作品意趣与内涵。《驿路梨花》多处设悬念,让作品整个内容构思先声夺人,情节一波三折,作品情节安排,看似情理之中,却又出人意料,以极强的戏剧性强化了作品艺术效果。
首先,先声夺人,开篇并不平淡。作品的开头,悬而不决,往往会让作品更具吸引力。《驿路梨花》开篇时,“我”和老余行至深山,意料之外地发现一处茅草屋,屋外梨花飘雨,“我”心下疑惑,这是谁的房子?“我”和老余走进后,意料之外地发现房门木板上用黑炭写着“请进!”,在情理之中本该有主人的茅草屋,也意料之外地空无一人,“我”和老余探讨这到底是谁的房子。暮色之中,“我”和老余吃住到底该归于何处?以此设置悬念,情节就此展开,三个“意料之外”,一个“情理之中”,读者阅读兴趣被充分激起。
其次,精细布局,情节一波三折。作品最忌流水席面,平铺直叙而毫无波澜的作品,往往毫无趣味性可言。因此,作品情节叙事应环环相扣。故事至此,情节还在缓步推进,瑶族老人出现,他扛枪提米,仿似那“风雪夜归人”,可能是房子的主人,但意料之外的是他并不是。“我”与老人关系渐缓,于是问及老人是否知晓主人身份,老人矢口否认,但观老人行事做法,颇有“主家”之感。随后便知,老人有与“我”一样的遭遇,也恰得相助,这一情节安排,更是大大出人意料。至此时,“我”和老余疑惑更甚,房子的主人到底是谁?不及弄清主人是谁,出乎意料,夜里“我”梦中出现了一个穿花衫的哈尼族小姑娘。这个哈尼族小姑娘是谁?她跟房子的主人是什么关系?不等“我”找到答案,一个能为群众着想的哈尼族小姑娘出现了,如果她是“我”梦里出现的那个姑娘,在情理之中;如果不是,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而她做了什么为群众着想的事?悬念堆叠,矛盾渐深,故事还在持续推进,而读者早已深陷其中,仿佛置身在“我”修屋挖渠的场景中。
最后,留白结尾,悬而未答引思。很多作品结尾处惯于呐喊口号,表明立场,看似荡气回肠,实则读之空乏无味。反之,犹如品茗般令人回味无穷的好结尾,则会为作品添上悠扬一笔,让作品久久引人沉浸和深思。看,更多的哈尼族小姑娘真的出现了,但她们是房子的主人吗?很显然也不是。那么,房子的主人究竟是谁?小姑娘说是解放军。可是,解放军只是房子的建造者。最终,“我”也没有真的知道房子的主人究竟是谁。作品以一句“驿路梨花处处开”,“匆匆”收了笔。但是,看似简单匆忙,然则采用了“留白”的艺术手法,再一次设置悬念,以“无言胜有语”的意境之感引发读者仔细品味,认真思考房子的主人究竟是谁。很多读者回过味来,会感叹一句“原来那些默默守护者、保护着房子的人,才是房子真正的主人”。但大多数读者不这样认为。
福特斯说:“布局良好的情节应该包含某些‘秘密’,随着故事情节发展,‘秘密’将显现在读者面前,并且使得整个故事体现出完整的结构之美。”《驿路梨花》始终以“房子的主人是谁”作为贯穿全文的“秘密”,层层悬念的设置,让作品情节起伏,波折再三,最终以“留白”留给读者无尽想象。可见,好的作品必不是平铺直叙,一叙到底。
二、“误会”丛生,情节起伏
误会法,简言之,就是在作品中有意识地设置误会,以行为、细节等将读者思维引向反方向,以“人造”悬念,推进剧情,引发读者兴趣的写作手法,分为正误、反误、一般误会和互误四种。《驿路梨花》中有两处情节使用了该法。误会一是“我”和老余都觉得拿枪扛米似归家的瑶族老人是房子的主人。误会二是“我”、老余和瑶族老人都认为哈尼族小姑娘是房子的主人。两处误会都由前面设置的悬念引发,而误会又进一步引发悬念。因此,《驿路梨花》中形成巧妙的“设疑—释疑—设疑”的环形构思与回环情节,以误会的消除和新悬念的产生扣人心弦。可以说,《驿路梨花》以悬念和误会,层层铺垫让哈尼族小姑娘梨花被追寻和猜想,情理之中的应该出场,而出乎意料的没有出场,仅是以呼之欲出之势就牵动所有读者的心,以悬念铺展情节,以误会推进情节,故事情节曲折,人物个性塑造鲜明。不正应了作者那句“特色和新意”吗?
三、“梨花纷扬”,手法迭起
除了作品中起起落落的悬念设置和误会安排,作品中还使用了大量的烘托、描写、象征、倒叙、矛盾、先扬后抑等创作手法。比如,作品中以正面描写刻画了“我”、老余、瑶族老人等人物形象,以侧面描写刻画了姐姐、解放军战士等人物形象。以“梨花”象征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以“驿路梨花处处开”描绘美景,同样也赞美奉献精神。除此之外,作品中还出现了大量映衬的修辞手法,以客观事物相似或相反的关系衬托作品形象。
首先,花与人的映照衬托。梨花本为自然之物,清雅淡泊,雪玉洁白且清香四溢,是很多文学作品中争相称颂的美好事物,且多用以映衬人物,正所谓,“以花衬人,人比花娇”。而《驿路梨花》中出现的本真“梨花”、梦中虚幻“梨花”、结尾处眼前的“梨花”,都以映衬人物主体而存在,以梨花衬托小姑娘的简单纯真和灵动美好,凸显少数民族地区民风的淳朴自然。“梨花”二字似乎早已成为一种象征美好的精神符号。很显然,在《驿路梨花》中,人与花早已不分彼此,合二为一。
其次,明与暗的映照衬托。彭荆风谈及《驿路梨花》的创作时曾言:“我认为生活中无处不包含色彩,特别是在多彩的云南边地。色彩不仅流露于外,更是蕴藏于人们的内心。对色彩的描写,不单纯是写景,它还应该贯穿于人物、语言、情节、故事之中……《驿路梨花》抒情味是较浓的,我喜欢用这种笔调写边疆生活、边疆风貌。”《驿路梨花》中就巧妙地以色彩的明暗对比完成了边疆少数民族人文风情画面的勾勒与描绘。作品开篇写到“青山”“暮色”,以暗打底。忽而,笔锋之下出现“梨花”“月光”,由暗转明。而这一转变也反映出“我”和老余由忧转喜的心情,为故事推进造势。此外,“黑屋”与“白门板”、“白羽毛”与“红布”等色彩对比的应用,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最后,虚与实的映照衬托。虚与实作为矛盾的辩证统一体,在文学艺术中的应用比较普遍,而“虚”并非就是无,“实”也不等于现实,而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托之势隐藏于对方之中,让作者以虚实互补、相得益彰的方式落笔成篇,既可以拓展作品意境,也能够强化审美价值,让读者在作品中获得无尽的想象空间。《驿路梨花》中的“梨花林”是作者笔下寄托理想的画意之境,此为“虚”,作品创作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地区民风淳朴此乃“实”,虚实结合,表达了作者对美好人性的想象,寄托了对美好社会环境的殷切盼望。此外,出现了的“我”、老余、瑶族老人等与没出现的哈尼族小姑娘、解放军叔叔等形成“虚”与“实”的映照衬托。其他自然景物相关的描绘中,凸显虚实结合的也比比皆是。
歌德说,只有对自己所表现的东西怀着深情的时候,你才可能淋漓尽致地去表现它。彭荆风的“淋漓尽致”不一定是《驿路梨花》,但《驿路梨花》的淋漓尽致,一定是悬念迭起的故事背后对美好的祈愿与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