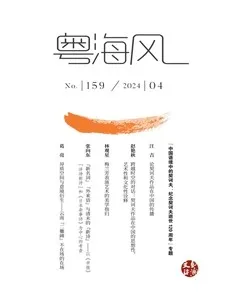论契诃夫作品在中国的传播
摘要:整体而言,契诃夫作品在中国百余年的传播与诠释自有其脉络和层次。简单而言,我们可以从文体层面分论其小说、戏剧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可以缕述国内对他的总体评价,反观他对中国文学的各种影响。这些演变反映了中国文学界对契诃夫价值的不断挖掘和理解深化,同时也映照出中国社会历史背景的变化与文学观念的演变。
关键词:契诃夫 中国 传播 中国文学
契诃夫(1860—1904)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位作家,他的许多作品都曾入选教科书。1904年6月,早已身患肺结核、身体每况愈下的契诃夫赴德国巴登魏莱尔疗养,随后出现了心力衰竭,7月15日在巴登魏莱尔去世,年仅44岁。但就在这短暂的生命旅途之中,契诃夫留下了令世界瞩目的文字,受到世人的敬仰。
契诃夫的小说虽然没有托尔斯泰作品中史诗般宏大的场面,也少有屠格涅夫小说中田园抒情诗般的爱情悲剧,但他创作的见风使舵的“变色龙”奥楚蔑洛夫、战战兢兢装在套子里的别里科夫、唯唯诺诺的小公务员切尔维亚科夫等文学形象是如此鲜活,他笔下描绘的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市井小民的喜怒哀乐又是如此贴近我们的生活,总在不经意间牵动我们的心。
契诃夫作品题材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既有反映底层老百姓悲惨生活的《苦闷》《凡卡》,也有描写小人物战战兢兢心态的《小公务员之死》《胖子和瘦子》,还有讽刺某些人物见风使舵、奴颜媚骨的《变色龙》,更有揭露专制制度对人性极端摧残压制的《套中人》。契诃夫的作品文短气长,描写人物一针见血,开门见山,许多作品被视作经典广为传颂,在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坛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契诃夫也由此与莫泊桑、欧·亨利并称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曾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类文明是由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在他举例提到的一系列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文艺大师名单上,契诃夫就位列其中。
第一个向契诃夫表达敬意的中国人可能是徐志摩。1925年徐志摩来到俄罗斯,专门去了两个墓地,其中一个就是契诃夫的。在《契诃夫墓缘》中,徐志摩专门记录了他探访契诃夫墓地时的所感:“当我站在契诃夫的墓地的时候我就想,假如契诃夫还活着,他会怎么样?”在遥远的中国,有那么多人在120年以后还能想起他、纪念他。
一、契诃夫小说在中国的传播
如果从1872年《中西闻见录》创刊号刊出《俄人寓言》算起,俄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已经走过近一个半世纪的历程。五四以前的近半个世纪,俄国作家及其作品已陆续被介绍到中国,不过当时的译介量不多,影响不大。俄国文学真正为中国文坛所关注,并对中国文学产生实际影响,始于五四时期,彼时中国出现了俄国文学译介“极一时之盛”的局面。茅盾说,当时“俄罗斯文学的爱好,在一般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种风气”。1920—1927年期间,中国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有190种,其中俄苏文学的翻译近五分之二,大大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被译介数量。这些单行本中,有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众多名家的名作。这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密切关系,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中国,中国的革命者把苏联视为圣地,中国的知识分子当然也把俄罗斯文学和作家视为榜样。
契诃夫在世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了解他的作品,但这些作品都是日文版或英文版。1907年,吴寿将《黑衣修士》译介给中国读者。1909年,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合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其中收录了契诃夫的《在庄园里》和《在流放中》。同年,上海的《小说日报》登载了契诃夫的《第六号病室》。1916年中华书局推出了陈家麟、陈大镫译述的契诃夫第一部中文短篇小说集《风俗闲谈》(上下两册),其中收录了他的23部短篇小说。五四时期,他的作品被广泛翻译,陆续出版,包括耿济之、耿勉之译的《柴霍甫短篇小说集》(当时契科夫被译作“柴霍甫”)、王靖译的《柴霍甫小说》、小说月报社编辑的《犯罪》、张友松译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集》《三年》、赵景深译的《悒郁》,还有东方杂志社编的《近代俄国小说集》第三集(为契诃夫个人专集)。这些集子总共辑录了契诃夫小说44篇,其余散见于报刊。尽管如此,五四时期对契诃夫作品的翻译、出版还是相当不够的,零散的翻译及有限的数量使契诃夫作为短篇小说大师的形象只能在当时显露出冰山的一角。
五四后的十年间,契诃夫的许多作品都被翻译成中文。在他作品的译者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赵景深,他翻译了契诃夫的162部短篇和中篇小说,并于1930年以八卷文集出版。除此以外,译者中还有瞿秋白、曹靖华、鲁迅、郑振铎等人。1921—1922年,瞿秋白在苏俄写了《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在第14章中他提到了契诃夫的创作,称其作品是19世纪80—90年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佼佼者。契诃夫深刻洞悉当代人的心灵秘密,是那个时代的真正代表。他的作品所讽刺揭露的社会问题,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也非常尖锐。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学习契诃夫,与当时深深渗入中国社会并戴着虚伪面纱的封建和资本主义反动腐朽思想进行斗争。
由赵景深译、开明书店出版的《柴霍甫短篇杰作集》(1—8卷),第一次规模化地初步展现了契诃夫小说世界的概貌。这套丛书大致按类分卷:恋爱题材集中于《香槟酒》《女人的王国》《妖妇》几卷;带有悲观、神秘和恐怖色彩的题材收入《黑衣修士》;少年儿童题材收入《孩子们》;还有滑稽短篇《快乐的结局》、乡村景物《审判》、宗教题材《老年》。该《杰作集》共收录契诃夫作品162篇。比较199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契诃夫小说全集》(收入480篇译作),可以大约估定这套丛书辑译了契诃夫全部小说的三分之一。开明书店原与赵景深订约翻译契诃夫小说全集,为此,赵景深于1928年辞去了开明书店编辑职务,安心译书。赵景深本拟以Constance Garnett(康斯坦斯·加内特)的13卷英译本为底本进行翻译,但由于普罗文学崛起,赵景深认为旧俄的作品已不时髦,担心书店亏本,且自己的兴趣想法也发生了变化,最终未能完成计划,无法称之为“小说全集”,才改为“杰作集”。一直到40年代末,还没有译者能够继续赵景深未能完成的事业——出版一套契诃夫小说全集,可见赵景深在当时是最具有雄心和毅力的译者了。他的八卷本《柴霍甫短篇杰作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独领风骚,是契诃夫小说的主要汉译本,是对其作品最全面的介绍。
赵景深的译文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翻译界代表着与“直译”相左的一种风格。他论翻译的第一句话就是“译书应为读者打算”,在“译得错不错”与“译得顺不顺”之间,他认为“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错不错”反而是“第二个问题”。因此,出现了广为人知的受到鲁迅批评的“牛奶路”译法这一翻译史上的趣事。之后的翻译实践证明,赵景深的译法之路是不通的。这也难怪赵景深的《柴霍甫短篇杰作集》未能流传下来。不过,赵景深的译本在题材、主题、情节、人物方面还是忠实于原著的,使国人能够了解到契诃夫小说的概貌,在一段时间内发挥了它的作用。
赵景深的译本出版后,仅有蒯斯勋和黄列那译《关于恋爱的话》、华林一译《吻》、鲁迅译《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几个薄薄的短篇小说集。《坏孩子和别的奇闻》中翻译了契诃夫的八篇短篇小说,鲁迅在前言中写道:“这些短篇,虽作者自以为小笑话,但和中国普通之所谓趣闻却又截然两样的。它不是简单的只招人笑。一读自然往往会笑,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就是问题。生瘤的化装,整脚的跳舞,那模样不免使人笑,而笑时也知道:这可笑是因为他有病。这病能医不能医。”此外,还有徐培仁译的《厌倦的故事》、彭慧和金人分别翻译的《草原》等几个中篇。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年,中国文学界以极大的热情全面介绍俄苏文学。20世纪50年代,被译介的俄苏文学作品总量大大超过前半个世纪的总和。有人做过统计,当时几家主要的出版机构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各出版了三四百种俄苏文学作品,各家印数均在一两千万册;从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中国共译出俄苏文学作品达3526种(不计报刊上所载的作品),印数达8200万册以上,它们分别约占同时期全部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种数的三分之二和印数的四分之三。这时期俄苏文学的翻译质量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批经过正规院校培养的译者加入了俄苏文学的翻译队伍,俄国文学作品大多通过其他文字转译的现象得到了根本的扭转。俄国古典文学的翻译量虽然不能与苏联文学相比,但是其繁荣景象也是前所未有的。
20世纪60—70年代,中苏政治关系全面冷却,两国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发生猛烈碰撞。与此相应,中苏文学关系也进入了长达20年的疏远、对立,乃至严重冰封的时期。1962年以后,中国不再公开出版任何苏联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1964年以后,所有的俄苏文学作品均从中国的一切公开出版物中消失。直到70年代后期,才有数量十分有限的俄苏作品中译本出现,这种情况直到80年代才有了根本变化。
在改革开放的良好氛围中,80年代的译介总量大大超过20世纪的任何一个时期。期间,中国翻译出版了近万种俄苏文学作品(包括单行本和散见于各种报刊中的作品),涉及的作家有1000多位。而这种译介态势又是在中国前所未有地全方位接纳外来文化的热潮中出现的。
与当代文学作品译介量锐减的状况相反,因不受版权制约和具有名著效应,俄国经典文学名著的出版在这一阶段再度繁荣起来,大量名著被重译。继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版了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多卷本文集后,90年代初期和中期又相继推出多位俄苏作家的全集(或文集),包括《普希金文集》《莱蒙托夫全集》《果戈理全集》《涅克拉索夫文集》《屠格涅夫全集》等。
在我国外国文学爱好者心中,契诃夫最权威的中译本出自翻译家汝龙先生。汝龙之于契诃夫,正如傅雷之于巴尔扎克,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亚,草婴之于托尔斯泰。
2014年、2015年分别是契诃夫逝世110周年和诞辰155周年,当时文化界掀起过纪念这位巨匠的热潮。2016年,又恰逢汝龙先生百岁诞辰,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由他翻译的《契诃夫小说全集》,献给喜爱契诃夫和汝龙的广大读者。汝龙是一个富有理想、毕生辛劳、淡泊谦虚,以翻译工作为自己终身事业的人,一生翻译的作品达1000多万字。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人们很少看到俄语书籍,所以当时他只能通过英文译作转译契诃夫小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使译作更加忠实原著,他发奋从头开始自学俄语,并买了俄文原版的契诃夫全集,其后又几乎将以前转译的契诃夫作品全部重新翻译了一遍。
二、契诃夫戏剧在中国的传播
2008年是中国人走近契诃夫非常关键的一年,因为这一年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戏剧节,而国际戏剧节的口号就是“永远的契诃夫”。当时不少媒体和作者质疑道,契诃夫不是一个小说家吗,为什么要举办一个契诃夫国际戏剧节?但是当戏剧节举办完以后,再没有人有异议了。可见在中国,长期以来,契诃夫作为小说家的名气要远大于作为剧作家。
五四时期,中国人对作为戏剧家的契诃夫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被看作是俄国唯一能称得上“世界著名之剧作家”的人,其剧作格外受重视。1921年契诃夫的五部多幕剧中有四部——《海鸥》《伊凡诺夫》《万尼亚舅舅》《樱桃园》被作为“共学社俄罗斯文学丛书”中的《俄国戏曲集》的组成部分,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在这部戏曲集收录的十种剧本中,契诃夫一人就占了四种,除《海鸥》是郑振铎根据英译本翻译的外,其余三种都是耿式之从俄文直接翻译的。
1925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曹靖华译的契诃夫的另一部多幕剧《三姊妹》,至此,契诃夫的五部多幕剧全部出版。曹靖华继续翻译了契诃夫的独幕剧《纪念日》《蠢货》《求婚》《婚礼》,1929年被收入《未名丛刊》出版。之后,何妨又翻译了契诃夫的一部无题四幕剧《未名剧本》,由正中书局于1935年出版。
契诃夫的戏剧第一次搬上中国舞台是在1930年,上海的新友剧社上演了他的《万尼亚叔叔》。在抗日期间,他的《樱桃园》受到巨大欢迎,而在解放区,《求婚》《熊》《纪念日》等也很受欢迎。
20世纪40年代是契诃夫戏剧中译进入系统化的大收获时期。文化生活出版社选编了“契诃夫戏剧选集”六种,除收录契诃夫的五部多幕剧外,契诃夫的九出独幕剧也由李健吾翻译,全部编入《契诃夫独幕剧集》。契诃夫戏剧的最佳译者是焦菊隐,他翻译了契诃夫的全部五部多幕剧,李健吾则翻译了契诃夫的一幕剧。
三、国内对契诃夫的评介
对契诃夫的评介,当时文坛也主要受到国外,尤其是苏联、日本批评家的左右,翻译家大多喜欢在译本前后附上他们的既有评论,或加以综述,很少发表自己的见解。如赵景深翻译的八卷本《契诃夫短篇杰作集》,每卷前面都分别附上一篇契诃夫亲友的回忆文字,还有美国、波兰批评家的评论。杂志上发表的对契诃夫的长篇大论,大多也都是译文。随着契诃夫在中国传播的广泛和深入,对他评介与研究的专著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也开始翻译进来,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伊尔·柴霍甫著《柴霍甫评传》,由陆立之翻译,神州国光社于1932年出版。毛秋萍翻译的苏联弗里采著《柴霍甫评传》,于193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40年代以后,开始有国内研究者的专著出现,肖赛于1947年和1948年接连出版了《柴霍甫传》和《柴霍甫的戏剧》(文通书局)。
五四时期契诃夫在中国的形象是一位悲观主义者,这种看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1924年为纪念契诃夫逝世20周年,曹靖华翻译了《三姊妹》,并根据《柴氏文集》第一卷上的《柴霍甫传》和伊万诺夫·拉祝姆尼克著《俄国文学》中论柴霍甫的一章,编写了长达近两万字的《柴霍甫评传》,其中心论题就是:契诃夫是否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文章细致地梳理了契诃夫不同时期的创作风貌,认为19世纪80年代的契诃夫“是一个忧郁的悲观主义者,并那悲观主义根深蒂固的盘结在他的心灵的深处”。由于契诃夫的小说大部分创作于这个时期,这些小说就可以证明,“柴氏对于人生的见解是悲惨的、失望的,生活原来就是凡庸的。这就是悲观主义的绝对重要的特质”。
19世纪90年代以后,契诃夫虽然树立了“进步的信仰”,相信“再过二三百年,一切生活凡庸的根性就消灭了,新生活的霞光就照耀出来了”,这些信仰在他创作于90年代初的小说《第六号病室》《好人》《我的生活》和剧作《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中表现出来。但文章仍然认为,进步的信仰还是不能满足他,或者只能满足他的一小部分,因为毕竟契诃夫自己“常常的觉得人类美丽的生活,是现在就需要的,即刻就需要的,不是过了二三百年之后才需要的”,所以在契诃夫的作品里,“抑郁悲观的色彩”“始终比愉快的色彩重得多”。茅盾也认为:“柴霍甫对于人性及其弱点是有深刻的理解的。他走上文坛的时候还能轻松地笑,但立刻他沉入悲哀失望的浓雾。直到他死,他是悲痛地呻吟着,他不曾有过乐观。”《柴霍甫评传》的译者陆立之则说得更绝对,认为作为一个“挹郁,悲愁与厌世”的悲观主义者,柴霍甫“没有勇气反抗时代的精神,只时常是呻吟痛苦和烦恼,他至多只在小说中冷讥热讽的指摘社会的病态,但只是指摘而已,却没有直接反叛的思想”,因而断定“柴霍甫对我们的时代——二十世纪的新时代,并没有什么特别贡献,他虽有一些特长,他虽是个讽刺作家,但那些细微得像蚂蚁般的东西,对我们只能留一些历史的痕迹”。“柴霍甫不过是一个寻常小说家而已”,“柴霍甫的讽刺已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了,在我们的时代中已不需要了”。
1929年为纪念契诃夫逝世25周年,鲁迅翻译了俄国列夫·罗加切夫斯基的《契诃夫与新文艺》,他认为这是一篇“很平允的论文”。这篇文章认为,俄国19世纪60年代的作品都留有“事业”的痕迹,“他们的艺术,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表现的样式,则是达到目的的工具”。契诃夫“只想做一个自由作家”,对于艺术的这种“不带什么一定的倾向”的新态度,使他能够把“真理和艺术融合起来”,“将俄国社会的倾向,比谁都说明得更锋利,暴露出国家的基础的丑态和空虚”。
几乎与此同时,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在我们时代里的契诃夫》也被翻译引进。这篇文章把契诃夫和苏联新文学、新时代联系在了一起,着重阐述了契诃夫的现实意义。文章认为,契诃夫的苦闷是“人类的真实而深刻的苦闷”,因而,他“仍不失为一个安慰者,显现于契诃夫作品中的世界一切的基石都要破坏了,伟大广袤的新国度的地平线可以看见了”。这使“契诃夫那个时代的最年轻,最有能力的社会阶级,藉他所表现的图画而醒悟而愤怒了”。继而他进一步论述说,契诃夫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代表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结、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还因为“我们的国度里充满着旧时代的残迹,而建立新国的工程尚未达到完成时期。在我们的周围密密地包围着旧时代的尘埃、细菌和朽蚀的败类。正需要大量而复杂的社会消毒剂去消灭这些包围着的,旧时代的痕迹”。所以“契诃夫在我们世界中永远生存着的原因,不单单为了他留着伟大的作品,其实因为他是战斗者的一员”。文章还高度评价了契诃夫“关于当时环境的真确的纪实”的写实主义,认为“这种新方法在我们新文学军队中,无疑是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卢那察尔斯基的这篇文章为肯定契诃夫对于苏联革命的积极意义定了一个基调。
随着对契诃夫生平事迹的大量译介,特别是胡风为纪念契诃夫逝世30周年而翻译的高尔基写的《契诃夫:回忆底断片》给中国读者描绘了一个迥然不同的契诃夫。胡风在后记中说:“契诃夫底作品似乎被介绍了不少,但他在我们底眼里只是一个冷冷的‘厌世家’,但很奇怪,从高尔基底回忆里,这位‘厌世家’却能够给读者一种为我们骂契诃夫的‘乐天家’所梦想不到的向黑暗的人生搏战的勇气。”1944年纪念契诃夫逝世40周年时,胡风就彻底为契诃夫翻了案。他在《A.P.契诃夫断片》中逐一批判了把契诃夫看作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凡俗主义底宣传者,小事件底迷恋者”“意志软弱的人”“客观主义者”,其作品“没有内容没有思想”的观点,认为“在前世纪末和本世纪开头的艺术文学的领域中,他是感觉到革命之不可避免的第一人”。“他底生命通向着他预感到了的东西‘所昭示的前途’,也就是俄罗斯正在走向的前途。”邵荃麟也写了《对于安东·柴霍甫的认识》一文,以矫正人们对契诃夫的“误解”。
从一个悲观主义者、厌世家到战斗者、勇士,其间的跨度不可谓不大,先不说究竟哪种认识更是对契诃夫的误读、把苏联革命强加到契诃夫所梦想的新生活上是否合适,赋予契诃夫描写灰色、黑暗、凡俗以“标志着一个阴暗的忧郁的旧时代的终结”,一个新时代开始的预言这样一种积极的意义,却意想不到地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以来小说与戏剧的一个相当典型的主题模式。
四、契诃夫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契诃夫的作品传入中国虽然较早,但其影响不能不说相对滞后,可对于鲁迅是个例外。20世纪40年代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契诃夫对鲁迅的影响,郭沫若为纪念契诃夫逝世40周年曾专门著文,认为“鲁迅与契诃夫的极类似,简直可以说是孪生的弟兄。假使契诃夫的作品是‘人类无声的悲哀的音乐’,鲁迅的作品至少可以说是中国的无声的悲哀的音乐。他们都是平庸的灵魂的写实主义”。他认为“前期鲁迅在中国新文艺上所留下的成绩,也就是契诃夫在东方播下的种子”。但对于鲁迅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来说,似乎是在经历了五四狂飙突进的理想时期和革命的亢奋年代以后,就像张爱玲所言,在经过了人生飞扬的放恣的一面以后,落在地上,踩到了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这平实的生活,认识了这人生的素朴的底子以后,才开始真正理解和接受契诃夫。
契诃夫作品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作家,巴金、沈从文等就曾公开表示受到他的熏陶,著名作家冯骥才也曾在文章中说:“在俄罗斯作家中,我受契诃夫影响最大。我迷恋他到处闪烁灵气的短句子,他那种具有惊人发现力的细节,他点石成金的比喻;更迷恋他的情感乃至情绪,他敏感的心灵,他与生俱来的善良和无边的伤感。”2002年夏天,冯骥才访问俄罗斯时专门到新圣女公墓,在契诃夫的墓碑前献上一支鲜红的康乃馨。
巴金自述他对契诃夫由隔膜到热爱的过程很有代表性。20岁时,巴金第一次接触契诃夫的作品,但他“读来读去,始终弄不清楚作者讲些什么”。20世纪30年代,当他怀着一种“永远不能够熄灭的热情”,拿起笔要呼唤和自己一样的青年人起来斗争,去“征服生活”的时候,他再读契诃夫,虽然自以为“有点了解契诃夫了”,但仍强烈地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不一样”,有时候竟会“读得厌烦起来,害怕起来”,窒闷得“忍不住丢开书大叫一声”,那时,他也多少把契诃夫看作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直到40年代,巴金说,当他“穿过了旧社会的‘庸俗’、‘虚伪’和‘卑鄙’的层层包围”以后,他才“不能不想到契诃夫,不能不爱契诃夫”。是“长时期的生活”,使他成为一个“契诃夫的热爱者”。他理解了从契诃夫那颗“真正的仁爱的心”中发出来的忧虑、关心和警告,也懂得了高尔基对契诃夫评价的意义:“契诃夫首先谴责的不是个别的主人公,而是产生他们的社会制度;他悲悼的不是个别人物的命运,而是整个民族——祖国的命运。”这也正是巴金对自己作品主题一再进行阐释的观点。对契诃夫的热爱和师法,使巴金的创作生活,从40年代起发生了与以往迥然不同的变化。在《憩园》里,作者对同样是大家庭的败家子杨老三就不像《家》中的克安、克定那样充满仇恨和厌恶,而是像契诃夫那样,怀有一颗“仁爱”的心,温和而诚恳地倾诉着自己的忧虑、关心和警告。最明显的当然是《第四病室》这部中篇,简直可以说直接化用了契诃夫《第六号病室》的主题和象征方式。《寒夜》则表明巴金已经掌握了契诃夫写实主义的精髓,标志着他师法契诃夫,从热情奔放的“青春型”激情抒发,转变到深刻冷静地揭示人生世相和没有英雄色彩的“小人物”日常琐事的悲剧命运,已经达到了圆熟的艺术境界。
契诃夫的戏剧作品同样对中国现代戏剧的演变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他的五部多幕剧,还有五部独幕剧都在五四时期翻译成中文,但远未像易卜生那样引起轰动。曹禺曾说,“这些年在光怪陆离的社会里流荡着,亲眼目睹了许多梦魇一般可怖的人和事,这些印象我至死也不会忘却,它们化成多少严重的问题,死命地突击着我”,因而,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和神秘的古希腊悲剧最先引起他的共鸣,启发了他的灵感。后来他才对契诃夫“着了迷,沉醉于契诃夫深邃艰深的艺术里”。他说,契诃夫的剧“结构很平淡,剧情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生展,却那样抓牢了我的魂魄,我几乎停住了气息,一直昏迷在那悲哀的氛围里”。对契诃夫的迷醉,竟使他“渐渐生出一种对于《雷雨》的厌倦”,他坦承:“我很讨厌它的结构,我觉出有些‘太像戏’了。技巧上我用得过分。”契诃夫“简单的深刻性”、寓深邃于平淡之中的戏剧艺术,使曹禺意识到从前拾得的一点点技巧和招数的“浅薄”与“简陋”。因而,他痛下决心:“我想再拜一个伟大的老师,低首下气地做个低劣的学徒。”曹禺的《日出》和《北京人》就是他向契诃夫学习,“试探一次新路”的产物。虽然曹禺本人觉得《日出》还不太有契诃夫的影响,但实际上《日出》通过对围绕着交际花陈白露的银行经理潘月亭、秘书李石清、富孀顾八奶奶、面首胡四等一群魑魅魍魉形象的塑造,表现了寄居大都市的一个腐烂的阶层的崩溃。这与契诃夫的《樱桃园》所描写的樱桃园的旧主人,一群腐旧迷恋者已没落得非崩溃不可了的主题是很相近的。特别是戏剧结尾,同样作为樱桃园寄生物的老仆人费尔斯,在砍伐樱桃园的斧声中一睡不再醒来,与陈白露在砸夯的歌声中喃喃自语着“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北京人》与《三姊妹》的亲缘关系已多有论述,它代表了曹禺从易卜生型转到契诃夫型而达到的艺术高峰。夏衍也从30年代中后期实现了创作的根本转变,已有论文专门论述了他与契诃夫的艺术联系,认为“夏衍创作的整体风貌,是最接近契诃夫的”。
不必过多列举,上述这些代表着中国现代小说和戏剧高峰的标志性作家和作品足以说明,契诃夫在引领中国现代文学走向成熟与深沉方面起到了多么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契诃夫在中国的传播,就如他的人与文的风格一样,缺乏轰动效应,但如郭沫若所说,他“在中国,虽然一向不十分为人所注意,他对于中国新文艺所给予的影响确是特别的大”。
弹指一挥间百年即逝,“中俄文字之交”从幼苗萌蘖到根深叶茂。目前的发展势头使我们有理由继续相信,在百年积淀的基础上,“中俄文字之交”将变得更加理性,并将获得更丰厚的成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