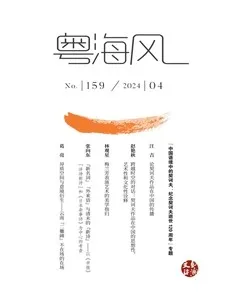中国文艺现代性的符号化表达
摘要:中国文艺现代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性偏向概念被提出,旨在超越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固守的西方中心话语,由以“新”的精神所指为重点向强调“中国式”转型,将现代性的时间内质空间化,重构其诞生语境之多重可能的同时,探索中国文艺现代性、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文学作为时代精神的载体将这一转型符号化,使宏观的抽象概念具体为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现代映射与共同体美学的现代建构,以黄河意象为中心能够更加清晰地再现问题本身。
关键词:中国文艺现代性 当代文学 黄河意象
西方现代性幽灵在中国土地的游荡不可谓不深远,当下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了质的飞跃,但现代性之路仍需不断发展完善,面对“后时代”的到来、国际形势的复杂化,如何追求“现代性”、追求何种“现代性”成为关键,因此,“现代性内生”、“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道路”作为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关键向度被提出并系谱化。与此同时,文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作为时代价值与社会思想发展的风向标显示出与西方文艺的较大差异,成为言说中国现代性的典型场域,以复归传统的人文主义本土立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表达,建构共同体美学多元一体的价值中心。本文以当代文学中的黄河意象为中心对此进行论述。
一、审美意识形态的意象书写
“现代性”自我与他者话语中心的争论由来已久,美国学者德里克指出启蒙现代性与非西方国家话语系统的不兼容:“启蒙运动既成为使人们从过去解放出来的工具又是对民族的主体性和智慧的否定”[1],由此显示出现代性的诸多矛盾。基于此,中国学者结合创作实际不断深入论述,如张颐武等的《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用“中华性”取代“现代性”,认为现代性作为舶来品在中国现代变革过程中被他者化,“中华性”成为价值中心旨在继承古典性和现代性的同时对其进行超越,以适应90年代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挑战。[2] 王一川在《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更进一步反思整合“中华性”与“现代性”概念;张法最终总结出“中国现代性”的命题,认为“中国现代性就是中国从分散世界史中的古代中国走向统一世界史的特性”,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对现代性的“积极认同”以及“壮士断腕的决心”,并且“总是念念不忘汉唐帝国和康乾盛世曾经有过的大国辉煌”[3],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实用理性精神与自我否定的思辨观念密切相关。王富仁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对比西方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历史底蕴、时代语境、表现形态等方面的不同差异,以此透视现代性话语在中国的特殊内涵。上述看似不同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同一性的本质关联,那就是中西方现代性差异的根源在于前者多元一体的传统思维与后者单向度思维间的对照,因此中国复归传统与西方抛弃过往,中国含混时间、空间与西方对二者的分隔,中国共同体的大同观念与西方民族本位的文化无意识等,均为思维对立这一根本差异的表征。
(一)黄河意象作为现代性符号化表达的可能
欧美中心的现代性话语随着人类文明发展显示出难以调和的自我矛盾,自由至上的人性话语被资本现实侵吞,马克思主义对此提出尖锐的质疑和批判:“通过那些承受了这些工具的残忍所造成的全部伤痕的人们,历史将被转变。在有力量的人疯狂横行的情况下,只有那些没有力量的人才能给我们展开人性的现象,而人性注定要获得力量”[4]。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艺现代性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美育与“诗言志”的抒情传统有相通之处。诗性意象及其内蕴的情感结构、文化-心理积淀维系着民族-国家认同与集体记忆,成为审美意识形态实现重要场域,意象化书写的复归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学标识。罗兰·埃利斯认为,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其实是水超越河流束缚的一种方式”[5],水对人的重要程度不限于“生命源泉”的物质供给层面,还在于二者间根本同质的存在特质,这一理念的存在照进现实,表现为人与河流的双向互动。河流为人类生存提供自然物质的同时,使之具有建构社会结构、区域划分、文化差异等的重要前提,因此世界古老文明无一不是河流的馈赠,中华文明正是以河流为中心、以黄土、黄河、黄种人为分支。河流具有的流动与滞重、开放与闭塞的二重性特征,与中华文化的圆形内向性循环模式相统一。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意义之重大表现在生命供给、文化起源与国家-民族本位等维度,经历史积淀与地域交流产生典型的隐喻作用和象征内涵,因此成为“想象的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源远流长的重要意象。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凝聚和共现赋予黄河意象自律性特征,使之成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集体无意识的本土化症候,并与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相同一,呈现出由旧符码向新符号转变的多重意蕴。因此传统经验与现代资源共同作用于黄河意象的成像中,非理性叙事和神性信仰与现代哲理和情感结构交往碰撞,使黄河意象成为反思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现代性的内生与外发等问题的场域。
中国文明景观的整体追忆弥散其中,使黄河意象与中国画上等号,如果以中国文学史为参照纵观黄河意象的演变,传统与现代的对冲被黄河意象整体性发展的混沌美缓和,表现为自然意象向文化意象和精神意象等类型开放的空间拓展、主体间性的话语杂糅以及反现代的现代性等内在特征。若要在浑融的流变中界定出时间以便对现代性演变做更加明晰的梳理,可将20世纪30年代视为黄河意象现代转型的起点,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拉开这一转型帷幕。在此之前黄河在文学中的形象多被定性为寄寓个体之情思的中国大观或标举地理方位的自然背景,30年代动荡外力的介入赋予文艺特殊的现实功用,“诗言志”的抒情传统被置换为更具意识形态内涵和情感偏向性的时代呐喊,黄河由此具有主体间性并与现实双向驱动成为国族经验的表征。黄河意象也成为战争语境中本土意志的表征,并以反抗和集体力量为中心塑造全新的民族形式,其中充斥着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悖论,一方面,民族形式是依托乡土或者说本土面貌而生,为强化本土意志、维护乡土家园与生活方式不受侵袭而发出的典型的反现代诉求;另一方面,这种反现代诉求的实现又以现代政治品质为依托,即反抗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强权侵略、保护大众不受摧残的革命理念。作为中国古典文明以及中华民族本体的符码,黄河意象在自身历史沿革中内生出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内生模式贯通延安时期的文学书写并在当代文学中持存,显示出中国文艺现代性发展的潜在路径,即用本土意志迎接环境之变化,用以生生不息的人民为本位建构革命英雄主义的民族历史,并以多元共生的世界性眼光询唤共同体美学的降生。
(二)现代性民族寓言初生
中国现代性的产生离不开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而现代化是由西方以暴力手段推介至中国,与中国“中心化情结”磨合后在此扎根,因此中国现代性具有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为动力的内生形态——革命,并且“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颠覆和改造了中国古代模式,然而,它又把古代天下为公的理想,嫁接在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翻身的基础之上。”[6] 黄河意象的革命精神初步形成于延安时期,因受到共产党的重视并在其有意塑造下变得丰富完整,成为再现民族革命、阶级革命的重要符码。首先,黄河具有区隔政党、阶级的地理意义,这是其革命精神生发的重要前提,“黄河和壶口瀑布是当时人们进入延安时需要经过的地方”,抗战时期许多革命青年进入革命圣地最先接受的是黄河的洗礼。“光未然参加的抗敌演剧队第三队正式从壶口附近渡过黄河,进入晋西南吕梁山抗日游击根据地,随后才到达延安。因此,《黄河大合唱》开头那句‘朋友!你到过黄河吗’就几乎可等同于‘朋友!你到过延安吗’,‘黄河’也就于地处其附近的共产党联系在了一起。”[7] 延安时期大量文艺工作者怀着革命热情进入延安,黄河也因此被纳入文艺创作的视野并形成革命精神的话语范式,如萧红的《黄河》、端木蕻良的《风陵渡》等,为当代文学黄河意象的书写构建精神预设。黄河“害河”与“母亲河”杂糅的背反形象对革命者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奠基式的冲击,前者隐喻的叛逆精神和伤痛经验,以及后者作为民族本位与国家象征显现出的正统力量,使之成为价值输出的精神符码来QfGfnro04OOXGYL3yf6Cog==获取民族主义话语竞争力。革命精神由此成为黄河意象现代性内生的关键指涉。黄河意象革命精神的显现首先具有现实性叙事肌理和情感基调,作为自然景观的黄河正是在历史真实中被赋予情感向度和精神指征,李準的《黄河东流去》正是在花园口决堤事件的史实背景下,从阶级性、民族性介入借人与河的双重隐喻诠释革命精神。人与河互为交互使“黄河儿女”成为黄河意象的潜在维度并赋予其人民性内涵,小说讲述黄河儿女的代际更迭、命运转变及其与家园空间的关系变化,从人民性角度对现代化展演进行具象投射,不同人物性格与命运的转折正是传统与现代更迭之时代变幻的缩影。乡土作为中华文化之根本与黄河意象并举成为现代性衍生的现实基础,政治因素和军事战略的介入改变了黄河意象的本土化所指,黄河决堤事件本身正是现代政治理念渗入传统话语并使之产生现代性变革的隐喻。《黄河东流去》中黄河既迫使黄河儿女离开故土,又引导他们寻找新家园,赋予“出走”这一现代性范式传统(“归来”)的价值中心,与中国圆形循环的历史逻辑相呼应。黄河作为乡土根系与家园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凝练着传统与历史,另一方面也是现代性言说的起点,二者间的纠葛与背反成为黄河意象反现代之现代性表达的证明。
与此同时,李準借黄河意象的流与滞揭示出阶级性的对立与杂糅,衍生出更为内在的民族性精神气质。革命源于阶级对立带来的难以调和之矛盾,当劳动人民被剥夺主体性及个体差异存在的资格成为底层群像时,伦理秩序与道德观念的分野随之明显进而产生现代性革命精神。小说中地主官僚和反动统治者呈现出与黄河儿女截然不同的面貌,暗示国民党反动统治与共产党的阶级对立与本质差异,诸海元对王跑毛驴被骗装聋作哑的可憎面目;海南亭欺诈难民为日本人卖命的伪善阴险;刘稻村为“熹平石经”构陷王跑坐牢的冷酷狠毒……阶级对立的精神意涵诞生出现代性动力,即对道德伦理与宗法秩序的彻底背反。只有为共产党所包容和发动的“黄河儿女”才能代表传统美德与现代气质,劳动人民显示出的高尚情操成为阶级性在道德秩序中的生动展示,并且更进一步显示出民族性的精神风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吞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主义破坏中华民族传统乡土秩序与生活方式的同时,促使中国广大群众进入现代性话语系统并以集体主义精神迅速整合出民族性的革命精神。《黄河东流去》中七户难民在逃难路上始终亲如一家,每个人都吃苦耐劳并且心甘情愿地将个体之所得融入集体的利益中,在危难中以反抗的现代性为导向自发形成具有民族性烙印、独立于统治集团外的共同体,以自发行动维护尊亲重孝、仁爱忠义等传统民族道义,在此过程中他们始终将黄河作为自身反抗意志与行为的精神导向,黄河意象以人民性为贯通成为内蕴阶级性与民族性革命精神的镜像反映。
二、精神图腾的现代映射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8],黄河意象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现代性的独特场域,与其自身蕴含的反现代与现代两种精神话语不无关系,由此透视出中国历史发展、民族文化变迁的内在逻辑与独特景观,进而在现代性的悖论中显示出内生本质。黄河意象从民族“去殖民性”立场出发将现代性悖论凝聚为映照现代的精神图腾,既是时代个体在追寻中实现救赎的精神此在,也是回归传统对抗西方现代性狂欢的精神复魅,从精神维度表现中国文艺现代性的核心要义。
(一)反叛精神:现代性的精神救赎
黄河意象熔铸革命精神的同时,现代性的反叛逻辑已在其内里播撒,当人民性指引下的阶级性、民族性无法满足个体存在的本质需要时,革命何为的根本问题成为个体存在询唤的对象,主体意义阙如带来的迷茫情绪成为“继续革命”理论的牵引。在这种背景下,黄河意象被赋予个体性的情感偏向,在虚实混杂的传统秩序中与存在主义的现代性哲理碰撞,产生出蕴含个体性、精神性与救赎意图的反叛精神。张承志《北方的河》历史阐释、精神图式的惯性滞后和人物当下具体实存之间的撕裂,使当代个体产生出存在主义式的精神危机,黄河作为精神之父为个体精神漫游与自我重塑提供了跨越时空和历史的精神场域。主人公的大河之旅不仅是他个体理想的反思与重审,也是对时代复杂性的追问和对民族价值的重构,他重返西部考察黄河的意图具有科学理性探索与人文精神回溯的双重内蕴,喻示着80年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这两大看似相悖的主潮的内在关联。两种话语范式双向并行赋予黄河意象丰富的现代性内涵,使之在精神层面引动实现个体的自我救赎、民族-国家话语在不同时代的交接,以及个体与民族整体的合流。小说从个人经验与即时性视角出发塑造黄河,黄河意象因此具有个性化隐秘特征与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较革命精神重视人民性的集体主义所不同。“山谷里蒸腾着朦胧的气流,他看见眼前充斥着,旋转着,跳跃着,怒吼着又清唱着一团团通红的浓彩。这是在呼唤我呢,瞧这些一圈圈旋转的颜色。这是我的黄河父亲在呼唤我。”[9] 黄河经个性化凝视后具有个体审美意向化转向,在小说中呈现出与视觉艺术——如梵高个性鲜明的油画创作——的相同之处,并在个性化审美观照与精神作用下赋予其精神之父的价值内涵。文中主人公多次渡黄河,将人与河的关联上升到知觉隐喻层面,黄河意象成为阳刚力量与坚硬生命意志的表征,人河合一使前者获得力量表征与生命存在之力证的同时,更在精神层面显示出个体存在的巨大能量空间。黄河意象成为引导个体在时代转型洪流中坚定自身理想信念、强化个人英雄主义立场,并由此获得精神根本力量的源泉。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的综合反映”[10],黄河意象也成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产物,因此黄河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意象共同建构起文学中的黄河世界,是为黄河意象的完整呈现。船作为黄河意象群的典型物象在文学中构造的“异托邦”同为反叛精神的显现,在个人遭际与时代命运的背反中使前者得以被救赎。福柯在《另类空间》中提出“异托邦”这一空间概念并且强调:“船是空间的漂浮的一块,一个没有地点的地点,它自给自足,自我关闭”“船既是经济发展的最伟大的工具,又是想象力的最大的仓库。在没有船的文明社会中,梦想枯竭了……”[11] 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可以构成异托邦,因此船作为异托邦同时出现在关于黄河的文学绘图中,以魏世祥长篇小说《水上吉卜赛》为例。黄河上的雁庄作为船上空间的代表被建构为偏离的异托邦,因为建构起这一空间的“水上游民都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扔了家扔了业逃出来的。船队五十上下的人,每一个都背过沉重的罪名: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国民党特务……”[12] 不仅雁庄人如此,被他们收留在船上的人也是所谓“行为异常的个体”,如疯媳妇阿花;“被斗得半死不活,断了一条胳膊”后逃出来的县委书记;以及因父母是地主成分,兄弟被害、新婚妻子受辱自尽,于是奋起反抗的杀人犯等。他们的“异常”正是特殊时代对主流话语和社会成规的偏离,表现为对生命自由的追求以及与权力意志的相互抛弃。二者的激烈冲突带给偏离者的创伤被空间化,河岸上的空间在雁庄人心中等同于权谋与阴恶,只有雁庄才是时代洪流中的诺亚方舟。异托邦遵从同时代文化共时性特征的同时以不同形式发挥历时性作用,因此不论是空间形态还是生命内质都显示出明显差异。雁庄以及雁庄人的异质性精神同样是黄河意象的精神表达,在小说中以河岸为参照对此进行反观,石令宇的闯入和对雁庄的凝视显示出异托邦对主流价值难以弥合的反叛。“罗家父子刚硬的种气使石令宇惊异感动,也使他折服。一种久远的、厚重的、象黄河一样滚滚不息的东西在他心里轰轰然涌动。”[13] 异托邦及其原始生命力背反于时代话语,展现出黄河意象的另一精神维度,即依照个体差异反思时代环境,强调个体心理性持存之潜能并且充斥着强烈的救赎意图。
(二)超越精神:回溯传统的表象之外
杨春时指出:“现代性与文学的现代性的二律背反,源于文学的超越本质。文学作为审美活动,具有超越现实的自由性,因而现代文学对现代性和社会现代化持批判立场,体现了人类对现代化过程中人性异化的抗争。”[14] 超越精神作为具有非理性意义并以神圣价值、永恒生命与存在本质为内质的现代性追求,是中国文艺现代性创作的重要意向。黄河作为“四渎之一”自汉代以来被赋予祭祀价值和神圣意义,因此黄河意象在文学书写中的神性意义不只局限于非理性层面,而且内蕴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自然、历史与神性三足鼎立于黄河意象成为中国文艺打破西方中心话语实现自身现代性的重要路径。现代化进程日益加速的当下,后现代主义审美日常化渐成大势,神性与自然性在理性与城市化侵袭下逐渐失落,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15],其创作“并不飞越和超出大地,以便离弃大地、悬浮于大地之上。毋宁说,作诗首先把人带向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16] 因此,黄河意象在诗歌中将存在的寓言向人敞开,使后者在世界的本质存在中建构作为此在的根本性与神圣性。
古马长诗《大河源》将目光回溯至黄河源头,地理环境与文学书写的交互使黄河意象集自然风情、历史厚度与神圣信仰于一身,一切生灵都被意象化为纯净澄澈的黄河源头自然景观的符号,不论是自然景物、野兽飞禽,还是女人或喇嘛,“都是水的骨肉水的梦想/都是大河有声有色的韵母”[17]。黄河意象超越表象升华为一切存在的本源,创造生命的同时内蕴非理性的神圣信仰与传统宗教文化色彩,“是活佛座前最高的侍者黄河在玛曲拐了个大弯/把牛群和乌云赶过甘川边界的人”。藏传佛教的文化典故极大地丰富了黄河意象的神性特质,并且与以线性时空观为典型的现代化思维方式相对抗,借神圣信仰强调以因果论、轮回观为中心的传统圆形时空观与思维方式。黄河因此将历史与现代循环成时空的环:“黄河的身影无处不在/穿越时空,打破常规/公元前641年/一支送亲的队伍翻过赤岭/霓旌向西,逶迤前行/一支送亲的队伍是黄河大智大爱的支流”,黄河以历史见证者身份存在的同时也是历史的一分子,时代流淌的同时更迭并且丰腴着自身存在的价值。黄河意象在变与不变之间回溯传统,成为以神性质素打破时空界限并将此在敞开在历史存在面前的生命本源,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其中国式反现代的现代性新论调。西方后现代在狂欢与解构中粉碎现代性一切价值,在单向度线性逻辑中重新拓展边界以求新生,中国式反现代的现代性恰好与此相反,往往呈现出往复传统、渴望赋魅的圆形思维惯习,古马《大河源》的文化意义与哲学精神正在于此。
三、共同体美学的多元探索
中国文艺现代性的实现离不开对个体与人类、民族与世界交互关系的阐释与重构,复归传统并在文明差异性中共生,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即为共同体美学的多元探索,就黄河意象而言表现在叙事与情感两个维度。
(一)叙事共同体:跨地域与跨学科的中国故事
黄河横贯东西、流经九省,其流域之广阔将中国自西向东不同的地域文化容纳于一身,不仅作为打破地域界限、呈现不同地区文化景观的意象出现在文学中,而且具有中国古典文明整体象征之功用,在跨文化视阈下实现对共同体样貌的阐释。杜·拉尔梅、王瑶的《黄河那道弯》以黄河为地域、族群、文化的天然区隔划分出边地与中原、蒙古族部落与汉族世家、草原文化与三晋文化间的巨大差异,与此同时也正是黄河的流动性与开放性催生出跨地域的文化交融。鲁枢元在《略论黄河史研究》提出:“文化就是‘人化’,就是人对自然的同化,就是人对自然的理性化、情感化、心灵化。一种文化体系总是伴随着一个民族对自然力量的认同与控制成长起来的……黄河,既是一条大地上的河流,又是一串流逝的岁月,同时具备了地理的空间性与历史的时序性。”[18] 因此,黄河意象在小说中发挥其作为文化共同体之效用时常以人物为媒介,小说参照母亲河原型赋予女性形象文化内蕴,王老槐的三个老婆正是三晋文化与游牧文化碰撞的征候。春娥作为传统山西小脚女人是传统农耕文化熏染下成长起来的文化符号,她的生命悲剧寓示着传统农耕文化面对商业文化的开放与游牧文化的交互难以维系自我固守的排他话语,需打破自我与他者间的障壁,在合作开放的语境中重构自我。杨槐花则是这一文化立场的能指符号,蒙汉文化的交融使她有着更强大的生命气魄,作为后继者却与王老槐情投意合,寓示着多民族文化交融释放出强大的生命潜能。乌云珊丹始终是游牧文化记忆坚定的承载者,象征着游牧文化在与农耕文化的交融场域中坚定的身份认同与自主性,诠释了文化共同体发展之根本在于文化跨地域实现渗透交融的同时,还需坚定其自身的本体地位与独立立场。人物的时空流转与命运进程熔铸着黄河意象的文化记忆,立足本土文化自身特色的同时,将其纳入现代性的共同体视域下予以新的发展路径。黄河不仅由流经区域之广带来文化层面的超越,漫长的黄河史赋予黄河意象从历时性角度阐释文化共同体的能力,因此黄河意象以其深厚的传统背景与历史积淀出现在当代文学作品中,使现代性笔法和论调自觉地生发出史诗气度。
黄河意象在文学中还表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征,即以科学求真的态度进行文学的非虚构写作,从生态环境、水利建设、生物多样性等维度述说现代黄河,文学性叙事交融科学性严谨态度、感性人文意志伴随自然地理知识、非虚构态度兼容充沛情感,从传统美学、实用理性与现代性功用极大地丰富了黄河意象的象外之意与现代性功效。哲夫的报告文学如《黄河生态报告》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调研黄河流域,并且真实叙述大胆揭橥黄河“丑”的一面:黄河之源玛多县濒临破碎的生态环境、过度放牧导致草原退化、鼠害泛滥、野生动物被偷猎等,大量引用自然科学知识与数据以及与黄河治理相关的时事政策,在文学文本中实现跨学科式的互渗交融。除科学性的求真态度与论证思维外,哲夫并未忽视文学性的写作,他善用诗意语言甚至用诗歌直抒胸臆表达自己对于黄河及其生态问题的看法,“笔者击节奋声而歌之:魂兮归来,匠巧难夺天工兮,食时俗恐难硕;既有绳墨以追曲兮,胡不改错?人道泯而天理灭,慈航有舵;海晏河清以养生兮,举世成佛;时不归兮永不归,孑遗难活。西有沙怪兮东有污鬼,生境危殆兮不归而何为!”[19] 融楚辞之风韵与实用理性精神与现代呼号中,纵深文本表达空间的同时显示出深刻的生态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情感共同体:物我相谐的生态伦理
中国文艺现代性的共同体美学建构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与情感结构的回应,黄河意象作为人化自然在文学中的展现,凝聚传统美学精神、情感向度于现代存在中,从以物观物的传统视角出发建构物我相谐的混沌情感追求,进而投射为自然和谐的生态观念。“混沌”在中国传统文脉与生存哲学中由来已久,可追溯至《山海经》等神话传说,经庄子阐释与发扬演化为具有哲学之思的意象群,衍生出自然层面天人合一的生存哲理与逻辑秩序,并且沿用至今。与此同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地》)的混沌哲学不仅强调自然层面的生存并置,还将其升华至精神层面的物我相谐,黄河意象凭借自身跨时空的潜在话语空间,以精神之父的原型意象统合个体的精神生命,成为传统生存观、美学观在现代语境下的重构,人与自然、历史与现代的镜像自我投射为黄河意象的情感共同体。
张贤亮《河的子孙》中极尽对黄河的景物描写,在情、景、事的交融中展开叙述,晨曦下的黄河如天地般宏伟,超越自然景观的物质存在引起魏天贵灵魂的战栗,是为与其人生声气相通的重要意象。荣格指出:“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一点残余”[20],黄河正是原始意象的典型,其历时性内涵使之成为观照个体历史、映射大历史的集体无意识场域。小说中魏天贵、尤小舟等人“看着河,迎着风,听着种种惊心动魄的音响,闻着泥水的浓郁的芬芳,人会感到这一切的一切不是来自身外的感受,而是从自己心底里生出来的幻境,一种在自己还没有诞生,还在母体里就赋予的原始印象。”[21] 黄河跨越时间的障壁成为凝聚集体无意识的当代性意象,赋予个体超越传统与现代、物质与意识、自我与他者的生命能力,与存在本质一同建构起现代性的情感共同体。魏天贵的人生历程、情感变化始终与黄河的情态相呼应,当他被迫接受“双打”任务、郝老三主动去坐牢时,“黄河冻结了”,黄河颂歌“失去了雄伟壮烈的神韵,变得如丝如缕、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当三中全会的召开带来时代的面貌时,黄河景观也呈现出新的希望:“在河对岸,出现了一片深红色的朝霞。”黄河作为人化的自然实现与人对时代情感回应的共振,蕴含着传统混沌哲学在现代视野下重现的深层逻辑。
工业主义作为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同时也是现代性进程的催化剂,“技术进步影响着我们作为人类的物质构造,同样也影响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22],尽管中国式现代性的实现同样离不开技术先导的发展模式,但其人化自然在形成过程中受传统混沌观念的影响,因此重视道德伦理的引入以及由此而来的主客体的精神同构与情感互通。正如加塔利在《混沌互渗:一种伦理美学范式》中指出:“我们怎样改变精神价值体系?我们怎样重建社会实践,使之回归人性中固有的责任意识——不仅对人类自身的生存负责,也同样为星球上其他生命的未来负责;不仅对动、植物物种负责,也同样为诸如音乐、艺术、电影、与实践的关系、对他者的爱与怜悯、融合于宇宙中心的感觉等精神物种负责?”[23] 黄河意象被赋予主体间性由此成为建构情感共同体的重要维度,耿占坤的长诗《黄河传》以黄河为精神生态的中心话语从人与河的情感共建中为其立传,反日常性的史诗歌书与现实主义基调交互将生态伦理融于人化自然的现代性书写中。原型意象黄河母亲被人化为当代性的人像符号,以女性不同的成长阶段同化黄河历时性、共时性的样态特征,宏大的史性空间与叙事视野兼容诗性浪漫与笔调,在以物观物的无我之境中呈现出具有先锋意味的含混气质,使中国文艺现代性的混沌美学在主客位移的情感共同体建构中具像化。三好将夫认为共同体是人们面对后现代的秩序混乱“创造出的一种怀旧的和伤感的神话”,是“一种人人皆为平等一员的没有阶级的有机共同体的感觉”[24]。美学共同体之于西方即人们在现代性发生后现代转向的消费时代为寻找归属感创制的审美幻象,在娱乐至上的消费意识形态中解构现实道德与刻板的社会秩序,然而正是对本体性安全的渴望和幻想使“标准”和“主义”在共同体语境中被模糊化,造成信任的消失以及更加混乱的孤独感。正如鲍曼所说共同体的诞生“只可能是(而且必须是)一个用相互的、共同的平等权利以及对根据这一权利行动的平等能力的关注与责任编织起来的”[25]。与此相对,当共同体作为现代性发展路径在中国上演时,厚重的历史文化惯习以及人民本位的政治观念使之呈现出明显的适应性和中国式风格,黄河意象的当代书写正是在美学共同体的价值引导下得以实现。
结 语
黄河作为中华文明漫长历史的见证内聚广阔的物质世界与精神内涵,因此显示出复杂的话语空间、情感结构由此成为中国文艺表达的重要意象。黄河意象包蕴着传统与现代、个体感知与民族情结、自我与他者等多重话语,成为中国文艺现代性符号化表达的范式,从精神图腾的现代观照、美学共同体的多元探索等方面具体展现出中国式现代性的含混特征,即以本土化思维与核心精神适应现代性的整体局势,形成多元并置的人类现代文明景观。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
注释:
[1] [美] 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载萧延中主编《在历史的天平上》,北京: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页。
[2] 张颐武、张法、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3年,第4期。
[3] 张法:《文艺与中国现代性》,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3页。
[4] [英] 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页。
[5] 转引自[美] 华莱士·J .尼科尔斯:《蓝色思维:与幸福感相关》推荐序,阳曦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6] 同[3],第30页。
[7] 罗雅琳:《上升的大地》,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第60页。
[8] [美]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26页。
[9] 张承志:《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第1期。
[10] 许玉庆:《远逝的村庄——新时期文学中的“村庄”意象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9年5月。
[11] [法] M.福柯:《另类空间》,《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
[12] 魏世祥:《水上吉普赛》,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13] 魏世祥:《水上吉普赛》,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页。
[14] 宋剑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15] [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小于一》,黄灿然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16] [德] 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08页。
[17] 古马:《大河源》,敦煌:敦煌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89页。
[18] 鲁枢元:《略论黄河史研究——关于黄河文化生态的思考》,《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19] 哲夫:《黄河追踪(下):魂兮归来》,北京:红旗出版社,第328页。
[20] [瑞士]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页。
[21] 张贤亮:《绿化树:中篇小说卷》,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7页。
[22]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修订版》,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第188页。
[23] 转引自张惠青:《混沌互渗:走向主体性生产的生态美学——论加塔利伦理美学范式下的生态智慧思想》,《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
[24] 三好将夫:《没有边界的世界》,引自汪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84页。
[25] 转引自李立:《审美社群体验的在世想象——后现代社会的‘美学共同体”批判》,《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