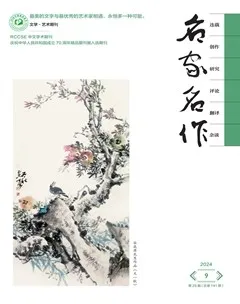精神乌托邦的一路“北上”
从花街进入北京,从北京走向世界,徐则臣以“北京书写”为圆心展开了他的文学志业,但其小说并不限于对“京漂”族生存的探讨。徐则臣的写作尝试以北京作为叙事的动力,“北京”成为“花街”出发的终点,也是“到世界去”的起点。在徐则臣的作品中,读者除了能够捕捉到“无法对自己的处境做出清晰的判断”的人物,还能触及他努力建构“一代人的心灵史”的文学愿景。
一、原乡“花街”与他乡“北京”
(一)先说“花街”
在作家的叙述中,“‘故乡’实际上是一个在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中产生的概念”①。当一个作家频繁地写到某一个地方,并对这个地方流露出特别的眷恋、怀想时,那个地方时常被视为作家“文学的故乡”。对徐则臣而言,水边的“花街”便是其文学的故乡,也是他“精神栖息之地”②。文学的故乡并非作家户籍的故乡,而是负责容纳作家对世界的见闻、感知、体悟和理想的缘起,也是唤起往日记忆的地方,是某一段独特生命体验短暂停留的空间位置。徐则臣把“花街”置于水边,不仅有作家的生活经验,还有作家为封闭的、固定的“花街”提供一种出发的途径。流动的运河展开了“花街的生活就像陷在一张陈旧的照片里,晃晃悠悠的,想忙都忙不起来”③。作为徐则臣文学故乡的“花街”是传奇的、日常的,也是一种从过去到现在以至未来的情愫,更是一个开放的、融入了想象的地理空间。
文学的故乡是作家建构世界的方法,也是作家对故乡记忆的修复与重建。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毕飞宇的苏北水乡,都为作家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文学空间和意象符号。徐则臣以《花街》《大雷雨》《伞兵与卖油郎》《水边书》等作品,想象了一个封闭的、停滞的、自然的地方,把他熟知的素材和故事,以及根植于故乡的想象搬到花街上。徐则臣说:“我喜欢花街这个名字,很多年前读书时,曾去过那条老街做家教,印象和感觉都在,写起来心里有底。小说中的花街,就是根据那条街展开想象的。”这条读书时去做过家教的老街是徐则臣展开想象的起点。所以,“花街”在徐则臣的小说中既是寄寓情愫的故乡,又是通连世界的载体。自“花街”开始想象的世界,时间与空间跨度极大,如《北上》是从清朝讲起,《耶路撒冷》中初平阳的“梦想之城”在死海与地中海之间。
1959年,作家钟理和写下《原乡人》是对自己族群身份归属不确定的反思。“所谓原乡,无非是他安顿自己的终极向往:原乡可以是土地国家,是至亲挚爱,更可以是他一生的文学志业。”④对于徐则臣而言,“文学的花街”无疑是他高高悬置于现实主义叙事之上,作为一种浪漫主义精神归依的乌托邦。在《耶路撒冷》中,初平阳回到花街,不仅是为了卖掉祖宅筹集去耶路撒冷求学的费用,还是他精神还乡的方式。王德威在《原乡神话的追逐者》中提道:“‘故乡’因此不仅只是地理上的位置,它更代表了作家所向往的生活意义的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⑤关于故乡的乡土叙事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重要的叙事模式。进入21世纪,在现代性、全球化的杂糅中,故乡的文学表达也不仅仅意味着是乡村,而很大可能是城市。在世界视野中思辨,甚至故乡就是中国本身。徐则臣在文学书写中赋予“花街”的意义是一种惯常不变的生活空间,与之相对的“北京”想象则是一种对抗稳定空间的地方性空间。
徐则臣借书写“花街”与“北京”之间的对峙,展现了对故乡静谧、稳定、停滞生活的抵抗与不满。鲁迅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徐则臣对“花街”形象的叙事恰是田园牧歌式的想象,他用具体的“花街人”形象表达出不同人对故乡的态度。徐则臣深入小说的细部,探讨人对现实生活不满的抗争与对精神满足的不断追求。一群人有对“花街”的依赖,表现在潜意识层面的熟悉和依恋。在《啊,北京》中,边红旗与北京姑娘沈丹缱绻温存,但边红旗绝不与边嫂离婚,他们之间的情感纠葛也构成了故乡与他乡之间的博弈。个人成长与社会相融合,徐则臣与“边红旗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关于时间、社会的流变,他们都渴望参与其中。还有一群人与初平阳一样,离开故乡是一种哲学,回归故乡也是一种态度。在《耶路撒冷》中,历经万难考上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的初平阳,却失去了深爱他的女友舒袖。舒袖对花街的留恋与初平阳对“耶路撒冷”的执着显然是错位的,二人的感情也必将终结。“花街”与“北京”也是小说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撑。因此,一种新的生命体验冲到了徐则臣的笔尖,“花街”烟火生活的纵深处在“北京”叙事中延展开来。
(二)再谈“北京”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说,“他乡”是一面负向的镜子,漂泊的人在“他乡”能够指认出自己的渺小与世界的庞大,庞大的也是永远不配拥有的实在。生活在花街中的年轻人,时常渴望到“北京”去,“北京”对于他们而言,是精神理想的至高地,也是他们对安逸、不变生活秩序的反抗。徐则臣笔下的花街青年,如行健、米萝、木鱼、宝来等人是一群行动力极强且略显鲁莽的人物。他们不断从花街出走,到“北京”去,到“耶路撒冷”去,甚至到“世界”去。对“北京”的想象,徐则臣并未如其他“进城叙事”的作家集中笔力在“城与乡”的二元对立方面,而是赋予“北京”以理想化、精神化象征的文学意蕴。
徐则臣关涉“北京”书写的作品多是中、短篇小说,“北京”与“花街”、“北京”与“耶路撒冷”、“北京”与“世界”成为意义与价值上的互文与参照。“北京”的魅力是混杂的,是由不同作家在不同时代给予不同意义诠释出来的。徐则臣赋予“北京”的文学意义则是梦想开始又破碎的“生死场”。自“花街”而来的这群人,在“北京”经历了与其他作家笔下人物相同的物化、异化的生存经验。不同的是,尽管这群人生活窘迫,但精神并未萎靡不振,他们对精神、理想的执拗与再次出发“到世界去”的勇气,使他们成为当代文学视野中出现的另一种生命形态和精神异质。他们陷于“返乡而不至,身寓而心未属”的两难中,“城市是一个梦,源自人的内心,是塑造与表达欲望与恐惧的地方”①。“北京”为“花街”年轻人提供了实现自我精神追求的场所,“北京”也冲撞着他们生存的原有秩序。“花街”年轻人在北京大多是从事制造假证、贩卖盗版光碟等“见不得光”的营生,他们酷爱文学、崇拜学历,暗合着他们对“北京”精神化的想象。在《啊,北京》中,初到北京的边红旗感叹:“世界一下子离我近了。到了北京我真觉得闯进了世界的大生活里头了。”
对北京的体认,一方面是他们安放精神追求的自由天堂,另一方面则是他们被迫居住、承载肉身的宿命场。在《王城如海》中,余松坡接受采访时说:“一个真实的北京,不管它如何繁荣富丽……还有一个更深广的、沉默地运行着的部分,那才是这个城市的基座,一个乡土的基座。”②显然,从“花街”出走至“北京”,又从“北京”到“美国”,而又返回至“北京”的余松坡对北京的指认,不免是一种精神“怀乡病”的体现。而余松坡的“怀乡病”是一种兼具现代性、全球化特质的“怀乡病”,也体现出徐则臣的文学叙述姿态,“情感立场和创作视角却始终是向下的而非向上的,是乡土的而非城市的”③。徐则臣的北京书写,不仅仅只是西郊一隅,在《耶路撒冷》《北上》中,尽管作家并没有直接以“北京”展开叙述,可北京的人文情感蕴藏其中。北京是“水上漂来的城市”。从元代大运河通航开始,这条连接北京与江南腹地的水上通道就承担着向都城输送南方物资的任务,而北京也利用这些顺河“漂”来的物资拔地而起。徐则臣在《北上》中讲述了京杭大运河边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北是地理之北,亦是文脉、精神之北。在《耶路撒冷》中,几位儿时伙伴从“花街”到“北京”,漫长的时空里缠绕交织着各种社会问题,而后又重新返回故乡,寻求再出发的意义。徐则臣在《北上》中探究普通国人与中国的关系、知识分子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用《耶路撒冷》道出了一代人的生qBJjNEjrVuXjxVlYfu3/Jw==命和精神历程,唤醒人们的反思精神。
徐则臣建构的“北京”在不同人物的叙事中,变奏、形塑、丰富了新世纪关于“北京”的文学想象。“北京”被塑造成与“花街”迥然相异的生活空间,徐则臣用历史性、地方性、全球性互融的方式把“北京”立体化,并以展现行走在时代巨变中的人物,浸润在全球化的潮水中,一面呼唤着他们离家出走,另一面召唤着他们去向更远的世界,在返乡与离乡“耦合”之间形成独特的文学意味。这种奇特的文学反应,必然发生在北京,也只有“文学中的北京”才能产生“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才能让作家有能力去处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境遇下人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文学北京”的经验是中国社会剧变的可能,也是具有寓言性“文学北京”的价值所在。
二、“花街”与“北京”之间的张力
“你无法把北京从一个乡土中国的版图中抠出来独立考察”①,抛开中国的乡土理解中国的城市是片面的。文学“花街”是徐则臣对故乡的想象,文学“北京”是徐则臣承载精神化追求的出发地。在“花街”与“北京”之间,徐则臣试图阐释的并非“城与乡”的二元对立,而是皆有一种原有生活秩序的破坏,探讨时代对一代人精神彷徨、困顿与归依的描述。
从2010年到2017年,徐则臣用了8年的时间,以中、短篇小说的形式形成《北京西郊故事集》。从形式到内容,徐则臣笔下的“北京的西郊”正在城市化、现代化的单行道上一路狂奔。海淀、北大、中关村、蔚秀园、承泽园排队进入小说;边红旗、沈丹、孟一明、舒袖、穆鱼、小唐等人物跃然于纸上。面对瞬息万变的时代,徐则臣用文学的方式探询和求证“北京”想象的新可能,对原来以类型化方式强调“底层人物”生存困境的突破,对人物在精神、文化方面诉求的展现,形成了人物与城市的相互塑造、影响。因为作家个体经验与叙事时代的不同,徐则臣的青年进城叙事不是“高加林式”的。徐则臣的文学姿态是由这群不断行走、奔跑的人物勾勒出来的,这群人物的命运起点是“花街”,但终点不仅仅是“北京”。
徐则臣的“京漂”人物在行走中不断地实现对自己生存价值的质询,这群人是逆境向上的生命力,也代表了某种隐秘却大胆的理想主义。对他们而言,“北京是放得下所有的怪念头”②的地方,“北京”也是这群人继续寻求精神意义的出发地。易长安放弃家乡相对稳定的工作,选择到北京成为伪证制造者,这与他在原单位不得志有关,更与他渴望出走有关,也与他性格里热爱冒险有关。舒袖义无反顾地追随男友进京,只为他人的梦,她的无意识跟随是“错位的梦”的象征与隐喻。当办假证的敦煌得知夏小容怀孕后,二人选择离开北京,回到故乡。离开的原因是生活困顿所迫,敦煌无法想象夏小容带着孩子在街上卖假证的场景。可北京已成为他们永久的记忆,尽管回到故乡,但他们的精神也许永远都将处在漂泊之中,故乡和北京都不再是他们的归宿。初平阳返回故乡,重遇昔日恋人舒袖的一番慨叹令人玩味:“我们都缺少对某种看不见的、空虚的、虚无之物的想象和坚持,所以我们都停下来了。我本可以再找你,但我也停下来了。每个人都有一堆借口……我们还缺少对现有生活的持守和深入;既不能很好地务虚,也不能很好地务实。”③他们面对的是必然的抗争,更多的是内心的焦虑与无望,以及对抗性格中的懦弱和自卑。
在徐则臣看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耶路撒冷”,徐则臣也敢于对心中的“耶路撒冷”发起挑战,他借人物实现“到世界去”的文学愿望,因为“世界意味着机会、财富,也意味着开阔和自由”④。一个城市与人的关系其实也就是一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此心不安处是吾乡,非吾乡者亦无乡。更可贵的是,“花街”叙事与“北京”叙事的共同逼近,也生发出作家关于“耶路撒冷”的文学想象与建构。
徐则臣的文学表达中,“北京”是远方,“耶路撒冷”是世界;远方是精神高度,世界则是情感深度。“‘世界’从一个名词变成了一个动词” ,故事在世界发生,人物在世界行走。用全球视野去理解历史和当下是徐则臣的文学笔法,所以在他创作中“世界”的概念不断被泛化,既意味着文明、进步、现代、秩序、繁荣、幸福和平安,又意味着拥挤、紧张、混乱、虚伪、空虚、浮华、欲望和贪婪。人物不断地在“世界”中奔走,为了追寻、为了信仰、为了救赎、为了意义、为了真相。徐则臣以进击姿态,为一代人进行自我清理,奔赴远方亦不忘回首来路,他的精神之旅一直“在路上”。
作者单位:吉林动画学院
作者简介:刘寅时(1986—),女,汉族,吉林长春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创意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