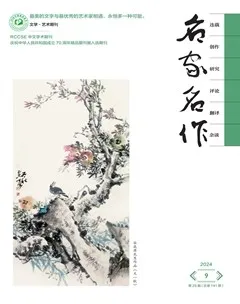雨果:用人道主义探寻“爱的艺术”
[摘 要] 维克多·雨果被誉为“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其人道主义已然成为雨果笔下的浪漫因子,他用“美丑对照”的诗学观念,来描摹人道主义的理想蓝图,最终追寻那“爱的艺术”,反思爱的方式和人爱的本质。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可以说是其人道主义践行失败的代表,而《悲惨世界》则成功践行,这两部作品中的爱都受到宗教的影响。从这一败一成的两部文学作品出发,通过分析作品中人物的各种爱,来反思宗教对“爱”的影响,探究人性之爱和人道之爱,并进一步探讨分析雨果所追寻的人道主义其实是“父性基督”之博爱。
[关 键 词] 人道主义;父性博爱;美丑对照
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在其生命尽头他这样总结自己的创作: “我在我的小说、剧本、散文和诗歌中向权贵和铁石心肠的人呼吁,替小人物和不幸的人鸣不平,恢复了小丑、听差、苦役犯和继母的做人权利。”这“做人权利”就是雨果人道主义理想的践行,而践行的方式正是用爱。何为“爱”?如何 “爱”?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说道:“爱,不是一种无需花费精力的享受, 爱是一门艺术,它需要知识和努力。”雨果用《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回答了这个问题,《巴黎圣母院》中通过“圣母院”将主要人物与“爱”联结,写出了爱斯梅拉达一见钟情的痴爱,伽西莫多感恩式的错爱,巴格特修女与克洛德偏激的私爱;《悲惨世界》用“冉阿让”将人物与“爱”挂钩,使这个悲惨世界沐浴到爱的温暖,比如冉阿让和珂赛特被给予的重生之爱。这两部作品中的爱是为了制“恶”,《巴黎圣母院》失败,人性之爱最终没能战胜以圣母院为代表的宗教力量,《悲惨世界》成功,人道之爱最终给他们带来了一扇“门”。本文从这两部作品出发,对人性之爱加以剖析,探讨雨果的“爱的艺术”,通过“美丑对照”来思考宗教对人爱的本能的影响和人爱的本质,同时跳出人爱的人爱来窥探雨果内心强大的期待:用伟大的人道之爱去改善虚情假意、真情沉灭的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雨果的人道主义其实就是“父性基督”之爱,同时思考要如何爱,才能避免“被异化”这一人类无法超越的困境。
一、爱的失衡:“圣母院”与人性之爱的对抗
美丑对照原则最早出现在雨果被认为是浪漫主义宣言书的《克伦威尔》序言中,他认为美丑在大自然中客观并存,文学作品中仅有“美”是单调枯燥的,崇高与崇高之间很难产生对照,而滑稽丑怪作为一种比较对象、一个出发点,却能使人产生新的感受而朝着美上升,产生阅读的震撼体验。本文不从人物与人物的对照出发来看该原则运用的效果,而是将其聚焦到一个人的内心思想深处,窥其人物自我本身在爱问题上存在的“美丑”。同时,雨果在《巴黎圣母院》序中写到,在圣母院墙上“有这样一个手刻的单词:‘ANA1KH’ ”,这些字母蕴含着 “悲惨的宿命的意味”[1]1,从这里就可预判到书中人物的悲惨命运。但是,正如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所言“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巴黎圣母院》悲惨的结局中,能看到“圣母院”所代表的宗教力量对人爱的撕扯毁灭以及各种爱的失衡,可以让我们反思那最有价值的东西的本质——人性之爱。
爱斯梅拉达是美、善、爱极致存在的集合体。她敢于追求梦寐以求的爱人弗比斯,能大胆把握机会,抓住爱情之绳。然而,占据她生命全部的男子——弗比斯,却是一个面俊心恶、追求肉欲和名利的不懂爱的世俗男子。“弗比斯”这个名字,本义是太阳神,象征着温暖和美好,但是这个男子用他的人格灌注给这个名字完全另样的生命代表,在爱斯梅拉达被捕之后,他回到了他的连队,根本不想亲自出庭,“发现在这段经历里巫术的成分倒比恋爱的成分多些,她或许是一个女巫,或许是一个魔鬼吧?那归根到底是一场滑稽戏,或者像当时的说法,一场很乏味的圣迹戏罢了,但他却在其中扮演了一个相当愚蠢的角色,一个被打击和被嘲笑的目标”, 甚至对此感到一种“拉封丹曾经描绘得绝妙的那种羞耻”[1]307,从这一点就能看出雨果对那“美好外衣”的怀疑,用名字解构了这类人的本质。他们的爱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文中总是用“孩子气”来形容爱斯梅拉达,更用其来定义她的爱情,她这样形容爱情:“那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合成一个天使。那是天堂。”[1]91这说明她是介于成人和儿童之间、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共存状态,这是她爱的弱点,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指出爱有成熟和非成熟的形式之分,非成熟的爱是病态之爱,只有成熟的爱才是真正的爱。另外,弗比斯从一开始爱的就是她的美丽皮囊。这种“一见钟情”式的爱情索取了爱斯梅拉达的生命,这就证明了此种爱的危险性,而弗比斯却不被要求付出相关责任,这又反映了社会对男女在道德规范上不平等的事实,可以说这种不平等击败了她的“孩子气”式的爱,从而造成一种失衡。
此外,为爱而付出生命的还有雨果“遗形取神”所塑造的伽西莫多,他因长相奇丑无比而只能依靠圣母院来生存,以敲钟获取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可以说伽西莫多表现出来的内心世界是阴暗的、漆黑的、沉闷的,当然这是长期缺爱的必然结果,所以爱斯梅拉达的一杯水就能使得伽西莫多流下生命史中的第一滴眼泪:“那一直干燥如焚的独眼里,滚出了一大颗眼泪,沿着那长时间被失望弄皱了的难看的脸颊慢慢流下来”[1]210,那阴沉的生命世界被那善的阳光猛然照亮,但是由于长期昏暗,这出乎意料的善之光会被伽西莫多自身过滤,变成了相当强烈的爱之光,但自己最终被这光反噬而失去生命,这类似犯罪心理学中所说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像极了《红楼梦》中被薛蟠所强夺但一心一意地跟从着薛蟠、忠爱着薛蟠的甄英莲(香菱),在这一点上看到了爱的失衡,警示我们给予爱的对象有时是要有必要的深思,否则会成为被爱者的桎梏。但我们在伽西莫多身上发现其实他的内心本质是光亮的、美好的、善良的,他将它封存是为了保护自己,和这个充斥着嘲笑、鄙夷、冷漠的世界对抗。
同样由于爱上爱斯梅拉达却无法冲破“圣母院”桎梏,而选择死亡来结束痛苦的内心撕扯的还有克洛德。克洛德的一生成也因“圣母院”,败也因“圣母院”。他爱她,但是他不懂得“爱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克洛德的爱是自私极端的。收养“怪物”伽西莫多,抚育亲生弟弟若望,然而伽西莫多从来没有从外表所带来的自卑心理走出,弟弟若望的人格也令人鄙弃,这种爱还不能达到真正意义的母爱,或许可以说是性别限制,但是我认为更多的是人格限制。克洛德的人格是不具有“属我性”的,而是一种迎合当时“圣母院”的需求,按人们的观念进行自我塑造,是为宗教活着,所以当他主动脱离世俗要求而追寻爱情时,他必然会造成人格失衡,从而异化他想得到的爱情。他披着一身代表圣神的宗教外衣,同时自己也被这一身外衣所辖制,其内心世界被其裹得透不过气,使得他呈现出一个外表光鲜但内心缺爱的自由之氧。另外,爱斯梅拉达的母亲巴格特不爱自己也不懂爱,在玩弄青春后堕落,在孩子被抢后受“圣母院”的影响而在老鼠洞中当修女,当其看到爱斯梅拉达即将被处以刑罚时是痛快的,而当她认出爱斯梅拉达是自己寻找多年的亲生孩子而不是自己认为的埃及女巫时却又极力保护爱斯梅拉达,这实质上是具有偏执的母爱与广阔的人爱之间的失衡,这种母爱具有强烈的排他性,靠着血缘来维系,而这还不是雨果所追寻的人道之爱。
二、爱的救赎:人道之爱与救赎意识的跃迁
弗洛姆针对爱的异化,以人道主义为基点提出了“爱”的救赎方案,即创发性,就是自己去创造,首要因素是给予,这类似于雨果的人道之爱。《悲惨世界》中,雨果将一种救赎之爱洒向这片悲惨的土地。用冉阿让的生命演泽人道之爱的救赎光泽,同时他的坎坷人生让我们看到其救赎行为选择下的救赎意识的跃迁:跳出狭隘的宗教要求,跃迁到一种人道之爱,同时向我们展示了在这种跃迁过程中救赎者和被救赎者的心理错位。这种人道之爱其实也有影子,正如太阳光的投射一样,这种“影子”的实质其实是人性的缺陷,这又说明雨果对于自己人道主义的理想的认知是清醒的,因为有种超越人性的现实。
冉阿让的生命转折是人道之爱所带来的救赎,当他出狱时拿着黄护照,神情狼狈不堪,衣着粗鄙凌乱,把自己的脸深深地、深深地压在帽檐底下,遭到所有人的排挤和拒绝,他似乎敲过了所有的门,甚至企图在狗窝里寻求一点点温暖和庇护,仍然没有得到“许可”。在他对这个世界充满怨怼、敌意、愤怒、仇恨时,卞福汝主教将善与爱的橄榄枝投向冉阿让,给予他尊重、丰盛的美餐、舒适的床和他自己盗取的六副银器和大汤勺,并说“您现在已不是恶一方面的人了,您是在善的一面了。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救出来,交还给上帝”[2]95,此后冉阿让经历了一番巨大的思想挣扎:他在田亩漫无目的地走着,在遇见小克伦威尔后,“他的膝弯忽然折下,仿佛他良心上的负担已成了一种无形的威力突然把他压倒了似的,他精疲力竭,倒在一块大石头上,两手握着头发,脸躲在膝头中间,他喊道:‘我是一个无赖!’他的心碎了,他哭了出来,那是他第一次流泪”[2]111,这一刻,冉阿让看到了自己和显现在他良心上的光,甚至对那个自己有种强烈的反感,然后在比孩子更慌乱的猛哭后接过这一橄榄枝,获得了灵魂的救赎,并用一生来播洒卞福汝传给他的人道之爱,被这爱所拯救的有芳汀、商马第、沙威、格吕斯、珂赛特等。值得思考的是,他不得不用一套名字来遮掩苦囚役的真实身份,这样才能让人道之爱被人所接受、铭记、尊敬,这在一定程度上又说明了书中那些渴求爱但不懂爱的人的自我欺骗性,所以当“马兰德”这一名字被冉阿让自己揭开面纱之后,那个市的人们就不再认同他,甚至鄙夷他、忘记他,那爱在他们心中马上就烟消云散了。这种爱的包装构成了跃迁,这可能正是雨果所要向人们展示的人道之爱在这虚构的文学世界的缺失,这种缺失构成了雨果的人道主义理想,似乎雨果自身又明白这种理想在现实世界的不可能性,所以通过冉阿让所展现。
另外,冉阿让这种人道之爱存在着自身跃迁的一面。冉阿让把救赎之爱给过着黑暗生活、缺失母爱的芳汀的孩子——珂赛特,让她重新找回被爱的体验,满足被爱的需要。但是当珂赛特的少女心萌动之时,冉阿让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感,“这个人,能接受一切,原谅一切,饶恕一切,为一切祝福,愿一切都好,向天,向人,向法律,向社会,向大自然,向世界,但也只有一个要求:让珂赛特爱他”“得到珂赛特的爱,他便觉得伤口愈合了,身心舒坦了,平静了,圆满了,得到酬报了,戴上王冕了”[2]890-891,这是人性自私的赤裸裸的展露。所以,真的存在着真正人道式的爱吗?这正表明雨果对这种人道之爱的反思。此外,冉阿让的救赎行为也值得思考,他总是因为给予他人无私的爱而被认出,一次又一次揭开刑犯身份,再次陷入危机,比如给装成乞丐的沙威救助、给德纳一家救助金等,这都说明了冉阿让的爱是包含了某种混沌感的,他认不出他们,构成一种跃迁。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恰恰是雨果让我们所要思考的:真正的人道主义之爱是会完全成为一种习惯,但是这种无防戒心理的爱又容易给自我带来困难。
三、爱的“基督”:人道主义与本性之爱的复归
雨果的人道主义是:要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以人为本,包含“平等”与“博爱”观念,传播正能量,从而感化他人、感化社会。所以,他的人道主义之爱,笔者认为乃出于为男性者的父爱本性,但这种爱是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父爱,跳出人爱的人爱,包含着雨果内心强大的期待:用伟大的人道之爱去改善虚伪无情、真情沉灭的社会现实。这种人道主义之爱具体而言就是父性博爱,蕴含着人类普遍性的真挚情感。他在《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里用美丑对照原则,用充满巨大力量的感情表现出了一种高尚的爱,来尝试让人的本性之爱得到复归,创造了一个属于全人类的人道主义之爱的范式——父性博爱,同时,又把自爱作为其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雨果浪漫主义之爱的具体投射。
在《巴黎圣母院》中表现心灵的美和崇高的是伽西莫多和爱斯梅拉达。在甘果瓦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爱斯梅拉达主动牺牲自己的婚姻来保住其生命,伽西莫多面对即将遭受制裁的爱斯梅拉达时,伸出援手救走爱斯梅拉达,这两个崇高的灵魂,最终以结束生命来反抗“圣母院”所代表着的宗教及人性的黑恶势力。此外还有克洛德,他在没有被困于圣母院编织的网之前,他离雨果所提倡的人道主义之爱的距离是不远的,他明白“人是需要感情的,他知道没有温情,没有爱的生命,就像一个干燥的车轮转动时格轧格轧的乱响” [1]132,当他肉体死去,而精神冲出“圣母院”的枷锁后,那爱的本能就重新回到其身上;在《悲惨世界》中“父性”更是被冉阿让体现得淋漓尽致,他获得了卞福汝的救赎,又用自己的一生去救赎他人,用一种超凡的力量,给予他人人道之爱。另外,还有因开朗的性格、顽强的生命力而演变成法国文化中拥有此类性格的人的代名词,且象征着乐观、可爱的粗鄙以及因为年少时一无所有而对人生的种种危险甚至死亡都显得极不在意的性格特征的伽弗洛什,他在儿时就展现出与年龄极不相符的父性的一面,比如他收养照顾被迫在街上流浪的两个马侬的“孩子”。虽然这些人物都逃不了人性的某些弱点,但是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人道主义之爱的 “复归”,并且通过不断地播爱而拯救一个个灵魂,比如冉阿让放走了一直追捕他的沙威,他本可以开枪结束沙威的生命,同时结束他被追捕的恐惧。沙威在冉阿让的父性博爱的冲击下,在自我的反省当中看到了冉阿让善良的生命本质,看到了自己被法律、规训所带来的盲目,由此他展开了一场思想斗争,最终选择跳河自尽,他是希望通过河流来洗涤自己思想上的污垢,净化灵魂,从而获得一种超脱。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指出:“最基本的爱是博爱,它是所有形式之爱的基础。”[3]47博爱是雨果人道主义的关键,爱所包含的基本意义与使被爱者体现出人类本质特性直接相关。因此,爱一个人就意味着爱人类,但笔者认为雨果的博爱是建立在自爱的基础上的。从《巴黎圣母院》到《悲惨世界》,我们可以看出雨果笔下的有些人物,他们的人格不断健全,越来越有自爱的能力,在拥有自爱的能力之后更加把那种博爱给予这个世界,比如爱斯梅拉达,她爱弗比斯,但是自爱残缺,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健全、不成熟的爱而失去了自己的性命;而冉阿让是首先完成了一场自我救赎,会爱自己之后,才去爱别人的。所以,雨果人道主义所追寻的父性博爱的基础是自爱。
另外,雨果在其《静观集》中的《我要去》写道:“人就应当以普罗米修斯,以亚当为榜样。人应该从巍巍天宫偷取长明之火;应该去揭穿笼罩自身的玄虚,并把上帝偷来。”[4]面对充满虚无、伪善的世界,雨果再次表明只有让爱变成父性博爱,人才能为人,其所倡导的人道主义就是在表明自己对父性博爱的追求,我们可以从中看见雨果内心的强烈期待。值得思考的是,他把这种爱的希望寄予在《悲惨世界》中的伽弗洛什身上,一方面孩子是代表着希望的,是人类生命史的接续者,他可以接续日益衰老的冉阿让,把这种父性之爱传承下去,所以雨果塑造了这个小小的生命;但另一方面从“孩子”的眼观看,与丑恶的政权革命不过是一场游戏,但是因为“父爱”的力量弱小,过于“孩子气”,其实是不能获得成功的,所以文中的伽弗洛什在捡子弹时被敌人打中,在革命途中呜呼哀哉,这样有着觉醒的人道主义之爱意识的孩子,最终未能从那异化的社会中被拯救出来,并且被伽弗洛什照顾的孩子,在获得短暂的安全和温暖之时,由于“革命”,又重返流浪的生活,逃到“革命”中那无人问津的花园,当然这又是雨果对自己理想的“父爱基督”不能实现的自我清晰的思考,正是不能够实现,所以内心的期待更加强烈,也看出雨果想要自己做觉醒的父性人道主义者是相当困难的,但雨果也在积极践行他的这种爱的“基督”。雨果不仅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更是作为法兰西民族的民族诗人和人民诗人,将文学与民族精神、人类发展联系起来,就像鲁迅所说的文艺作为“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便负有“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塑造“精神界之战士”的职责[5],而且他对于这种爱的“基督”有着更广的思考,把视野扩展到人类永恒存在之上:人类必然要经历带有周期性的磨难,如何在人道主义之上实现这种父性之博爱,是每一代人必须面临的困难,只要人类存在,就要为此努力;他还在普法战争的硝烟中,揣着炽热的情感,积极投身于斗争之中。他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激励人民的斗志,并毫不犹豫地报名加入了国民自卫军的行列。
总之,爱是一门艺术,在雨果笔下的爱主要是受宗教影响,这构成两个极端,一种为冉阿让所代表的父性式的人道之爱,另一种是以克洛德为代表的冲破教条思想束缚的异化之爱。如何爱?怎样去爱?怎样才能避免爱被异化?这是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面对的困境。弗洛姆还指出爱在现代社会衰变就是因为 “现代人与他自己、与他的同类、与他的本质异化了。他被转变成一种商品;在现存的市场条件下,他对自己生命力的体验变成一种必须带来最大回报的投资”[3]86。因此,雨果用他的人道主义追寻“爱的艺术”,笔下人物爱与被爱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刻的思考,这种父性式的人道主义之爱是我们当下需要去学习的。
参考文献:
[1]雨果.巴黎圣母院[M].陈敬容,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雨果.悲惨世界:全 3 册[M].李丹,方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3]弗洛姆.爱的艺术[M].李健鸣,译.商务印书馆,1987.
[4]雨果:雨果诗选[M].程曾厚,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226-227.
[5]鲁迅.摩罗诗力说[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01-102.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褚梅娟(2002—),女,汉族,云南玉溪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