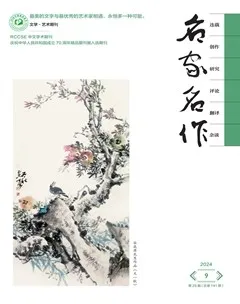试比较夏志清和李欧梵关于鲁迅早期作品文本的差异化解读
[摘 要] 作为五四新文化浪潮的领军人物,鲁迅始终是中外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焦点。夏志清先生和李欧梵先生同作为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二人因解读角度、政治立场等因素,对鲁迅作品内涵之解读存在差异性。以两部海外研究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铁屋中的呐喊》为视角,分析比较夏志清和李欧梵关于鲁迅作品文本的差异化解读。
[关 键 词] 鲁迅;夏志清;李欧梵;作品解读
对鲁迅作品思想的分析与解读,历来众说纷纭。在夏志清和李欧梵的研究中,存在的较大差异是:前者侧重于对其作品“文学性”内容的解读,分析的是一个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后者则在其作品所体现的“思想性”的内涵上进行了更多的深掘。夏志清曾经明确地指出,他纂史的首要目标在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亦即,焦点落在探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所体现的“文学品质”上。①但不可否认的是,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夏志清对鲁迅作品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偏见性”。李欧梵在对鲁迅作品的总结性研究里,不仅关注鲁迅小说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同时也深入分析了其文本底蕴的思想内容和与之息息相关的社会现实的演进变化。《铁屋中的呐喊》从相对客观的角度追根溯源,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真实的鲁迅。
一、夏著对鲁迅的“偏见性”解读
夏志清在评述文学作品时的最显著特色,在于他能从简洁的几句话中提炼出深刻的见解,尽管没有详尽阐释,但足以对人产生极大的触动,激起更多新颖的思维与创意②。他对《药》的解读可以说明这一点:
《药》……既是一篇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真实暴露,也是一篇革命的象征寓言,更是一个叙述父母为子女而悲痛的动人故事。……这两个青年(夏瑜和华小栓)之死,情形虽个别不同(一个是为理想而牺牲的烈士,一个是因无知愚昧的牺牲品),可是对他们的母亲来说, 他们怎样死去是不重要的。做母亲的丢了儿子,感到的只是一种难以名之的悲伤,一种在中国封建社会生活中不但要接受,而且还要忘怀的悲伤。这两位青年死后,葬在相距不远的地方。一个寒冷的早上,这两位母亲到坟上去哭儿子时,碰在一起;她们所感到的痛苦,可说是完全相同的。③
夏志清对《药》的解读超越了具体时代和人事的局限,谈出了亲子之情的普适性和永恒性,而不只是囿于传统的“革命寓言”说。这篇文作被作者划分为四个部分,前段主要描绘了华老栓为治愈儿子的病,从刽子手那里买“药”(实为“人血馒头”)的详尽过程与内心感受,其他杂事他已全然摒弃。“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接下来的部分讲述了华老栓和妻子全心全意照顾儿子进补之情,“他(华小栓)的旁边,一面立着他的父亲,一面立着他的母亲,两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里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文章的最后一节聚焦在华小栓的母亲与夏瑜的母亲为孩子们上坟时所表现出的深沉哀痛和叹息。至于辛亥革命的议题,则是在第三节通过华老栓在茶馆中与其他客人的谈话间接展现的。根据篇章长度即可窥见,在这个故事中“亲子情深”这一主题的重要性。这份深情,是跨越时空、地域、种族等界限的普遍情感。
尽管夏志清并未否认《药》中对华老栓及其妻子的指摘,但在他看来,鲁迅并非以民众的无知为斥责核心,而是在揭示传统生活方式的现实。在夏志清眼中,中国传统封建制度植根的文俗和环境造就了人们的昏昧无知,对于像华老栓这样的普通夫妇来说,他们无力自省,要求他们有所觉悟无异于逼迫他们面对难以承受之重,他们只好接受以“人血馒头”医病这样的旧观念。然而不管华老栓夫妇在“传统”压力下如何行事,他们对子女的天性之爱,仍然是不可抹去的人性之光。换言之,他们的“愚昧”并非彻头彻尾的愚昧。显然,通行的文学史教科书对华老栓及其妻子的评判只停留在个人层面,而且认为鲁迅的批判也是针对这位特定人物;相对地,夏志清则指责整个种族的“传统”观念,并且认为鲁迅的批判同样针对这些“传统”。如果将两种观点对比,毫无疑问夏志清的见解显示出更深层的洞察力。鲁迅曾自我概括其作品充满了深刻的忧虑与愤慨,基于此,夏志清的解释无疑与鲁迅的自评更为契合。
作品中除了对《药》的非传统型解读外,其他地方也可见一斑。例如将《孔乙己》比作海明威早期作品关于尼克·亚当斯系列故事的风采;而对吕纬甫这一人物的刻画,正体现在《在酒楼上》中,昭示了传统人生的若干优点;至于《肥皂》,该作在其讥讽本质的底层,巧妙地隐喻了更深层的意涵等诸多论调①。
尽管如此,我们依旧可以明确地观察到,夏志清仍旧未能彻底脱离意识形态的影响,其在政治立场与学术研究的交汇处显著展现出特定的政治偏好,这也对他的艺术评价造成了影响。例如在谈论《狂人日记》时,夏志清评价其“非常简练地表露出作者对中国传统的看法”,并体现了“鲁迅对于传统生活的虚伪与残忍的谴责”。分析虽然正确,但确实略显浅薄。《狂人日记》这部作品是他全面反击封建主义的首次强烈宣言,透过主人公的“疯狂”剧烈抨击封建礼教,其在现代思潮与文化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如此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岂是简单一句话即能概括的吗?夏志清评价《狂人日记》展现了极佳的艺术技艺及颇具深意的讽刺色彩,然而对于其表现手法的细节,则未予详细解读。除此之外,夏志清对《阿Q正传》的解读也不尽人意。文末篇章描述了阿Q邂逅了“一个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子”,坐镇衙门之地,此景激发了他内心的压迫感,使其不自觉地产生了恐慌,甚至连腿膝都不听使唤的软了,不由地“跪了下去”;旁人对他吼道:“站着说!不要跪!”但阿Q却似乎“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此一细微描写被众多学者重复提及,因为它突出体现了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这种无意识与阿Q这一形象紧密相扣,使阿Q成为一个“共名”,象征着当时中国人的国民性,对于研究鲁迅的批判观点颇有贡献。但是,夏志清却未将其视为洞察鲁迅揭露国民性格的途径,相反对阿Q这一名字持有偏见,认为把阿Quei缩写为阿Q是“作者故弄玄虚”等等。这样看来,夏志清对《阿Q正传》的解读和对鲁迅的评价显得有所偏颇,其评述中透露出情绪化的成分②。面对夏著的这种偏见,需要我们以审慎客观的态度去分析。
二、李著对“独异个人”和“庸众”的解读
李欧梵先生对鲁迅作品文本分析的一大特点是提出了“独异个人”和“庸众”的概念,这个概念源于鲁迅在《呐喊自序》里创造的“铁屋子”意象。鲁迅把当时的中国社会看作是一座密不透风、岿然不动的“铁屋子”,里面的人有“昏睡者”,也有“觉醒者”。“昏睡者”在其中占多数,他们长眠于这铁屋之中,没有任何的不适,也没有逃离的意识;“觉醒者”则是少数人,他们意识清醒,一边奋力唤醒昏睡的人,一边拼命毁坏这座囚禁他们的牢笼,试图以反抗来换取自由。鲁迅借由“铁屋子”这一形象深刻观察并解剖了当时社会的情况,刻画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实况及不同社会阶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轨迹。《铁屋中的呐喊》一书中,李欧梵所做的“庸众”与“独异个人”之区分,正是出于“铁屋子”寓意中“众多昏睡者”对“极少数觉醒者”的映照,进而增强了“铁屋子”这一文化象征的深度和影响力③。
鲁迅笔下的“庸众”与“独异个人”这两种典型形象,是以不同的方式所呈现的。李欧梵根据这两个形象构筑的“家谱”,探究了鲁迅作品对民族特性的深层关怀:对“独异个人”的质疑与哀悼。“独异,即个人自大,通常有着‘几分天才与狂气’;庸众则是指‘合群的爱国的自大’。”①
在《药》一文中,夏瑜身为“独异”的革命者,努力激发沉沦民众的政治觉醒,却不幸沦为刽子手刀下的牺牲品。更为凄惨的是,用他的鲜血浸染的馒头,竟被华老栓一家用来治痨病。李欧梵在这里对这种“独异个人”的孤立状态进行剖析:“烈士被庸众所疏远和虐待,成为孤独者;但这孤独者却只能从拯救庸众、甚至为他们牺牲中,才能获得自己生存的意义,而他得到的回报,又只能是被他想拯救的那些人们关进监狱、剥夺权利、殴打甚至杀戮。”尽管夏瑜愿意为革命事业献身,但那些昏睡的民众依旧停滞不前、守旧并茫然不觉——华老栓一家继续迷信旧有的封建说教,民众的奴性与愚昧也未有所改变。鲁迅通过《药》表达了对那些革命先烈的悲惨命运的哀悼,同时也抒发了对中国社会前途的渺茫希望的忧愁。②
《狂人日记》描绘了主角在得知了“吃人”与“被吃”错综复杂的关系后,呈现出混乱而又清晰的心智状态,深刻映射出了“独异个人”的核心。这位狂人在其心智紊乱之际,逐层剖析“吃人”的本质,其行为却更加令周遭的人确信他的精神病症加剧。正是在这残酷的社会背景下,狂人挣扎着寻求“独异”之道。
根据李欧梵的观点,越是意识觉醒的人,他们的言行往往更加受限,更难以对庸众施加影响去转变他们的观念。从思想的进步来看,这样的人是幸事者,他们超越了当时大众的时代局限性。但是,此种改变却遭受了大众无情的排斥,导致这些具有个性独异者的悲剧命运。此外,李欧梵对《狂人日记》中狂人的结局“然早已愈,赴某地候补矣”做出了阐释:这表明狂人重新融入了被认为是“正常”的状态。这似乎是清晰的认知,实则是其“独异”的清醒意识的消退,其独立的思考力量已荡然无存③。
李欧梵创立的“独异个人”与“庸众”的理念框架,显现了他对鲁迅文学创作“思想性”的独到见解和文本回溯的学术贡献。他深入细致的文学阐释为现代学界提供了新的视角以探讨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与研究,从而让读者对鲁迅深邃的思想有更为清晰的认识④。
三、综述
夏氏和李氏从不同角度对鲁迅作品价值的解读,反映出海外汉学界对鲁迅评价的多元化。但不论是前者带有“偏见性”的“文学性”解读,还是后者对鲁迅作品中丰富的文化意象和思想建构的深掘,都为鲁迅作品的解读提供了多种视角与方法,为海外汉学界的鲁迅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后人皆需要在充分理解夏著和李著的基础上,对鲁迅作品的文本作更深入的批判性思考与分析。
参考文献:
[1]刘迎.何种“洞见”,如何“偏见”?:谈谈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鲁迅书写[M].名作欣赏,2020(3):5-8.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34-35.
[3]刘畅.在政治立场与学术探讨之间:评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鲁迅专章[J].重庆社会科学,2007(1):60-63,68.
[4]李梦冉.“铁屋子”意象与其包含的文化形象:评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对“独异个人”和“庸众”的诠释[J].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5):57-60.
[5]戴诚诚.回本溯源:评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J].青年文学家,2014(12):44-45.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