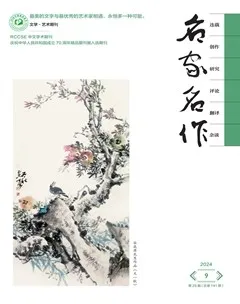同人异体:袁机传状文中的人物再现
[摘 要] 早在20世纪,传记类文字以其对人、事的生动记录就已经成为各方学者研究古代文学的重要史料。其中,祭文又因其蕴含作者对传主的强烈情感而使我们能还原出有别于其他传记类文字的人或事。传记对于现代学者复现、完善相关人物事件有着极大的作用。如果说史传类文字是将古人古事讲给现代人听,那么带有极强抒情性质的祭文则是将情感注入这些人物、事件之中,把一个孤立的形象还原成一个生动的人,把一段生硬的文字编写成一段精彩绝伦的演出。着眼于祭文中的人物再现,以三大祭文中的《祭妹文》为例,对比其余记录袁机的小传,浅谈《祭妹文》再现出的人物形象,并以此归纳总结祭文对于传记人物再现的意义。
[关 键 词] 袁机;传记;文学形象
一、祭文中的人物再现
袁枚曾言,家中三个妹妹,三妹袁机是最端丽的一位,精读诗书、通晓诵读。可惜的是,这样美丽端庄的女子却英年早逝。袁枚所作《祭妹文》表达了其对妹妹最真挚的情感:他从日常家庭琐事入手,写出妹妹德能才干皆优,正是过往种种如此可爱浮现在眼前,才映衬得阴阳两隔如此之痛,其间浓厚的思念、哀愁与悔恨不禁令人涕下。而在这样蕴含真情的文字背后,一位栩栩如生、惹人怜爱的才女跃然纸上。
袁氏兄妹从小一同长大,共捉蟋蟀、一同温书的场景历历在目。离别时的悲伤痛哭、归家时的怅然大笑,如此种种无不体现出二人情谊之深。所记不过日常繁杂琐事,但又正是因此在斯人已逝后再不复往日情景,这种巨大的落差感让人痛彻心扉,便是袁枚所叹:“我一日未死,则一日不能忘。”身有疾却不愿让兄长忧虑,直到弥留之际才将思念的情感无约束地流露出来。她身上的坚持太多,别人看到难免心生怜爱。可如此可爱的女子婚姻却是失败的,这不禁让袁枚反思为何幼妹的婚姻会走上这条道路。忆起幼时兄妹二人学堂“差肩而坐,爱听古人节义事”,从小便接受经书熏陶的袁机不仅仅是将这些所学记在心里,长大成人后的她也在践行仁义礼智信。恪守职责是她行为的指南,所以她从始至终都对自己的婚姻抱有极致的“忠贞”。同婆家断绝关系回到娘家,她的遭遇却让哥哥自怨“累汝至此者,未尝非予之过也”。兄妹本是共同学习经书礼仪,但在目睹妹妹婚姻的悲剧之后,袁枚又是如此痛心,让他不得不回头审视那些经书。一位本该大放异彩的才女却因为婚姻变故逐渐泯然众人,以致草草结束一生。在袁枚看来,妹妹才华横溢、通情达理却又一生多难,此种经历难免让人无比痛心。袁枚曾认为女流之辈中少有明事理、兼赏雅俗之人,但自己的妹妹却在离婚归家后在他面前展示出了女子独一无二的风采。照顾长辈、扶持兄长、操理家事,袁机做得井井有条。在袁枚笔下,袁机是如此可怜又可爱的一个人,她有喜有忧,生动活泼又神采奕奕,绽放着特有的风采。
二、其余小传中的人物复现
除袁枚的记载之外,其余史书中也有不少关于袁机的传记或传记类片段。其中比较完整的是:
《杭州府志》所记:
袁机,国朝诗别裁集,字素文,仁和人,袁枚之妹。幼字如皋高氏子,后高以子有恶疾,愿离婚。素文曰:女从一者也,疾我侍之,死我守之。卒适高。高躁戾佻荡,倾奁具为狎邪,费不足,扑抶外至,以火烧灼之,姑救之,殴母折齿。既,欲鬻妻以偿博者,不得已,始归母家。长斋素衣,孝养母氏。高氏子死,哭泣尽哀,血泣尽。越一年,亦死。女子中苦行无逾此也。检箧笥,得手编列女传三卷,诗一卷。[1]
《通州直隶州志》所记:
袁机,字素文,钱塘太史枚女弟。幼许字富平丞高浤子绎组(祖)。长而弗类,家人请改盟,机持姑所寄金项锁对,泣不食,遂归组。组性狂悖,以火灼机,索其籢具几尽,将负机而鬻于博者,机乃大归,依母与兄。衣不纯,采不发,剃不闻。乐皋人至,必出问:堂上姑安否。有一女病喑。尝有句云:女儿言语输鹦鹉,兄弟情怀感鹡鸰。闻者怆然。[2]
这两段文字都围绕其婚姻生活展开,二文所记也大抵相同:袁机未婚夫高绎祖荒诞无度,未结亲前高家长辈曾主动提出离婚,可袁机却始终坚持“女从一者”的观念,甚至毅然决然地坚守自己还未达成的婚姻。可这样的坚持换来的婚后生活对她来说是可怕的。高氏暴躁性情,不但花光了袁机的陪嫁,而且还对她拳打脚踢、拿火烧她,最后甚至想卖掉袁机来偿还赌债。唯一不同的是二者对于袁机归家后与婆家交往的记录:前文所记乃是高绎祖死后袁机哭泣尽哀,后文则是通过同乡人代问婆家姑母情况。末尾皆是附上带有评点性的语句,后文更是引袁机七言古诗;但前者所叹乃是带有创作者的个人情感的惋惜与可怜,而后文则是更为客观的转述,以袁机诗词的接受情况隐喻了作者对此事的态度。
除祭文外,袁枚在《随园诗话》里也有一段记载的文字:
三妹名机,字素文。秋夜云:不见深秋月影寒,只闻风信响阑千。闲庭落叶知多少,记取朝来着意看。闲情云:欲捲湘帘问岁华,不知春在几人家。一双燕子殷勤甚,衔到窗前尽落花。他如:女娇频索果,婢小懒梳头。怕引游蜂至,不裁香色花。皆可诵也。遇人不淑,卒于随园。香亭弟哭之云:若为男子真名士,使配参军信可人。无家枉说曾招婿,有影终年只傍亲。豫庭甥哭之云:谁信有才偏命薄,生教无计奈夫狂。白雪裁诗陪道韫,青灯说史侍班姑。[3]
可以看出,袁枚非常肯定袁机的文学才干,才在她过世后收集诗稿。在此段记载中,袁机所咏诗歌或是因为自然美景或是处于闲情逸致心境之中,都能看出这位女子对于生活有着如此多的细致感悟,袁机才学之高也由此有了具体表现。文中提到豫庭甥是袁机的外甥陆建,陆建在《哭从母》中把袁机比作谢道韫、班昭,也能看出她的才学在家族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对于她的婚姻,哥哥袁枚也曾发出“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的感叹。她四岁读书,才学不输家中兄长,却又固执坚守自己身为女子的本分与高氏结亲。高氏无才无德,袁机对于诗书的兴趣毫无疑问遭到了巨大的打击。在袁家可以同兄长谈笑经书,在高家却要面对一个不能文且品行极差的丈夫。说袁机对高绎祖有爱,实在是无迹可寻。《小仓山房集》卷7中袁枚曾为袁机作《女弟素文传》。在《女弟素文传》中,对这场婚姻的缘由也有写明:二人婚约本是袁家、高家上一辈人恩怨的缔结物。袁机和高绎祖没有青梅竹马之情,一把当作信物的金锁,便把袁机死死地锁在了这场失败的联姻中。在冯雪的《清代婚姻制度研究》一文中曾对清朝律法婚姻嫁娶做了详细的研究:子女嫁娶皆由家族中长辈做主,对于结婚年龄,清朝通典中规定,男子结婚必须年满16岁,女子必须年满14岁。若说古代推崇早婚早育,可袁家长辈面对二十余岁的袁机也没有“恨嫁”之说。收到信件之后袁家本愿退亲,并未固执地想把女儿嫁到高家,怎奈何袁机又大哭又闹绝食,父母这才不得不同意。如此看来,袁机落到这样的结果全因她死板又固执,可怜又可悲。传中袁枚记录了一处有关妹妹婚姻的细节:高氏“见书卷怒,妹自此不作诗;见女工又怒,妹自此不持针黹”[4]。对于妹妹的遭遇,不同于《祭妹文》中情感直接流露,此两篇中将情感抽离出了兄妹之外,再现出来的形象同前文提到的两篇传记有更多相似之处。本是一个灵活生动的女子,在纵观一生的记载视角下剩下的却是固执的标签。
三、形象再现差异与原因探究
(一)作者与传主关系带来的差异
从前文论述可以看出,《祭妹文》中的形象之所以更为饱满,最大原因就在于袁枚同袁机自小一同长大,所知更多。《女弟素文传》中所记袁高两家如何结缘,将一脉相承的因果抽丝剥茧,才有更多的细节浮现。袁枚同袁机本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袁枚所描述的袁机更加生活化,而《杭州府志》与《通州直隶州志》皆为地方志,其作者同传主本人或不相识,其笔下的人物也难免单薄、性格唯一。
(二)叙事详略带来的差异
在《杭州府志》与《通州直隶州志》中,对于袁机的婚姻都提到了是在“高氏欲鬻妻以偿博者”后,袁机才离婚归家。归家的原因并未写明,但从文字联想一下,袁机的归家很可能是在丈夫种种暴行之下失望累积够了的“无奈而归”。可在《祭妹文》中明确提到袁机是“义绝而归”。而从“义绝”这个行为出发,也能让我们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结论。
清代律法中的“义绝”是一种一定程度上为保障夫妻双方权益的判决离婚。《大清律例》中明确规定了“其夫里妻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二等(须妻自告乃坐)。先行审问夫妇,如愿离异者,断罪离异”[5]。同样,将妻嫁卖、典雇官府也应当判决义绝。袁机的婚姻是通过义绝来离婚的,但在《女弟素文传》中袁枚也写明:妹妹婚姻的义绝是通过父亲袁滨上至官府才得以判决的。从这里能看出来,袁机的离婚归家也并非全然是自己的选择。清代法律已明文规定丈夫殴打妻子可以上报官府判决离婚,但袁机在被高氏踢打、用火烧烫之后并没有选择上报官府,而是在高氏要“卖妻鬻博”之后见其“耳目非是”才告以家父。在被殴打致伤之后没有告知家里,却在要被丈夫卖出去的时候向父亲求助,她对妻子身份的“忠贞”的坚持是如此固执又刻板。面对一个随时会对她施加暴力的丈夫依旧选择隐忍,只是在丈夫将要把自己卖了赔赌债的时候才惊觉自己所坚持的“贞”即将受到极大的玷污,才又向娘家人寻求帮助,离婚的行为是由父亲去推动,而并非袁机意识到了高氏不是可以托付的良人。她可以容忍丈夫抢夺嫁妆、打骂烫伤自己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她依旧要维持那名存实亡的婚姻。但她不能容忍自己的丈夫要把自己典卖出去另做他人妇。在她年幼的时候无视高家长辈与自家父兄的劝诫,仅仅用一纸婚约将自己束缚在高绎祖的身边,年长的时候更是任打任骂也要守住自己“忠贞”的底线。《随园诗话》收录了袁机在离婚之后惦记婆母的诗作。《女弟素文传》中也记载,在高氏病逝之后袁机病倒,一年后病逝,我们尚且不能将高氏的病逝同袁机病倒相关联,但从她所作的诗作中也能看出,即使离婚之后,她心中仍然挂记着自己过往所忠的夫家。
若说《杭州府志》与《通州直隶州志》中对袁机的描述让后人认识到此女子是一位固守“忠贞”的妻子,那么袁枚在《女弟素文传》中所提到的袁机离婚细节,则是让人进一步意识到这样的女子实在是“愚贞”。
(三)文体不同造成的差异
袁枚本人为袁机所作传记类文章或文字并非唯一,《祭妹文》中的袁机和《女弟素文传》中的袁机也存在不同。前者与韩昌黎《祭十二郎文》、欧阳修《泷冈阡表》并称为三大祭文,其中涵盖的对于已故之人的浓厚思念已然不是篇幅文字所能限制的。
《祭妹文》作为袁枚葬三妹的奠词,所流露的真挚感情又如同细流一般涌动。其中回顾的是袁机一生与自己有关的事情。祭文所作之时是内心悲伤已经安抚到可以提笔作文,便一件一件回忆与已逝之人共同经历过的事情,但文末这种悲伤又被重新唤起,所剩下的就是一声声悲伤的呜呼哀哉。而这实际与祭文的文体特征相关。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言:“ 祭文者,祭奠亲友之辞也。古之祭祀止于告飨而已。中世以还兼赞言行,以寓哀伤之意,盖祝文之变也。”[6]可以看出,祭文的文体功能是得到扩展的。追忆逝者生前美行赞语,反而与斯人已逝的现状对比更强烈,天人两隔之愁苦跃然纸上。而《祭妹文》书写也依旧符合此种文体要求。所记袁机同家中兄长一起捉虫斗虫,一起诵读诗书,这些生活化的情节融入让后人在读到此处时所看到的是天真可爱的正面形象,而她失败的婚姻仅仅是一笔带过。
而《女弟素文传》则是带有明确作传意识所写的传记。韩兆琦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中将传记分为五类,分别为史传、类传、散传、专人传记、传记小说,而《女弟素文传》则属于散传的范畴。不同于祭文的哀悼目的,散传所侧重的是“立传”方面。在衣若兰《明清女性散传》研究中曾言:“当(文章)作为‘传’时,它进入的是一个非私人悼念、庆贺的公开场域。”换言之,则是需要更为客观真实地记录传主事迹。而回顾袁机的一生,绕不过的便是她那失败的婚姻。妹妹一生的转折点在于婚姻变化,在于她对于女子“贞”的固执。高袁两家的结姻在《女弟素文传》中也得到了进一步剖析。而《随园诗话》作为一部诗集作品,其中关于袁机的类似小传的记载也会更多偏向袁机在诗作创作上的具体行为,并以记录其创作诗文为中心。
四、总结
对于袁机,记录她的文字并不单一。但若仅仅从史书中看,便只能看到一个固守陈规、毫无新意的女子。若是又只从祭文中看到她与兄长相处的灵动,又难以意识到这位女子还是一位自愿被史书经义带上镣铐的可悲之人。传记本是当代人尽量真实全面去认识、还原古人往事所依靠的珍贵的文字记录。对一个过去的人展开评价,断不能仅仅依靠一段文字定论。跨越时代在现代再现出千年以前的人物本就是一件困难之事,通过文字记录尽可能真实地去还原出那些人物,便是对比不同类型传记差异存在的一大意义。
参考文献:
[1]杭州府志:卷一百一[M].清乾隆刻本.
[2]通州直隶州志:16卷首1卷末1[M].清光绪二年刻本.
[3]袁枚.随园诗话[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4]袁枚,著.王英志,校点.小仓山房文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5]大清律例:47卷[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徐师曾,著,于北山,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李懿昕(2000—),女,汉族,四川宜宾人,本科,研究方向:女性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