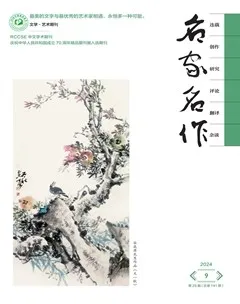立象以尽意 酒里品人生
[摘 要] 《饮酒二十首》是陶渊明一生中的重要作品,在这二十首酒后之诗中,作者通过大量“酒”意象的设置,展现了其遗世独立的人格追求、安贫乐道的生活姿态以及豁达乐观的思想境界等深刻意蕴。《饮酒二十首》是走近陶渊明、了解陶渊明的重要作品。
[关 键 词] 陶渊明;《饮酒二十首》;酒;意象;意蕴
在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河中,“酒”与文学关联密切,早在《诗经》《楚辞》《乐府诗》《古诗十九首》中就有酒的存在。魏晋时期,“酒”与诗的关联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酒”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道具与体现途径,譬如刘伶嗜酒如命,常常大醉不醒,自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还作了《酒德颂》;再如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短歌行》)的喟叹等。生于东晋的陶渊明,深感朝廷的风雨飘摇、黎民的朝不保夕,在入世与出世之间,他矛盾过、挣扎过,“酒”便成为他对酌山水云烟、抒发人生真意的重要方式。在《饮酒二十首》中,陶渊明通过对不同类型的“酒”意象的营造,展示了其独特的酒意人生与诗意生活。
一、“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其七)——遗世独立的人格追求
陶渊明曾在《五柳先生传》里这样描述自己:“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 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1]陶渊明爱酒,他在《止酒》中说:“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可见,酒在陶渊明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酒”在陶渊明这里不仅仅是他的饮食爱好,更是他消愁的工具,他更多的是把酒引入诗文,借酒来传达他有关人生的思考。梁昭明太子萧纲曾指出:“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陶渊明集序》)。逯钦立先生在他校注的《陶渊明集》中收录了陶渊明诗文142篇,其中提到饮酒的就有56篇,约占总篇目的40%,可见“酒”是陶渊明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意象。
陶渊明是一个对自己与社会有期待的人,他生于乱世,一心想要匡世济民,曾经五次出仕、五次归隐,他为社稷殚精竭虑,但又生性耿介,终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落得满心的失望与落寞。陶渊明四十一岁时彻底离开了官场,退隐田园,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要远离纷扰,保持人格的独立自由。陶渊明辞官后,“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 《归去来兮辞》)。田园生活显然激发了陶渊明饮酒诗的创作。在陶渊明一生的创作中,《饮酒二十首》是其重要作品,学界多认为其写作于陶渊明归隐之后。《饮酒二十首》组诗虽以酒为题,实质上并非单纯咏颂酒意,而是陶渊明借酒为引,以诗歌为媒介,抒发内心情怀、表达思想之作。《饮酒二十首》写于桓玄篡晋的政治背景下,是陶渊明表露心迹的重要作品。我们通常说“酒后吐真言”,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通过饮酒的方式,一吐胸中块垒。因此,《饮酒二十首》凝聚着诗人的哲学思考,表达了他对人生的独到见解。
在《饮酒》(其七)中,陶渊明这样写道:“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陶渊明远离喧嚣动荡的社会后,饮酒赏菊,忘却尘世烦恼,这里有的是对归隐生活的陶醉和对世俗纷扰的超脱。“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倾”,他独自饮酒,自斟自饮,体现出一种自在逍遥的状态。这种日子虽然有些孤独,但更多的是自在惬意,恰如空中的“飞鸟”一样。在末句中,诗人仿佛回归到一种纯净、超脱的境界,表达了他对精神自由和宁静的追求,也让整首诗在一种空灵的氛围中结束。这首诗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和饮酒行为的展现,传达出诗人归隐生活中的闲情逸致和对独立人格的追求。
陶渊明虽然归隐山野,但作为一个心中有着诗与远方的人,终其一生不能遂其所愿,内心的隐痛与不甘是显在的。在这个远离俗世纷扰的世外桃源,他常常借酒抒怀,宣泄心中的苦闷,其中有自解、有宽慰,所以他很不理解“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饮酒》其三)之人。在《饮酒》序中,陶渊明说:“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在《饮酒》(其十三)中,陶渊明写道:“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很显然,陶渊明不愿意做一个醒者,无力地旁观世间百态,他只愿沉眠于酒乡,在其中排解内心的苦闷,同时做一个兀傲不羁的“酣中客”,过一种惬意的秉烛夜饮的率真生活。在饮酒(其二十)中,陶渊明不断慨叹世风日下,思慕远古伏羲神农时代的真纯之风,愤慨“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的世道,只能借酒抒怀,“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与其说是醉酒,不如说是对现在这种遗世独立的生活的沉醉。
在陶渊明的一生中,酒就是他抵御苦闷、沉醉归隐的最佳伙伴,其中有失落,更有坚守。《饮酒二十首》深刻揭示了作者以清高自许、坚守节操的品格,清人张潮就曾说《饮酒》诗“独标清操,世无其匹”。
二、“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其十九)——安贫乐道的生活姿态
陶渊明是一个注重精神生活而淡化物质生活之人,他生于乱世,从小家境清贫,他的生活从不曾优渥过,他有着安贫乐道的品质。他在《五柳先生传》中很明确地写道:“不慕荣利……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因此,对于陶渊明来说,“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正是他一生的写照,他还常常“酬觞赋诗,以乐其志”。
在《饮酒二十首》中,陶渊明屡次写道归隐之后生活的清贫。在《饮酒》序中,陶渊明就说归隐之后的生活“偶有名酒,无夕不饮”;在《五柳先生传》中,他说酒因家贫不常得,名酒就更有偶尔得之,其清贫的生活可想而知。他在饮酒(其二)里也谈到君子“固穷节”,显然是他自己的写照。在《饮酒》(其九)中,陶渊明写到在归隐之后,善良的田父携酒来访,“壶浆远见候”,直言他不能寄身于“褴缕茅檐下”,劝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让他随波逐流,但他断然拒绝田父的好意,“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安贫乐道的意思是显见的。他在《饮酒》(其十)中也写到常为“似为饥所驱”,身上“少许便有余”,所以贫穷是他的常态,但他并不以此为意。他在《饮酒》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揭示了自己的生存境遇:“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其十五)“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其十六)住处荒草疯长,淹没了房屋,这显然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只有飞鸟为伴;因为“竟抱固穷节”,所以“饥寒饱所更”,诗人一直备受饥馑与寒冷的折磨。粗衣、少食、饥饿、北风、荒草,这些就是诗人生活的境况。
清贫的生活固然与金钱紧密相连,但这里的清贫还指生活的简单。陶渊明在《饮酒》(其五)中曾描绘了他归隐之后的生活图景——地处偏僻之境,没有车马的喧闹,日常生活是采摘菊花、闲看南山,视飞鸟结伴而还,从“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中我们能看出陶渊明淡泊宁静、满足欣喜的心绪。在《饮酒》(其七)中,秋菊佳色,助人酒兴,诗人一杯又一杯地喝着,此时“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日落之后各类生物都已歇息,归鸟也欢快地回来了,他喝酒赏菊,满足地看着这一切,不由纵情欢歌于东窗下,姑且逍遥度此生。两首诗中,无论是东篱采菊,还是对菊畅饮,诗人的生活都极其简单,但简单中有诗意,诗人营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氛围,这种浑然天成的满足感让他可以暂时忘记外界的纷扰,这也正是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对陶渊明的评价,如入“无我之境”。
既然选择了归隐,选择了不与世俗同流合污,选择了不为五斗米折腰,那么对于陶渊明来说,生活自然就与清贫相连。在《饮酒》(其八)中,陶渊明以青松自喻,感慨虽然被众草遮蔽,虽然有寒霜相逼,虽然经常被寂寞所困,但“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只要有酒,为什么要被尘世所羁绊呢?
《饮酒》(其十九)可以说是陶渊明自己安贫乐道的人生总结。虽然诗人一直以来,“畴昔苦长饥”,被饥饿所困,又被寒冷所逼,“冻馁固缠己”,但心里想着的是一定要保全坚贞气节,归去终老田园,“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如今十二年已经过去了,这一切都不算什么,“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对于陶渊明来说,人生短暂,应顺从自己的内心,坚守自己该坚守的,在清贫、简单而自由的生活中聊度余生,未尝不是人生幸事。
三、“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其一)——豁达乐观的思想境界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战争迭起,朝不保夕,置身于这样的社会中,对于生死问题诗人是坦然面对的。陶渊明的生死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庄子在《大宗师》中提出了“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2]127的说法,并认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2]133。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陶渊明认为“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3]。面对死亡,陶渊明不畏惧、不惊慌,无喜于生,无畏于死,反而以一种豁达乐观的态度来面对,正如他所说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esW6Inef2vieeLslyrNDPA==(《归去来兮辞》),他最终期待的是天人合一的境界。
在《饮酒二十首》中,“酒”便成为陶渊明展现自己豁达生死观的重要意象。组诗虽然只有九篇直接写到酒,但各篇都是酒醉后的感想,可以说是陶渊明豁达乐观生死观的总体呈现。陶渊明在诗前序文中说明作诗缘起:“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其中的“自娱”“欢笑”等都体现了陶渊明达观的饮酒思绪。在《饮酒》(其一)中,陶渊明这样写道:“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陶渊明认为世事无常,衰荣无定,事物总是在相互转换,有衰就有荣,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就像邵生不能长久富贵一样,草木也不可能长荣不衰。在陶渊明看来,人生短暂,死死生生、生生死死有如季节移迁,重要的是任情适性,解悟生命之奥义,这样才不枉一生。一旦领悟到了这个道理,乐观的人自然会明白,不会自寻烦恼。陶渊明在这种感悟之下,选择不自寻烦恼,选择与美酒相伴,随意地带上一壶酒,想喝就喝,日夜开怀畅饮。因此,“乐知生”可谓是陶渊明生死观的重要体现。
在《饮酒二十首》中,陶渊明不止一次地书写饮酒的乐趣,而不是“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范仲淹)。陶渊明常有的饮酒状态是“乐饮”与“醉饮”:“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其一),这是日夜畅饮的欢乐;“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倾”(其七),这是对菊痛饮的洒脱; “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其十三),这是醉饮的意境;“数斟已复醉”“殇酌失行次”“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其十四),这是醉酒的意味,等等。当然,面对现实,陶渊明胸中已经郁结了过多的忧愤,不用“行乐”的办法来驱散它,又怎能安心于隐居生活呢?
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十二),陶渊明正是有着对生的达观认知,所以对死亡的认知显然是极其理性的。在《饮酒》(其十一)中,陶渊明这样写道:“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意思是说人死后并不知道什么,只要能称心就好,所以即便是裸葬也没什么不好,“裸葬何必恶,人当解其表”,在洞穿了生死之后,去路便不再可怕。陶渊明在《还旧居》中写道:“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只要有酒,对于陶渊明来说死亡也可以是不以为然的。所以,梁启超曾这样评价陶渊明:“若文学家,临死时,从从容容,视化如归,临凶若吉的留下几篇有理趣之作品,除陶渊明外象没有第二位。”(《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袁行霈先生也说:“他饮酒是饮出了‘深味’的,他对宇宙、人生和历史的思考所得出的结论,他的这些追求那种物我两忘的境界,返归自然的素心,有时就是靠着酒的兴奋与麻醉这双重刺激而得到的。”[4]1-2
陶渊明一生爱酒,他在最后以酒入诗的《拟挽歌诗三首》中竟然说“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对于陶渊明来说,“酒”可谓是一生所爱,而他以酒入诗,用“酒”意象的设置增添了诗歌的诗意与意境,深刻展现了他的生命哲学。袁行霈先生曾说:“陶渊明的诗,不论是哲理性的,或者是抒情描写之作,常常透露着他特有的观察宇宙、人生的智慧,许多诗都可以看作一位哲人以诗的形式写成的哲理著作。”[4]114毋庸置疑,《饮酒二十首》正是这一类诗歌的杰出代表,陶渊明的“酒”意人生就是他的诗意人生。
参考文献:
[1]陶渊明.陶渊明集[M].逯钦立,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2]成玄英.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龚斌.陶渊明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511.
[4]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作者简介:柯昱仰(2004—),女,汉族,浙江淳安人,本科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