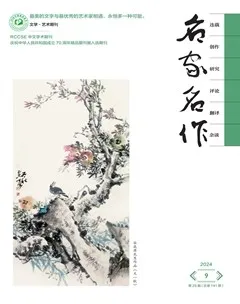《宋文鉴》所收录陈师道散文校勘拾遗
[摘 要] 南宋吕祖谦所编纂的《皇朝文鉴》收录了北宋文学家陈师道的不少散文作品,当代学者齐治平先生在对该书点校时将原书名改为《宋文鉴》,并对其中收录的陈师道作品做了校勘,但主要是参考了《皇朝文鉴》流传至今的宋明版本,对于陈师道文集参考不多,所以在校勘方面有不少遗漏。点校者存在因文字形似而致误、因不明古代地理水文或不熟悉典籍内容等而导致误标误断等方面的情况,参考陈师道文集的南宋版本,再加上其他文献作为旁证,对陈师道相关散文的失校误校加以拾遗补缺。
[关 键 词] 《宋文鉴》;陈师道;《全宋文》;校勘
中华书局出版的由当代学者齐治平先生点校的《宋文鉴》,是南宋时期文学家吕祖谦奉宋孝宗赵昚之命编选的。吕祖谦收集了当时众多的公私藏书,花费一年多的时间,最终成书一百五十卷。在这本书编纂完成之初,赵昚即命人传谕:“令专取有益治道者。”等到书成奏进皇帝,受到赵昚嘉奖,并赐名为《皇朝文鉴》。这显然是有意模仿北宋神宗赵顼赐名司马光编纂史籍《资治通鉴》的故事,由此可见此书的内容及其宗旨。
在齐治平点校本《宋文鉴·前言》中提到校勘此书的基本方法:“此次整理本书,以《四部丛刊》影宋本《皇朝文鉴》为底本,这是现在通行的最早最好的本子。……因此在校勘时,主要以《文鉴》(《皇朝文鉴》的省称)各本互校;遇到有疑难之处,再取各文作者本集及他书参校,将异文写入校记,对原文尽量不加以改动,以存《文鉴》之真。”[1]5-6从以上引文可知,齐氏点校本《宋文鉴》采用的底本“是现在通行的最早最好的本子”,从版本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比较稳妥可靠的;校勘的方法采用的是 “互校”和“参校”,方法上也是比较科学可取的,目的是使《宋文鉴》成为一个比较完善可读的本子。因为《宋文鉴》一百五十卷收录的文章比较丰富,再加上点校者参校的别集不足,所以在校勘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遗漏。笔者以《宋文鉴》所收北宋文学家陈师道散文的点校为例,加以拾遗补缺,以求教于方家。
根据《宋文鉴·前言》中提出的“参校”方法,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对《宋文鉴》所收录陈师道散文校勘的拾遗。
一、因文字形似而致误
中国古代的典籍,无论是传抄,还是雕刻前代文献,抑或是采用活字排印,总是抄刻排印一次便多一次发生错误的机会。同时,中国古代的文字多,字形相近或相似的字也多,抄写刻录的时候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错误。
《宋文鉴》卷第七十五收录陈师道《孔北海赞》:“子曰:‘枨也欲,焉得刚?’刚者所以制欲,非胜人也。是故自用之谓英,自胜之为彊。”[1]1091齐治平所作校勘记:“为彊,‘彊’原作‘疆’,据明刻本改。按,疑当作‘雄’,方与上文相应。”此处原作“疆”,据明刻本改为“彊”,使用互校法,应该是正确的,可从。
但是,齐氏所作按语“疑当作‘雄’,方与上文相应”是错误的。齐氏根据的是上下文意的对应关系,采取的是理校法,认为应该修订为“自用之谓英,自胜之为雄”。这样修订后的文字,从形式上来看既有上下句式方面文字整齐的对应,又有“英”与“雄”字义相近的对应关系,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合理,实际上缺少版本与文字使用方面逻辑上的证据。除了齐氏校勘记所提及《宋文鉴》明刻本此处‘疆’作‘彊’,我们还可以参校陈师道文集宋刻本《后山居士文集》。据徐小蛮《陈后山集版本源流考》一文介绍:“《后山居士文集》二十卷,也刻于蜀中,是现在最早的陈师道诗文集。编者不知何许人,他把魏衍本所不收而流传在社会上的陈师道诗文一并编了进去。卷首有谢克家作于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的序文。书中避讳至‘慎’字,刻于孝宗时期。”[2]曾枣庄和刘琳主编的《全宋文》点校本有陈师道文集,其所依据的版本就是南宋刻本《后山居士文集》,而《全宋文》所收《孔北海赞》记载:“是故自用之谓英,自胜之为彊。”[3]4 此处的“彊”字也作“疆”。另外,“自胜之为彊”,此处在修辞上明显是用典,语出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强”与“彊”二字相通,可参考《康熙字典》所收“彊”字释义第四条:“又《集韵》:‘胜也。’《尔雅·释诂》:‘当也。’《注》:‘彊者,好与相当。’《史记·商君传》:‘自胜之谓彊。’”[4601a0a3cae6751df1c1bdfdb9afb92449b2d0560e34deb199fe9b0d7da3c0eca] 《史记·商君列传》原文如下:“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彊。”“自胜”句用词也应该是来源于《道德经》。
综上所述,齐氏校勘记所提及《宋文鉴》的明刻本此处‘疆’作‘彊’而校改,为是;其下所做的按语“疑当作‘雄’,方与上文相应”仅仅是推测之辞,缺少版本和文献学方面坚实的证据。
《宋文鉴》卷第七十三所收陈师道《黄楼铭》:“下顾城中,井出脉发,东薄两隅,西入通洫,南懷水垣,土恶不支,百有余日而后已。” [1]1061此处的“南懷水垣”,《全宋文》中作“南壞水垣。”[3]2“懷”与“壞”因为形近而误用,《宋文鉴》此处失校。从上下文意来看,因洪水泛滥进入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中,水势比较大对水垣产生了很大的破坏性,所以“壞”字为是。据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所收“壞”的义项,此处的意思是“倾圮,倒塌”。这个义项所列举的例征如下,《诗·大雅·板》:“无俾城壞(坏),无独斯畏。”《韩非子·说难》:“宋有富人,天雨墙壞(坏)。”汉王充《论衡·偶会》:“壞(坏)屋所压,崩崖所坠,非屋精崖气杀此人也。”唐鲍溶《隋宫》:“炀帝春游古城在,壞(坏)宫芳草满人家。”
二、《宋文鉴》文本与其他书文字不同,可以保留校勘异文
陈师道(1052—1101)是北宋中后期一位影响较大的文学家,所以他的散文作品被收入《宋文鉴》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除了《宋文鉴》这样一代文学总集的选录,陈师道作品还有《后山居士文集》这样的别集流传后世,由于版本来源不一,抄写雕刻者的水平有高下,二者虽然收录的篇目一样,但是存在不少异文,这也是正常的文学版本传播现象。
《宋文鉴》卷第十三所收《黄楼铭》:“诚乐君臣之尽道云。臣不佞,冒死上《黄楼铭》。”[1]1061《全宋文》此处为:“诚乐君臣之尽道云。忘其不佞,冒死上《黄楼铭》。”[3]3“臣不佞”和“忘其不佞”有明显的异文,此处《宋文鉴》失校。如果从上下文意来推断,似乎“臣不佞”与上下文衔接得更好,语气方面更能彰显出下臣上奏天子时的卑谦之辞。
《宋文鉴》卷第八十四收录的陈师道《汳水新渠记》原文是:“汳水如箫,其阙如玦。”[1]1194 《全宋文》中为:“汳句于萧,其阙如玦。”[5]“汳水如箫”与“汳句于萧”两句,文字差别比较大,此处齐氏《宋文鉴》失校,笔者也不能确定以哪个版本所收录文字为是。
《宋文鉴》卷第九十一《茶经序》:“陆羽《茶经》,家传一卷。……学者谨之。”[1]1288-1289《全宋文》卷第二六六六所收录为:“陆羽《茶经》,家书一卷。……学者慎之。”此段文字有两处异文,齐氏《宋文鉴》失校。一是“传”字作“书”,未明孰是;二是“谨”字另作“慎”字,二字意思相近,对文章的理解影响不大。
三、因不明古代地理水文或不熟悉典籍内容等而导致误标误断
后人对前代典籍进行整理刊刻时会出现误标误断的现象,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前人对此多有论述说明。例如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杨树达《古书句读释例》、王迈《古今标点例析》、段喜春《古书标点释例》等专著中都有归纳总结,并举例子加以说明,此处因文章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宋子然《中国古书校读法》在“文言断句标点与校读古书的关系”中提出:“纠正前人断句标点失误必须运用校读的方法。前人断句标点失误原因很多,概括起来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误解致误;二是失校致误。因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标点断句失误都要用校读方法去验证,去纠谬复真。那就是依本书之句例,寻一书之义理,得书中的谬误,并参校他书相关的异文互文,综合判断,以求得正确的标点断句。”[6]宋子然先生在书中提出的断句标点失误原因和校读方法,笔者以为同样适合于《宋文鉴》中陈师道作品的校读。
《宋文鉴》卷第八十四收录陈师道《汳水新渠记》:“《水经》谓河至荥阳,莨荡渠出焉。渠至阳武,其下为沙,蔡水是也。其出为阴沟,沟至浚仪,其下为渦,别为汳。汳至蒙,别为获,余波迤于淮阳,东历萧、彭城,入于泗。《注》谓鸿沟、官度、甾、获、丹浚,与渠一也。”[1]1194此文中“《注》谓鸿沟、官度、甾、获、丹浚,与渠一也”断句有误,其中“甾、获”不当断而断,应该为“甾获”;“丹浚”当断而未断,应该标点为“丹、浚”。《全宋文》中这一段文字标点断句为:“《注》谓鸿沟、官度、甾获、丹、浚,与渠一也。”[5]这样处理断句应该是正确的,理由如下:
其一,“甾获”处不应该断开。“甾获”在《水经注》中有时称“甾获”,见下文《水经注·获水》部分引文。有时亦作“菑获”,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汳水》:“汳水又东,龙门故渎出焉。渎旧通睢水,故《西征记》曰:龙门,水名也。门北有土台,高三丈余,上方数十步。汳水又东迳济阳考城县故城南,为菑获渠。”[7]556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知道,“菑获”是“菑获渠”的省称,是《水经注》中记录的水道名,自然不能断开。“甾获”与“菑获”是相通的。
其二,“丹浚”当断而未断。“丹”和“浚”都是河流的名称,二者并列,所以应该使用顿号加以断开。郦道元《水经注·获水》:“《汉书·地理志》曰:获水首受甾获渠,亦兼丹水之称也。《竹书纪年》曰:宋杀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又曰:宋大水,丹水壅不流。盖汳水之变名也。”[7]559又见《水经注·汳水》:“阴沟即蒗荡渠也。亦言汳受旃然水,又云丹、沁乱流,于武德绝河,南入荥阳合汳,故汳兼丹水之称。河、济水断,汳承旃然而东,自王贲灌大梁,水出县南,而不迳其北,夏水洪泛,则是渎津通,故渠即阴沟也,于大梁北又曰浚水矣。”[7]555从以上引文可知,“丹”是“丹水”的省称,“浚”是“浚水”的省称,在此处二者不能连用,点校时应该使用顿号隔开。
《宋文鉴》卷第九十一《茶经序》原文记作:“家书近古,可考正。自七之事,其下亡。”[1]1288其中的“七之事”,是唐代《陆羽》原书中拟定的小标题,应该加上双引号。今天的传本与陈师道所见“毕氏、王氏书三卷”的分卷相同,卷上为“茶之道”“茶之具”“茶之造”,卷中为“茶之器”,卷下为“茶之煮”“茶之饮”“茶之事”“茶之出”“茶之略”“茶之图”。从中可以发现,“茶之事”正好排在第七位,陈师道所见的《茶经》,第七篇应该是“七之事”,没有这个“茶”字。今天的大多数《茶经》点校本多出了“茶”字,并非《茶经》的原版格式。原因在《茶经·续茶经》中有明确的解释:茶之源,即茶的源。陆羽《茶经》中的这个小标题,原来没有“茶”字,清代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将《茶经》收入,并在各小标题中增加了“茶”字。这样,从“一之源”至“十之源”便成了“一茶之源”至“十茶之源”,这是清代以前的各种《茶经》版本中未见过的。[8]《宋文鉴》比较全面地收集了上古至唐代有关茶的历史文献资料;大体上是按照年代编排的,这为后人研究茶的历史提供了不少方便。
因为点校者对词义的误解或对古代典籍的内容不熟悉,所以校勘时导致以上几处误标误断或者失校。
王瑞来先生在《万般无如校书险》一文中写道:“万般云云,所指并非世间万般,而是泛指为学而言。常为校书之业,时正鲁鱼亥豕。前人有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不仅旋扫旋生,每校一过,也往往会发现失校之处,漏网之鱼。”王先生的感慨可算是校书者的知音之叹,笔者对《宋文鉴》校勘的拾遗补缺,可算作该书点校者的“漏网之鱼”。
参考文献:
[1]吕祖谦,编.齐冶平,点校.宋文鉴[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徐小蛮.陈后山集版本源流考[J].文献,1984(1):168-178.
[3]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24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4]张玉书,等.新修康熙字典:上[M].上海:上海书店,1988:476.
[5]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23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370.
[6]宋子然.中国古书校读法[M].成都:巴蜀书社,1995:404.
[7]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陆羽,陆廷灿,著.志文,注译.茶经·续茶经[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4.
作者单位: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南通分校区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2020年哲学社会科学一般性课题“陈师道散文选注”(项目编号:2020SJA077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韩留永(1978—),男,河南郾城人,文学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唐宋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