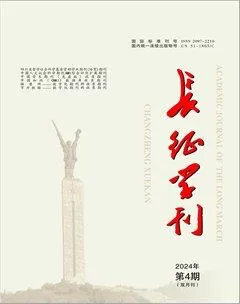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川西北地区开展文化教育工作的实践及现实启示
摘 要:本文着眼于长征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梳理红军在川西北地区16个月期间开展文化教育的史实。通过文献研究和史料分析发现,中国工农红军为了教育广大指战员和当地群众,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教育活动,包括制定符合民族地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开办红军大学、培养适应复杂环境的各类人才、教育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创造了在民族地区和极端环境下开展文化教育工作的实践模式,给今天复杂形势下更好开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工作带来了历史的经验和启示:文化教育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文化教育工作必须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展开;文化教育工作必须以民族团结进步为题中应有之义;文化教育工作必须立足实际、开拓创新;文化教育工作必须将培养优秀少数民族地区干部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关键词:长征时期;阿坝地区;文化教育;现实启示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7-2210(2024)04-0048-11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工作,并将文化教育作为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方法。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出台的文化教育工作总方针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1]。党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cf7quQuzLz88j+Z7kdldRQ==,“除了受到特定的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制约外,又由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地域性与超地域性的特征,使它还要受到所在区域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2]。红军长征在川西北地区那段艰难困苦的时期,党的文化教育工作也不曾中断,它既延续了党在苏区进行文化教育的经验,又对民族地区和极端环境下如何开展文化教育进行了探索。梳理党在川西北地区开展文化教育工作的实践,总结其成功经验,对于今天攻坚克难、凝心聚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党在川西北地区开展文化教育工作的实践探索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自1935年4月到1936年8月,在川西北地区往返、停留达16个月。川西北地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松理茂汶屯区的别称,即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所辖境域。参见中共阿坝州党史研究室、阿坝州地方志办公室:《阿坝州志之红军长征在阿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在这里,中国工农红军以其艰苦奋斗的革命实践,在川西北地区谱写下了壮丽的历史篇章。
红军长征在川西北地区的这段行程,是整个长征过程中最为艰难困苦的一段历程参见朱成源:《长征在雪山草地》,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序言。
:频繁的战事、严酷的自然环境、绝地断粮的威胁、激烈的党内斗争、国民党的蛊惑宣传、语言的不通,等等。尽管如此,党的文化教育工作不仅没有中断,相反,为适应川西北地区特殊的民情和斗争环境,党在文化教育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和探索。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可以发现党在川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工作既有面对红军队伍内部,也有针对地方群众的教育。红军内部宣传教育主要有:党在民族地区的政策、纪律要求、工作方法,适应高原生存的经验、做法,针对高原骑兵作战的技能、方法。地方教育则侧重: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揭露国民党和四川军阀的反动本质,号召川西北地区各族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实现民族自决。形式上主要采取:
(一)制定符合民族地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为红军指战员提供工作遵循
进入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后,如何破除国民党散布的谣言,赢得各族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增强战胜严酷自然环境及适应新的作战形势的本领,关系红军能否胜利走出雪山草地,关系革命事业成败。为此,党要有明确的民族地区工作的思路和方向。开展文化教育就是民族地区革命工作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红四方面军即将攻克土门封锁线进入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时,为使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有所遵循,1935年5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西北特区委员会下发了《西北特区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提出每一个工作干部和战士在对回、番民族工作中必须注意的10条工作要点,即每一个工作干部和战士,必须了解回、番民族情形状况;要学会回、番民族的语言文字,遵守他们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向回、番民购买物品要公买公卖,照货给价;向回、番民家中借用用品,应经过他们许可后才准借走,用完应迅速交还;到回、番民家中不准乱动其一切物件,如拿草、下门板、拿水桶、锅、碗等;对回民清真寺应遵守他们规矩,不准随便进行东摩西搞,一切要切实遵守他们风俗习惯;对回、番妇女更要绝对遵守他们礼节。[3]1935年5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又专门发出给中央红军各军团政委、政治部的《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其中强调:“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的关联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因之,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4]并要求各军团政治部必须向全体战斗员解释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及其必须注意的事项。这些工作要点明确而具体,没有深奥的理论,就是对一些日常中的细碎事情提出要求,在广大红军指战员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便于理解,也便于红军指战员操作和执行。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中共中央到达卓克基(今阿坝州马尔康市马尔康镇)。1935年7月3日,在卓克基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以下简称《纲领》),其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解放被压迫的各少数民族,并积极帮助一切革命的民族建立自由选举的革命政府,同时号召藏族民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成立游击队,加入红军,实现民族自决。”[5] 《纲领》就成为广大红军指战员在川西北民族地区开展民族工作及与少数民族群众交流交往的根本遵循。
党中央停留黑水期间,根据卓克基会议精神,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红军必须遵守六条纪律》的命令,要求全体红军指战员严格执行此命令,对严重违反纪律者及时进行处理。[6]
党中央到达松潘毛儿盖地区后,又在沙窝会议上通过了《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提出:在部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军事政治训练、严紧纪律、加紧阶级教育等12项中心工作,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1935年8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巴西(班佑)常委扩大会议上,又专门研究教育和宣传问题。会议决定:近期尽可能出一至两期《干部必读》,同时建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博古、凯丰、杨尚昆、李维汉担任委员。[7]对于这些会议精神和纲领性文件及工作要求、指示,各部队都会进行认真传达,教育引导广大红军指战员明确如何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明确党的群众纪律和工作要求是什么等问题。通过这些文化教育工作,红军指战员在行动上就有了准则和方向,工作成效也十分明显。
(二)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提升红军指战员的斗志和勇气
从1935年4月底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后,条件变得更加艰苦,饥饿、寒冷、高原不适随时威胁着红军的生命,语言不通、群众敌视、土官土兵袭扰等因素增加了开展文化教育工作的难度。但红军领导机关仍然通过组织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来教育激励广大红军指战员,特别是培养坚定的理想信念、大无畏的思想境界、乐观的革命情怀。中央红军的军人俱乐部和猛进剧团,红二、六军团的战斗剧社和红四方面军的工农剧团的战士们不畏艰险、不惧困难,以艺术为刀枪,与其他的红军战士并肩战斗。
红军文艺工作者在川西北地区开展的文化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红军文艺工作者将党在川西北民族地区的政策要求、纪律规定、工作方法、注意事项编成顺口溜、快板或浓缩成一些简捷、响亮的口号,边行军边吹、拉、弹、唱进行宣传教育,由于朗朗上口,容易记忆,又寓教于乐,党的重要决策精神很快就传达给每一位战士。同时,由于表演灵活生动、妙趣横生、不拘一格,从而使广大指战员在笑声中忘却疲劳、忘却饥饿、忘却伤痛,激发了革命豪情,提高了革命斗志。
到了宿营地,红军文艺工作者经常会组织一些“同乐会”“对歌会”,用山歌、民谣调子,依据感受、情景,即兴对歌。这类“同乐会”“对歌会”在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中最为流行,以战士们喜爱的形式和充实革命的内容,在给广大红军指战员枯燥而艰辛的生活增添无穷乐趣的同时,还起到了互相激励、统一思想的作用。
在红军部队停留较长的地区,红军文艺工作者往往把工作深入到连队和地方群众中去。他们搭台表演,为前方战士和地方群众送去欢笑,与当地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比如,红军在茂县,每当红军进行宣传演出时,街头、场口、村寨的坪坝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们竞相观看。就连反动派统治下的一些报刊也不得不发出慨叹说:红军在茂县城里,每夜与民“相混聚市,六街灯火如上元。……在城隍庙大打大豉,大演其平民剧”[8]。又如,红军在汶川的威州,除演出历史戏“乌泥河救驾”“樊梨花”“干妈问别”等外,还演出一些以邓(邓锡侯)、田(田颂尧)、刘(刘文辉)等军阀及其家庭丑闻为题的活报剧。[9]如,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今阿坝州小金县)会师后,红一、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和懋功城内的人民群众,举行了盛大的联欢晚会,分别在营盘街较场坝(今小金中学所在地)、城内四方台子(今小金县人民医院所在地)及城隍庙(今小金县幼儿园内),演出了丰富多彩、富有战斗性的文艺节目,如“火线”“猛进”剧社的歌舞,还有“太阳纵队”演出的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为题材的节目。 [10] 在今天阿坝州的茂县、汶川的雁门和威州、理县杂谷脑和薛城、小金、金川、马尔康等地,都留有红军巡回演出的遗迹。
结合党在川西北地区的中心任务,广泛运用民歌、山歌形式谱写歌词进行宣传、动员、鼓劲;运用活报剧、话剧、川戏揭露敌人,教育红军指战员和群众,是长征期间红军文艺工作者的主要工作。比如,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后,军事上要与反动土司、头人组织的骑兵作战,生活上物资极端匮乏,战士们又不适应当地饮食习惯。为了帮助各部队克服这些困难,让战士熟悉打敌人骑兵的战术,尽快适应高原生活,红军文艺工作者创作了《打骑兵歌》和《吃牛肉歌》。《打骑兵歌》的歌词是:“敌人的骑兵不须怕,沉着敏捷来打它。目标又大又好打,排枪快放易射杀。我们瞄准它,我们消灭它。我们是无敌的红军,打垮蒋匪百万兵。努力再学打骑兵,我们百战要百胜。”[11]《吃牛肉歌》则写道:“牛肉真是个好东西,吃了养身体。不会错,是真的。吃了牛肉浑身有力气。爬上雪山,走过草地;练好本领,上前杀敌。”[12]将战术要领和改变饮食习惯的内容寓于歌曲之中,教红军指战员们学唱,大家既掌握了高原作战、生活技能,又学会了歌曲,增添了生活乐趣。再如,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达维,陆定一用《二次全苏大会歌》的曲子,填写了《两大主力会合歌》的词,歌词内容为:“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欢迎红四方面军百战百胜弟兄,团结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力量,哎!团结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力量,坚决争取大胜利!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来伟大的会合,为着奠定中国革命巩固的基础,哎!为着奠定中国革命巩固的基础,高举红旗向前进。”[13]词意激越,气势磅礴,充分表达了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喜悦之情。在广大红军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红军尽管面对极地考验、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堵、断粮威胁,却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昂扬的斗志。
(三)建立红军大学,培养适应复杂环境下斗争的各类人才
红军长征在川西北地区期间,除了平时以连为单位组织干部、战士进行日常的文化学习、军事技能训练和接受军事政治教育,针对新的工作、战斗实际情况,红军还建立红军大学,进一步提高指战员的军政素养,培养各类适应复杂环境的军政人才。
1935年8月上旬,根据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关于“设立红军大学与高级党校,大批的培养军事的与政治的干部”[14]的决定,将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合编,在松潘毛儿盖建立了新的红军大学。新组建的红军大学校长为倪志亮(未到职,由共产国际代表李德负责),何畏任政委,黄超任秘书长,李特任教育长,莫文骅任党总支书记,刘少奇任政治部主任(未到职)。红军大学设有指挥科、政治科、步兵科、工兵科、炮兵科及骑兵科等专业。指挥科和政治科的学员主要是营以上干部;步兵、工兵、炮兵科的学员主要是各军选送的优秀基层干部(班、排、连)和战士。
红军大学成立后,由于即将北上过草地,学员们学习时间并不多,只进行了有关战术、图上作业等方面的教学,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筹粮及过草地的准备工作上。
为了执行党的北上战略方针,根据沙窝会议的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主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红军大学被编入右路军系列,随中央和前敌指挥部行动。中央组建的红军大学从1935年8月成立到9月10日巴西分开,仅仅只存在了一个月时间。由于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北上路线,仍然顽固地坚持其“乘势南打”的错误主张,红军大学被迫分家,原一方面军学员和部分红四方面军学员随中央北上,在中央抵达哈达铺后又恢复了干部团建制。红军大学其余学员未跟随中央北上,而是在李特等人的率领下南返二过草地,经巴西、毛儿盖、马塘、卓克基等地,于10月初到达松岗(今阿坝州马尔康市松岗镇)。
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加紧进攻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为培养军、政干部,提高各级干部的军事政治水平,以便适应抗日救国的需要,经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提议,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10月9日恢复了红军大学。这时期的红军大学,刘伯承兼任校长,何畏任政委,张宗逊任参谋长,王新亭任政治部主任。下设三个专业科:高级指挥科,张宗逊兼科长,吸收军、师级干部学习;上级指挥科,科长周子昆,吸收营、团级干部学习;上级政治科,科长彭绍辉,吸收营、团级干部学习,学制均为三个月。
红军大学的教育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全面培养干部。”[15]教学方法采用“教员讲课多示范,学员学习多操练”[16]。课程设置有政治课、军事课和文化课。军事课教学多联系实际,要过雪山时就讲雪山气候变化规律、高山行军、宿营等方面的知识,并发动学员总结之前爬雪山经验。讲对高原骑兵作战的战术时就联系之前对骑兵作战的经验,尤其是刘伯承亲自教授学员“排枪快放”的打法,还把它编成打骑兵的战术教材,供学员学习。红军大学测绘教员赖光勋带着高级指挥科学员在沙尔尼村外的河边教测绘略图,他讲完“测距”内容后,一位学员提出:我们要知道大金川河水面多宽,请教员测给我们看看。赖光勋边讲边做,他说:测距离有步测法、三角交会法、三角光线法等,要测这条河的水面宽度,可用三角光线法。他将北面的独立树作为河东水面的边缘,二者之间为河的水面,运用三角光线法,宽度就测出来了。赖光勋请学员们用尺去量,他们返回后说“距离一样”。又有一个学员提出让赖光勋测一座山的高度给他们看,赖光勋就借助喇嘛寺房顶为基准点,用水准仪测了一下,经过计算,告诉他们高度,又让学员用绳子去量,得出的结论又是一样。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易于学员接受,效果十分明显。
政治课教学更是把红军对少数民族政策和做好驻地群众工作紧密结合。在沙尔尼村时,有一首民歌唱道:“兵占平,民占坡,蛮家住在山窝窝。”[17]这首歌反映了旧中国我国少数民族在大汉族主义压迫下的苦难生活。在一次军民联欢会上,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从这首民歌谈起,他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穷苦人民的军队。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欺负兄弟民族。中国各族人民都是在一个国家、一块土地上生活的兄弟姐妹,是一家人。[18]王新亭的讲话得到参加联欢会群众的拥护,对红军大学的全体学员也是一次很好的政治教育。
然而,红军大学开学上课不足10天,即奉命随军沿大金川西岸经丹巴东渡大金川河,翻越夹金山南下。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大学编入中路军,随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由炉霍出发,经色达、壤塘、毛儿盖、巴西地区,三过草地北上,教学也就相应结束。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12月,红军大学的高级指挥科、上级指挥科、上级政治科调到保安与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合并为抗日军政大学。红军大学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它的教学内容贴合实际,教学重点突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对军政干部提升高原作战、高原行军技能,正确与民族地区人民打交道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红军大学还在战斗极为频繁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采取边打边教学的灵活方式,这种情况在陈伯钧的日记中清晰可见:“10月15日,阴,黄昏前风作。驻军中阿坝。第一堂上课。利用第二堂课时间,起草连的侦察警戒讲授提纲一段,并拟定第四周的操课表。下午野外演习,一连担任前队。下午,骑蛮又来阿坝附近骚扰,追捕我红大的马匹。结果被我学生击溃。”[19]“10月19日,晨霜,晴,下午大风。驻军中阿坝。上午上课,讲山地战的防御。下午在中、下阿坝之间演习山地战,连的防御。晚上演习夜间接敌运动及通信联络记号。演习中遇蛮骑三名,将其打走。”[20]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红军大学先后吸收各级学员达三千多人次,为党和红军培养了大批干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探索地方文化教育,培养少数民族革命干部
红军长征在川西北地区期间,除了对红军队伍自身的文化教育,还对川西北地区的群众也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文化教育活动。这种文化教育始于宣传工作,以消弭各族群众对红军的疑惧,同红军逐步接触,在此基础上,“发现和选择基层积极分子,送到县以上政权等组织举办的各种训练班或短训班学习、培养,使其成为当地基层组织的骨干和领导力量”[21]。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中向各军团、政治部提出:“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政治部对于这些份(分)子在生活上、政治教育上都应加以特别的注意。在人数较多时,应成立某个少数民族的单独的连队,并特别注意与培养他们自己的干部。”[22]沙窝会议决议也明确指出:“必须挑选一部分优良的番民给以阶级的与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23]为了使更多的人熟悉中国社会状况,实现民族地区的独立与解放,建立川西北各族人民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壮大革命力量,红军建立了各种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机构,并举办短训班。比如,西北联邦政府内设有教育部,协助地方政权培训当地干部。再如,红军在茂县、绥靖地区都曾兴办过苏维埃干部训练班、军事训练班、格勒得沙学校等。“绥靖(今金川)建立了西北联邦政府的劳动学校,有140人参加了学习。格勒得沙中央政府在绥靖举办的藏人训练班,后改称为格勒得沙大学。中共大金省委党校也曾吸收过少数民族的地方学员”[24]。这些训练班或学校虽然没有正规教学计划,但都培养了大批干部和工作人员,何雨龙、沙纳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二、党在川西北地区开展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作用
长征时期,党在川西北地区开展的文化教育工作,为党和红军最终战胜国民党的围追堵截,经受住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胜利走出有“死亡陷阱”之称的茫茫草地,创造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增强了广大红军指战员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信心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灵活生动的文化活动的开展,激发了红军战士的革命豪情,提高了革命斗志。正如潘振武在《打骑兵歌》一文中所述:“事实证明,《打骑兵歌》及其舞蹈的推广普及,的确发挥了应有的效用。以后红军遇到骑兵,再也不会感到惊慌失措了,一阵排子枪打过去,打得敌人人仰马翻。”“敌人骑兵嚣张一时的凶恶气焰,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彻底地崩溃了。”[25]党在川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使一支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装备落后的人民军队汇聚起了磅礴之力,他们不畏艰险、不惧困难、勇于牺牲。美国记者斯诺对此毫不吝啬地加以赞美,“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仅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26]。所以,当年红军几万大军过草地,队伍拉得很长,路途中饥饿、寒冷、疲劳、疾病夺去了很多战士宝贵的生命,但红军走出草地就在包座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之后,更是一路凯歌到陕北,胜利实现了红军的伟大战略转移。
(二)提高了各级干部的文化素质和理论水平,增强了应对复杂问题的本领
长征时期,红军各级指挥员和干部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这从王波的《在雪山草地的红军大学》一文就能真实地反映出来,他在文中写道:“就我们高级指挥科的学生来说,除一位军参谋长陈天池同志读过几年小学、我读过一个月的高中外,其他同志都是一字不识的文盲。虽然他们在军事指挥方面都是身经百战、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指挥员、红色的战斗英雄,但都没有文化,好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或根本写不出来,还得从一、二、三、四、五学起。”[27]红军大学建立后,教授内容既有语文、数学、中外地理、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党史等文化知识,也有马列主义理论常识。由此,提升了红军各级指战员的文化素质和理论水平,使他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政策及红军纪律、军民团结等党在民族地区的政策要求,更好地推进革命事业发展。同时,面对川西北地区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少数民族善山地作战、善骑射的特点,红军大学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活动,提升了军政干部高原作战、高原行军技能,最大限度保存了红军有生革命力量。像许世友等许多党的优秀高级干部都是当时“红大”的学生,他们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极为宝贵的人才资源,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中坚力量。
(三)赢得了川西北地区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持和衷心拥护
《西北特区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红军必须遵守六条纪律》等文件下发后,广大红军指战员以此为尺,严格遵照执行,使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真正成为一支为国家民族人民利益而战,不同于任何旧政权旧军阀的新生力量,赢得了川西北地区各族群众真心的支持与拥护。川西北地区各族群众对红军由开始时的疑惧,到后来倾力支援。红军经过川西北地区时“各族人民先后支援的牛、马、羊、猪等各类牲畜总头数达20万余头,粮食2000多万斤”[28]。不仅如此,很多少数民族群众主动为红军当通司(翻译)和向导,给红军作宣传、想办法、出主意。比如,黑水藏族群众九十三曾亲自到深山密林中将红军的主张翻译给受蒙蔽而躲藏的藏民,动员他们返家,还帮助红军完成了在当地的筹粮任务。[29]这些工作为党和红军顺利走出雪山草地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和物质基础。
(四)革命真理播向了藏羌大地,鼓舞了川西北各族人民的革命士气,为长征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下,川西北地区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还组建了番民骑兵队、回民独立连、格勒得沙革命军、金川独立师等少数民族革命武装,一大批优秀的藏羌回各族儿女为争取本地区和本民族的解放加入其中,有一些人还直接参加了红军,壮大了革命力量。“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5月至1936年8月,在今阿坝州境域内参加红军的人数就达5000人以上。”[30]这些地方政权和武装力量发动群众为红军筹粮筹物,组织运输队、修路队、担架队配合红军作战,同红军一起与残酷的自然环境和凶恶的敌人殊死拼搏。比如,“为了配合、协助主力部队行动,红军南下时在大小金川地区建立的各级党政军和留守部队,积极发动群众,筹集了大批粮食、牛羊、柴草等军需品,修筑沿途桥梁,设置兵站,布置宿营地,并完成了运输物资,转移、护理伤病员等工作,有力保证了主力部队的顺利行动。”[31]总之,党在川西北地区开展文化教育工作的实践探索,唤起了当地各族群众的觉悟,鼓舞了当地各族人民的革命意志,发挥了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重要作用,为长征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三、党在川西北地区开展文化教育工作的现实启示
长征时期党和红军在川西北地区开展的文化教育工作,不仅为长征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也给今天复杂形势下民族地区更好开展文化教育工作以启迪。
(一)文化教育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文化教育工作离不开党的领导。长征时期的文化教育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坚持党对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把握文化教育工作的正确方向,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国家、民族荣誉感和认同感教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文化教育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团结奋进,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才能破解党和人民面临的各种危局。
(二)文化教育工作必须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展开
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展文化教育,是文化教育工作的生命力所在。长征时期,党在川西北地区开展的文化教育工作始终围绕“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最终取得长征胜利”这一主题展开。
从党的二十大开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2]。文化教育作为立心塑魂工作,就是要围绕这一中心任务进行思考、进行谋划,通过加强理论武装,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培育正向、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情趣等,真正形成国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合力,才能更好地推进各项事业发展,民族复兴才不会停留在纸张和笔端上。
(三)文化教育工作必须以实现民族团结进步为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休戚相关、命运与共,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族关系的深度分析与认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教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如今,面对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的分裂活动,如何教育民族地区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不盲目听信、跟随少数别有用心之人,既是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工作的使命与责任。通过建好民族地区文化教育阵地,深挖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教育素材,铸牢民族团结进步之魂,从而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成为民族地区群众自觉。
(四)文化教育工作必须立足实际、开拓创新
立足当地实际又开拓创新是文化教育工作有效开展的保障。川西北地区藏、羌、回、汉等多民族杂居,不同的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历史文化交织交融,思想文化更加多元多样,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复杂,因此,必须立足实际,创新文化教育的方式方法。特别是随着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深刻改变了川西北地区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教育工作也必须与时俱进。比如,灵活运用数字技术创新文化载体和文化样式,将川西北地区多彩的文化元素融入其中,丰富数字空间文化供给,以满足各族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让优秀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活”在当下,服务当代。真正使文化教育工作在新时代川西北民族地区发挥敲击灵魂、触动人心,引起共鸣、发人深省,激起斗志、凝聚力量的作用。
(五)文化教育工作必须将培养优秀少数民族地区干部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资源,是党实现民族地区社会长治久安、民族和睦相处、经济文化繁荣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川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干部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熟知当地的风土人情、社会发展状况、民族文化心理,他们容易与当地各族群众进行语言沟通、产生情感共鸣、拉近与当地群众的距离。同时,他们也更热爱自己的家园故土,工作当中会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情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33],川西北地区作为治边稳藏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区域和曾经的“三区三州”(指中国特定的深度贫困地区),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和谐共处,并与全省全国一道实现共同富裕的难度相对较大,选拔培养优秀的本地区民族干部就显得尤为重要。要充分发挥优秀民族干部在川西北地区各族群众中的动员力、组织力、引领力,以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1]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1页。
[2] 王予霞、汤家庆、蔡佳伍:《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3]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2页。
[4] [22]陈宇:《红军长征年谱长编》(中卷),蓝天出版社,2016年版,第848、849页。
[5] [7]徐占权、徐婧:《决策·存亡——长征中重要会议的解读》,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第161、195页。
[6]黑水县史志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黑水县历史》(1935—2012),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8] 中共阿坝州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中共阿坝州委党史研究室:《阿坝州党史研究资料》第5期,2015年版,第28页。
[9]中共阿坝州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中共阿坝州委党史研究室:《阿坝州党史研究资料》第1期,2015年版,第10页。
[10]中共阿坝州党史资料往集小组办公室、中共阿坝州委党史研究室:《阿坝州党史研究资料》第12期,2015年版,第14页。
[11][12] [13] [15] [16]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在四川》(修订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5、415、415、419、419页。
[14] [2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1、282页。
[17] [18]邓艺兰:《战争与红军史话》(史话金川丛书),开明出版社,2017年版,第82、82页。
[19] [2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1》,中央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70、171页。
[21] [24] [28] [29] [30]中共阿坝州委党史研究室、阿坝州地方志办公室:《阿坝州志之红军长征在阿坝》(一九三五年四月——一九三六年八月),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01、110、110、113页。
[25] [26] [27]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化局:《红军长征过阿坝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内部印刷,1996年,第346—347、序1—2、351页。
[31]朱成源:《长征在雪山草地》,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页。
[32]《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9—20页。
[33]《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新西藏》(汉文版),2020年第9期。
(特约编辑:文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