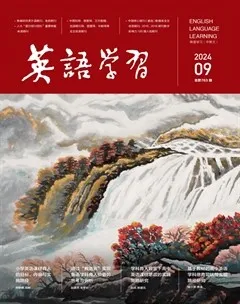释意理论在视译教学中的应用
引言
口译是一项历史悠久的职业,也是一种比文字诞生更早的翻译形式,在笔译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其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在中国夏商时期,就有人开始跨部落开展口译活动。到了19世纪,口译在欧洲逐渐兴起,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即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目前在欧洲,影响力最大的三种口译理论是释意理论、认知负荷模型理论和思维适应控制模型理论。达尼卡·塞莱斯科维奇和玛利雅娜·勒代雷是巴黎高等翻译学院的两位著名教授和翻译家,她们致力于探讨翻译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创立的释意理论在翻译领域掀起了轰动,为后人所广为熟知、学习和研究。该理论的核心要义在于,译员在口译时应避免被源语字面意思干扰,准确把握源语中的核心内涵,然后使用目标语清晰地表达出来,实现“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的翻译效果。释意理论对丰富口译理论和推动口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视译是指译员在没有任何听力输入的情况下,根据纯文字材料进行口头翻译。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将释意理论融入交替传译,从而实现源语字面意思与内在含义的有效转换。高璐璐和朱云翠(2013)详细阐述了译员如何通过释意理论,将源语的表面意思转换为表达深刻内涵的过程。沈雨(2013)总结了视译的特点及释意口译理论的核心内容,并探讨了该理论在视译中的具体应用。覃美静(2017)详细阐述了口译教学的四个关键方面(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师和学生)及口译教学的三大原则(沟通原则、认知原则和思维原则)。上述研究都强调释意学派理论对口译教学的启发和实际应用,但将释意理论与视译结合开展深入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本文将尝试探讨释意理论在英汉双向视译中的应用方法和运用技巧,旨在为口译研究、实践及教学提供有益参考。
释意学派理论
1968年,塞莱斯科维奇在她的博士论文《国际会议成员——言语与交际问题》中首次提出释意口译理论。从那时起,释意学派以巴黎高等翻译学院为研究中心,充分利用当时在应用语言学、篇章语言学、神经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领域以及其他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经过诸多学者多年、持续的深入研究,其理论建设日臻完善。
巴黎高等翻译学院的专家不仅致力于口译理论的研究,还重点关注如何将口译理论有效应用到口笔译教学实践中。1989年,塞莱斯科维奇和勒代雷合著《口译推理教学方法》一书,首次将释意学派的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到口译教学中,系统地阐明了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的原理、内容、步骤和方法。1994年出版的由勒代雷所著的《释意学派口译与翻译理论》在讲解口译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释意学派的翻译理论。基于这一理论,此书讨论了语言教学和翻译教学之间的本质区别,以及翻译教学与技能训练的关系,成为释意学派理论结合翻译教学的经典范例(覃美静,2017)。
勒代雷教授是释意学派创始人之一。她在《现代翻译——释意法》中详细讨论了“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的内涵。她强调在口译过程中,“脱离源语语言外壳”是连接理解源语涵义与重新表达目标语之间的关键环节。在这一阶段,译员省略语言的结构符号,从而更深入地理解源语内在涵义(高璐璐、朱云翠,2013)。
释意学派提出的经典口译理论中的“三角”模型如图1所示。这一模型包含理解源语、摆脱源语外壳和目标语表达三个阶段,首先,译者利用自己的学科知识、认知知识和语言知识,在接受源语言符号时建立源语的话语层次含义;其次,摆脱源语话语措辞的限制,即“脱离源语语言外壳”,记忆源语真正想要表达的信息内涵;最后,将源语信息转换成目标语,并发布翻译后的文本(目标语)(高璐璐、朱云翠,2013)。该模型打破了人们以往认知的“理解→表达”这一简单的思维方式,否定了翻译只是简单的代码转换的观念,强调了中间阶段的重要性,即在不受原文表达形式约束的情况下注重本义(许菲菲等,2015)。在口译过程中,“意义”的核心概念处于“三角”模型的顶端,显示出意义的形成在口译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意义属于非言语范畴,在说话者的口头表达和接收者理解文本之前就已经存在。理解含义需要结合非语言思维和符号迹象,而接受意义则需要接收者的行为是有意识的。语义单位仅存在于篇章层次,它们与固定短语中的单词、声音和意义片段的排列方式并不相同(勒代雷,2011)。

释意学派认为,涵义形成的首要步骤是理解原文意思。在口译过程中,译员首先需要理解源语言符号,然后经过语义和认知信息的整合,生成一个篇章性的意义片段,最后用目标语重新表达。比较原文会发现译文与源语言片段意义等效。
勒代雷在《现代翻译——释意法》中详细讨论了“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的内涵。她强调在口译过程中,“脱离源语语言外壳”是连接理解源语涵义与重新表达目标语之间的关键环节。在这一阶段,译员省略语言的结构符号,从而更深入地理解源语内在涵义(高璐璐、朱云翠,2013)。
视译原则和视译过程
从句子结构角度看,英语注重形合,汉语注重意合;英语重视语法结构的正确性,而汉语更注重表达的含义。因此,汉语显得更加灵活多变,即便一个汉语句子缺少关联词来明确内部逻辑关系,也不会影响人们理解该句的含义。因此在实践中,尽可能保持目标语与源语的词序一致是视译的第一原则。
在翻译过程中,句子的切分和断句非常关键,通常是根据“意群”,即在意思表达上相对独立的词组或短语来划分。句子通常是由多个意群相互组合而成,因此意群常被用作切分句子的标准。根据视译要求,句子中的意群可以根据以下三个特点进行划分:(1)具有相对独立含义概念;(2)在视线范围内;(3)通过巧妙运用连接词,使得前后的基本单位能够紧密结合(秦亚青、何群,2009)。
保持目标语与源语词序一致又称为“顺句驱动”,译员会根据源语的词序将句子分为不同的意群组或信息单元,然后通过选择合适的连接词自然、流畅地连接这些意义单元,最终口译成目标语。依据原句结构进行翻译可以提高翻译效率,减少译员在处理原文时的困难,避免消耗过多精力。
在视译过程中,译员首先通过视觉信息接受源语内容,然后利用所掌握的语言和学科知识深入理解源语。译者在理解源语含义基础上,以恰当的方式将源语信息翻译成目标语。
释意理论在英汉双向视译中的应用
若译员拘泥于字词本身进行口译,可能会造成译文佶屈聱牙,听众难以理解,导致口译失败。释意理论可以帮助译员“脱离源语语言外壳”,抓住核心意义,避免受制于文字形式。接下来,笔者通过真实的翻译案例,说明视译中译者如何将源语的含义从语言外壳中脱离出来,并用目标语重新表达源语内涵。
[例1 ]
原文:Three big uncertainties loom over the Rice State Department. The first concerns the new secretary herself. For four years, Ms. Rice has been a sounding board, tutor, and weather vane.
原译:三大不确定因素笼罩着赖斯的国务院,第一个因素与国务卿本人有关,四年来赖斯女士是传声筒、辅导老师和风向标。
改译:三大不确定因素笼罩着赖斯的国务院,第一个因素与国务卿本人有关,四年来赖斯女士传递信息、辅佐总统、指引方向。
原文中使用了隐喻,将美国国务卿赖斯比作传声筒和风向标。原译保留了修辞手法,直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但听众如果缺乏相应的背景知识,可能无法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根据释意理论,译员在口译中应“脱离源语语言外壳”,以准确传达传声筒、辅导老师和风向标的含义。改译更好地表达了a sounding board、tutor以及weather vane的内涵,使得目的语受众能够更清晰地理解原文。
[例2 ]
原文:They had numerous meetings of various kinds to discuss and debate over important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issues during the turbulent yea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原译:在法国大革命的动荡时期,他们多次举行各种形式的会议,讨论和辩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改译:他们召开过无数会议,各种各样的会议,讨论并辩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那时正处于法国大革命的动荡时期。
英文句子的状语位置灵活多变,并非是固定的;而汉语句子的状语通常置于句首,位置较为固定。原文的时间状语位于句末,符合英语语法规范,在英汉笔译中,时间状语通常移至句首翻译;但为了减轻译员在处理信息时的压力,视译中通常保持原文语序不做改变。根据释意理论中“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的基本思想,将介词during改译为动词,转变词性,译为“正处于”,使得译文更加流畅、自然。
[例3 ]
原文:For westerners in China,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ffective team of managers means attracting local management talent.
原译:对于在中国的西方人来说,有效的管理人员团队的建立意味着要同时吸引本地的管理人才。
改译:对于在中国的西方人来说,建立有效的管理人员团队意味着要同时吸引本地的管理人才。
中文多使用动词而英文多使用名词。译员在处理“冠词+抽象名词+ of +名词”这一英文结构时,通常会把该抽象名词翻译成对应的动词含义。establishment的动词词根为establish,所以直接翻译为动词“建立”。
[例4 ]
原文:Robots will have to operate with less human supervision and be able to make at least a few decisions for themselves-goals that pose a real challenge.
原译:机器人需要在较少人类监督的情况下进行操作,并且至少能够独自做出一些决策。这些都是真正的挑战。
改译:机器人需要在操作中减少人类的监督,能够至少做出一些决策,独立地做出决策。这些目标是真正的挑战。
英文原句较长,原译通过调整两次语序,将with less human supervision和for themselves均提前翻译。然而,这种频繁调整语序的方法更适合笔译,不太符合视译的要求。减少语序的调整可以减轻译员的认知负荷,实现“先进先出”、依序翻译。改译将形容词比较级less转译为动词“减少”,并借助重复技巧翻译for themselves。尽管改译与原译相比有些啰唆,但更适用于口译实战操作。
[例5 ]
原文:Based on what it saw as a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growing economic clout and its increasing military power and diplomatic influenc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adopted a strategy that could be described as“Economically Containing China.”
原译:特朗普政府认为,一种直接关系存在于中国不断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其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外交影响力之中。所以,它采用了一种策略,可以看作是“经济上遏制中国”。
改译:一种直接关系存在于中国不断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其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外交影响力当中。因此特朗普政府采用了一种策略,就是在“经济上遏制中国”。
原译文对句子语序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将真正的主语提到句首翻译。然而在视译特别是在同声传译中,这种做法不具备可操作性,因为句子过长,译员无法等到真正的主语出现后再开口翻译。因此,依据释意理论,译员“脱离源语外壳”,从翻译核心信息a direct relationship入手,顺序翻译英文,同时将句尾的定语从句断开,单独成句,并添加适当连接词“就是”,以确保语句通顺连贯。
在开创释意口译理论之初,塞莱斯科维奇和勒代雷主要针对印欧语系内部各语种之间的互译提出该理论,并在欧洲语言口译实践中取得了积极成果。然而,该理论起初并未考虑汉藏语系的特点,也并未对汉语等亚洲主要语种进行详细的实验分析与说明。实际上,译员在实践中发现,巴黎学派的释意理论同样适用于汉藏语系,可以在汉英口译中进一步得到应用,在汉英视译中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一理论可以帮助译员跳出中文语言框架,摆脱文字本身的束缚,从而译出源语内涵,让译员在翻译中更加游刃有余、从容不迫。
[例6 ]
原文:自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物价飞涨,给人民群众尤其是那些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原译:Last year, particularly the latter part of last year, goods prices rose fast, making people’s lives, particularly those low-income groups more difficult.
改译:For the second half of last year, the price of goods rose greatly. This has made people’s lives difficult, especially that of the low-income group.
在汉语中,以“是”字构成的动宾短语做谓语的句子叫作“是”字句。这类句型广泛应用在现代汉语中,通常用于表示“等同”“分类”“存在”“强调”等意思。“是”字前后的实词构成了句子的核心意思。视译时,应重点关注“是”字前后的句子成分。改译版本首先分析出源语分句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然后把汉语分成两句单独翻译,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译员“视幅”压力,方便灵活造句,另一方面使母语听众能够更加容易地理解源语信息。
[例7 ]
原文:该国南部有数千家工厂倒闭,引发人们对失业率上升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担忧。
原译:Thousands of factories have closed down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country, triggering concerns that rising unemployment will cause social unrest.
改译:Thousands of factories have closed down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country, which triggers concerns that rising unemployment will cause social unrest.
在笔译中使用现在分词triggering是非常恰当的,但现在分词作为伴随状语在口译中却很少使用。只要情况允许,在口译中,译文的形式大多体现为口语风格,即“口头”的交际方式。
[例8 ]
原文: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疫苗加速普及,药物加快研发,让我们看到了彻底战胜疫情的希望和曙光。
原译:With joint effor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vaccines have been popularized speedily and medicines are being developed rapidly, which has enabled us to see the hope of winning the war against the pandemic.
改译:With joint effor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vaccines have reached more people and medicines are being developed. We now see the hope of winning the war against the pandemic.
现代汉语中,“让”字句是一种典型的句型结构,其结构可表示为:“NP1+让+NP2+P谓”。原文中的“让”表达致使义,语义基本等同于“使”字。句式语义表示“让”前成分导致“让”后成分发生某种变化,产生某种状态。在英文中,这种用法通常对应于使役动词。原译使用“enable”而非使役动词,是为了使语域更加正式,更加符合笔译措辞;而改译依据释意理论“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的原则,将长句切断,译成两个单独的短句,这样能够减轻译员的认知负荷与压力,更适用于实际口译工作。
[例9 ]
原文:各国人民需要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原译:People in all countries need to cross a river in the same boat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at the moment.
改译:People in all countries need to work together against current challenges.
原文中出现了“同舟共济”“共克时艰”这样的典型汉语四字短语,原译只是按照字面意思翻译,没有脱离比喻义,听众很可能难以理解。根据释意理论“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的核心原则,翻译“同舟共济”的内涵即“合作”,改译中没有受到源语汉字的束缚,直接言简意赅地翻译文字内涵,译文清晰、简洁,符合视译要求。
[例10 ]
原文:牢牢把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大势,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破解难题,不断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我们就一定能携手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明天!
原译:Following the trend of multi-polarization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e need to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building of an open world economy an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opportunities in the opening-up and the resolution of problems in the cooperation so that we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better future for mankind.
改译:We need to follow the trend of multi-polarization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e need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through opening-up and address problems through cooperation. We need to build an open world economy and contribute to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Only doing so can we together build a better future.
原译是标准的笔译版本,将长句一气呵成,充分调整语序并显化中文内在的逻辑关系,形成一个较为正式的译文版本。而视译长难句时,首先需要做的一定是断句。原文中有五个分句,其中第二个分句与第三个分句结构相同,可采用“合并同类项”的方法,合译为一句。故而翻译成四个短句,补充缺失的主语we。
从上述实例中可以看出,英汉视译的策略首先是切分断句,其断句的标志包括:介词、分词、关系词和从句;其次是重复,即当修饰成分与被修饰成分被切断翻译时,需要重复被修饰成分;最后主要集中在词性转换以及句式转换这两个方面。词性转换是指通常将英文中的名词、介词和形容词转换成中文里的动词;句式转换则包括被动句译为主动句、强调句的增词处理(添加“正是”一词表示强调意味)等特殊句式的转换技巧。
汉英视译的策略同样包含三个方面:首先,确定中文句子的主谓宾,即抓住句子主干,判断句子的主语是否可以作为英文译文的主语,构思译文框架;其次,灵活断句、化整为零,特别是在原文主语内容较多,或者是遇到中文流水句时尤为适用;最后,透过现象看本质,当原文表达较抽象或者重复烦琐时,需要快速提炼原文核心信息进行翻译,冗余以及细枝末节的信息可以省去不译。
结语
综上所述,在视译过程中,无论是英汉视译还是汉英视译,译员都需要摆脱源语的语言形式和字面意思,彻底理解原文的内在涵义。同时,译员需要充分运用自己掌握的语言、学科和百科知识,结合源语的背景信息,避免机械地字面翻译,从而快速、准确、流畅地传达源语在特定语境下的涵义。
口译实践和相关教学是释意学派口译理论的基础,同时该理论也为口译实践活动提供了有力指导。近年来,释意口译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我国翻译教学中,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例如,厦门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提出的“厦大模式”,成功地将该理论运用到高校口译教学中。巴黎高等翻译学院以重点培养译员的翻译技能和语言外知识能力为己任,不断深入推进口译实践与口译教学的良性互动融合,其作用将得到更广泛的认可。
* 本文系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融合发展(外研社)重点实验室基金项目(项目编号:NKF2023BC08)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高璐璐, 朱云翠. 2013. 从释意理论看交替传译中“意义脱离语言外壳”现象[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 177—180.
勒代雷. 2011. 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M]. 刘和平, 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覃美静. 2017.释意学派理论与口译教学研究[J]. 中国校外教育, (8): 111—114.
秦亚青, 何群. 2009. 英汉视译[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沈雨. 2013. 口译视阅中释意学理论的应用[J]. 青春岁月, (12): 105.
许菲菲, 陈圣白, 张丽红. 2015. 从图式理论看交替传译认知过程——以口译初学者为例[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1): 119—126.
作者简介
张君 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口译和高职英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