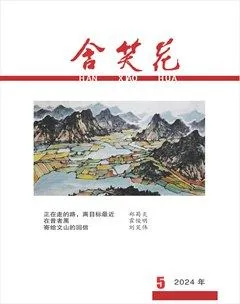轻轻的手帕有重量
拿起轻轻的手帕,感受沉甸甸的重量,这是我经常做的一件事情。我至今仍保留着两方手帕,一方灰色,一方深蓝色,有些褶皱和泛旧,上面的勾花及针脚却依然明晰,被我放在一个木纹邮票收集盒里保存了起来。一来算是怀旧念想,二来两方手帕与我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
现在的生活中,手帕已经过时了,大多被纸巾所替代,像竹简被纸张代替一样。纸巾一次性,用罢丢弃,潇洒又便捷。
我固执地守护着那两块方方正正的手帕,因为我与它们,有着诸多的故事。我从小就与手帕有缘,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几乎是我的一个标识。这话说得或许有些夸张,但是真的。
从我有记忆开始,我的胸前就飘有一方手帕。
小时候的我,在乡下长大,印象中家里很穷,父母很努力地干活,对我们宽严有度。小时候的我鼻涕多,母亲就在我胸襟前系上一方手帕,这让我成为村里孩子们中“独一无二”的存在。以至于村里的人遇到便会笑着对我说:“人家是挂红旗,戴红领巾,你是脖子底下吊一条鼻涕巾。”一起玩乐的伙伴们也以我系手帕作为取笑的乐子。当时在村里,还不流行手帕一说,只知道可以擦鼻涕。
母亲不计较村里人怎么说,回到家,她抚摸着我的头说:“什么鼻涕巾,人家明明有学名呢,手帕,这叫手帕。”我虽然也不知道确切的应该叫什么,但我相信妈妈的话。儿时的我总是很佩服妈妈,妈妈虽不识字,却能给我们讲出许许多多关于孝养父母、推恩及人、尽忠尽孝等方面的故事。
打记事起,我就喜欢跟着母亲形影不离,连她下地干活,晚上开家庭成员训话会,我都要守在她身边,听她认真地讲:“做人要守规矩、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无为也要立德感恩……”
大约在我3岁那年,印象中母亲临近天黑了还出去打猪草,让哥哥照看我。哥哥也只是比我大三岁而已,显然,母亲高估了哥哥的照管能力。当我忽然发觉母亲不在身边,立刻如“百爪挠心”般不安,疯狂寻找无果,正哭叫无助之际,哥哥告诉我母亲的去向,听罢,我哭喊着冲出门,踉踉跄跄朝着距家一公里左右的那方田地走去。母亲在玉米地里也似乎听到我的哭声,慌不择路地冲了出来,看到满头大汗、满脸泪水的我,一把拉了过去,紧紧地抱了起来,并不停地用我胸襟上的手帕帮我擦拭鼻涕和眼泪。那方小小的且温暖无比的手帕,充满了母亲对自己满满地爱,于她而言,是责任,于我而言,是安全和护佑。
关于手帕的更多记忆,就是出现在乡邻间“红白”事宜和走亲串戚的饭桌上了。因村子小,几乎全村都是本家,哪家有什么大事小事,都是集体帮忙,活一起干,自然饭也就在一起吃。每当临近吃饭,母亲总是先带我去洗手,再用手帕把我的手擦得干干净净,拉整好衣襟。再三叮嘱我:“要学会懂事,敬亲尊长,不能上桌,长辈讲话时要保持安静,不要大声言语等。”当时我对母亲的话不谙其理,自觉坐在母亲摆在其身后的小凳子上,所食菜品也是母亲夹来的,吃饱后自己用手帕擦嘴,擦手,然后诚恳的和同桌的长辈说“你们慢慢吃,我吃饱了。”长辈们都夸母亲会教子,懂礼节,有礼貌,母亲总是笑着说:“人之初,性本善,得从小教起,避免以后走偏了。”
我六岁那年,父亲受了严重的伤。政府出资,村民出力,在村西头河流上游修筑近五十米高的拦水大坝,需在距水坝不远处的大山开山取石。在一次炸石过程中,一块棱角锋利的石头从山腰滚落下来,父亲躲闪不及,石头擦着小腿部位划过。顿时,小腿就被划开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一起干活的村民急忙用衣服做简单包扎后,用拉石头的推车拉着父亲就往医院赶。最后伤口缝了三十多针,伤口缝合线像紧紧趴在父亲小腿上的“蜈蚣”,让人瘆得慌。当我看到父亲泛白的脸上因疼痛涌出的汗珠,母亲含着眼泪,让我取下胸前的手帕帮父亲擦拭汗珠,“儿啊!越是有患难,一家人越要互相关心,彼此照应,千万别忘了父母的苦,我们养你们小,你们要养我们老……”母亲就是用这样朴素的方式,教会我们如何行孝悌之事。
关于手帕的记忆,太多太多,直到后来手帕被纸张所替代,那两方最常用的手帕才被洗净晒干,永远的封存了起来,但关于手帕的思考,却从未间断。
随着年岁的增长,如今我已到而立之年,不仅是父母的孩子,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我也常常透过这两方小小的手帕,细心琢磨母亲的教子之方,也渐渐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其实,勤劳朴实的母亲,虽不懂得用“圣贤之语”来归纳总结传承千年的文明礼仪、尊卑有序,但她时刻以自身对社会万象的“好”与“不好”的理解,言传身教地为我们传承为人处世的哲学和待人行善的礼仪之道。
以至于在我后来的成长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就懂得了更多,比如尊老爱幼,是要对上孝顺,对下爱慈;文明礼仪,是要尊重他人,善泽惠客,笑迎宾客;赡养父母,是要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夫妻共处,是要相敬如宾,相濡以沫,仁心对待;教其子女,是要教其明德、修身、齐家。
母亲的家风教育是如此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的就把大道理、大学问细化分解,变成接地气,冒热气,善于认知和吸收的东西。而这些或大或小的生活认知,却影响了我的一生,无时无刻,总有一个人在告诫我,在劝慰我,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
我的一生中,总有一杆“天平”在称着重量,让我的人生不会倾覆。
现在,每当我拿出珍藏已久的两方小小的手帕,这两方曾挂在我胸襟前的小手帕,我都感觉是在和多年前的母亲对话。如今母亲已上了些年岁,仍然不改谨言慎行的作风,在适合的时间,适合的场合,教会我行走社会的方法、经验和规矩。同样,对我的孩子,她的孙子,也一直沿用教育我的方法,规范孩子的一言一行,这是一代和一代人,对于良好文明礼仪,良好家风的自觉传承与升华,这些都是做人做事必不可少的部分,是带有光环的学问。
前几天,阳光正好,我又再次把手帕拿了出来,掸去上面积淀的微尘,盒底放上樟脑丸,避免虫蛀。经过二十多年,手帕颜色更淡了,更轻了,似乎有些“吹弹可破”。但只要双手捧起手帕,仍然会感知到它像良心一样澄明干净,像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一样厚重。
等孩子再大些,我要告诉他关于这两方手帕的故事,让他好好留存,并透过这两方泛旧的手帕,汲取那些不能丢失的东西。
【作者简介】张一骁,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美文》《滇池》《阳光》《散文诗》《鄂尔多斯》《牡丹》《含笑花》等刊物,有作品入选《云南文学年度选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