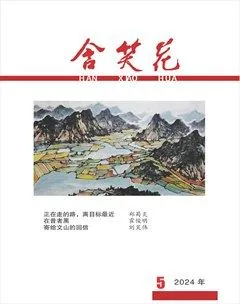乘着轻轨去旅行
“铛、铛、铛——”
试运营第一天,4号有轨电车快速从丘北县城六十米大街驶过,在一个个十字交叉口发出一串串鸣笛。有轨电车那极具绅士而古老的声音,让我恍惚间穿越到古老的大上海,那些有着窈窕身段的旗袍女郎正挎着手袋,优雅地踏上电车。头戴礼帽的老绅士们侧倚在车厢里的木长椅上,气定神闲地看着当天的报纸……直到有轨电车驶出我的视线,我还久久伫立在六十米大街旁,瞧着电车消失的方向出神。回到家,与妻子聊起,话头间浸染兴奋,朋友圈跟我的心情一样,都在奔走相告着有轨电车开通的喜讯,试运营的通告、电车行驶在各路段的图片、自拍的坐电车图……翻着,瞧着,兴奋的心情已到达极致,便与妻子约定乘州庆放假去体验一趟。
翌日六点五十分,我们早早到达椒莲广场,站台上早已站满人,熙熙攘攘的,谈话间我才知晓,大部分人跟我们心情一样,没有出丘北的打算,只是怀揣喜悦的一次尝试。电车外观鲜明、亮丽,车内清洁、宽敞,能坐能站,瞧着一节节车厢里黑压压的人,不用数就得过百。乘务员说,最高可达三百六十余人。七点十五分,有轨电车“呜——”的一声长鸣,接着“铛、铛、铛——”动了起来,稳稳当当。林立两旁的现代化建筑群从宽大的车窗闪过,有种摁快门的愉悦感。我们的座位靠前,在电车的提速中,就像坐在一支射出的箭头上,穿越在山间林丛。
望着窗外不断更替的一幅幅画卷,我的血液开始湍急,那份安放在心底的记忆随之鲜活起来。在我人生驿站里,乘车能怀揣如此激越的心情得从十二岁的当口说起。那年小升初,县一中扩招,父亲要我试试。坐着手扶拖拉机,沐浴在万里微风和灿烂的阳光下,比展翅在天空的鸟儿还要美。我们十点多到的县城,父亲指着头顶偌大的沟渠建筑告诉我,那叫渡槽。年代久远且高大威严的建筑让我肃然起敬,也就是从那刻起,“渡槽”一名以现代化气息的代名词植入我的大脑皮层,牛车、马车、拖拉机、“一三菱”让我目不暇接,心底也自此盘踞起艳羡。两个月后,我接到了县一中的录取通知书,父亲将我送到学校安置妥当后,径直带我朝着渡槽的反方向而去,我紧张地跟父亲强调回家的方向,父亲笑了笑,告诉我要去找个亲戚。亲戚?县城竟然有亲戚。惊喜之际,心底竟突然飙升起一种骄傲。
父亲说的亲戚在客运站工作。在父亲的介绍里,我羞涩地叫了声:“大孃。”大孃扎着马尾,脸盘子宽宽的,笑起来很亲切,在给我们煮面条的时候一个劲夸我,说能进城读书不容易,要我好好学。在她一句句的夸赞里,我觉得她更亲了,有种母亲的味道。吃面条的时候,我的眼神不断溜出窗外,盯着窗外往来的车。那些车的颜色比停在渡槽的好看不说,还有篷有玻璃有窗,最主要是里面安有装着靠背的椅子,远比我坐的拖拉机要高档豪华得多。当时我想,这要哪样的人才坐得起?
回到学校,一辆辆安着靠椅的车子盘踞在我的脑海,如影随形,在饭间、闲聊、梦里,甚至课堂上,冷不丁跑出一辆,占据着我当前的思绪。下午放学,顾不上太多犹豫径直朝客运站奔去,可到站外我竟踌躇起来,该对大孃咋说?直接说想看车,还不得羞死人,不说又能找何种借口?就这样离开,那些车又像一只只长在心底的猫使劲抓挠得难受。长时间的踯躅、徘徊,引来保安的厉声盘问,惊恐中不得不说出大孃的名字。大孃嗔怪我:“到门口了不进来,你怕哪样?”那神态、语气,像极了母亲,我没啥好担忧的,依着她最后的叮嘱。我来的趟数多了,但好些时候,满足了心底的那份渴望后就偷偷溜了,回到宿舍,时常会在梦中笑醒。还别说,三年后我考取文山民族师范学校,真是梦想成真。
每每说起第一次乘客车,欢悦的心情及尴尬的窘态就会从折叠的记忆里流淌出来,每一次都那样清晰,那样鲜活。那天,瞧着干净的坐椅,用手横扫了几次裤子都不敢落座,最后还是旁边的大叔好心劝说:“不怕,脏了可以抹的。”我的脸在这份劝解里烧起来,转瞬我才想起,身上的这套衣服是出门前母亲才叫换上的。车速很快,进出弯的时候像风吹过玉米地,整车人跟着摇摆。出城没多远我的整个腹部就开始翻江倒海,最后把临行前母亲的那份关切都给吐了出来,浑噩间,我陡然发现自己把客车给弄脏了,整个侧面,粘了好多呕吐物。难受、担忧,让我更是无所适从,到达文山,客车刚停定便落荒而逃,那狼狈的样子至今还历历在目。
想想当时的尴尬,我忍禁不禁窃笑了一下,妻子问我高兴啥?我说:坐这电车开心。就她的表情我知道她不信,可我也不好意思仔细跟她解释。后来也呕吐过几次,直到2010年,赶上城市规划的步伐,丘北至炭房路段扩建,由三级公路升为一级路,我这才得以解除去文山路途劳累的畏惧。
本想着工作了就会好些,哪知分配到树皮中学的我又体验到了坐车的艰辛。从县城到树皮,一天一趟,太多的乘客见到车来就全没了秩序,等不及车上的人下来,捡个空隙就往上挤,有的干脆爬窗子,坐的坐,站的站,每一个角落都摞满了人,没一丝缝隙,比父亲谷箩里插的玉米苞还要密集。去年十月,我与妻子到树皮收集辣椒图片,行驶在平整的柏油路上,她突然讲起当年的窘事。那次她到学校看我,没挤上车,搭了一辆手扶拖拉机,站到我面前差点没认出来,整个人除了轱辘转动的那两颗黑眼珠,全身堆满厚厚的灰尘。
比起妻子的那份尴尬,让我更受罪的要数上昆明。以前,从丘北到昆明得五六个小时,我本不想去,可面对学历的提升,到云大参加函授势在必行。为了完成学业,再如何精减,每年至少两趟,脚僵腿麻是小事,主要肝胆都吐出来的那份痛苦,不是人人都体验得到的。车坐多了,自然就找到了让自己舒坦的办法,上车前半小时淡淡喝几口粥,不能吃多,也不能空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头晚必须睡踏实。说来也怪,越想睡好却越睡不着,汽油味混合着车里乘客发出的各类异味,老早就侵蚀着我的每一个细胞,还未天亮就开始晕起车来。后来想着坐夜车,天亮睁开眼睛就到昆明多省事,哪料更遭罪,挠人的鼾声能忍,可刺鼻的脚臭,实在受不了。在司机的叫骂声中虽然套上了塑料袋,可哪里套得住脚上浓重的异味,那趟车我比任何一次都晕得厉害。拿到文凭后发誓再也不去昆明,哪料2016年底,云桂铁路开通,丘北到昆明仅一小时二十分,稳稳当当的高铁彻底治愈了我晕车的毛病。有时想想,还真得感谢高铁时代。如今,高铁路过我家乡,继普者黑机场之后树皮又开始筹建新机场,中铁十五局乘兴而入进驻丘北,沪丘广富高速路即将像树根一样铺展开去,想想丘北发展如此之神速,不自觉又咧开了嘴。在我兴奋之际,行政中心站、人民医院站、黑箐龙站、高建槽站、瓦窑冲站、密纳站、物流园北站,在我眼前一晃而过,也就十来分钟的时间,普者黑高铁站就铺展在眼前,熙熙攘攘的人群大都操着本土方言,他们是沉浸在州庆假日的休闲里,还是体验到有轨电车的喜悦,每张脸庞堆挂着如此灿烂的笑容。
能不高兴吗?丘北,成了国内首个拥有有轨电车的县级城市,首次实现了“高铁站”与“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的“绿色”“无缝”连接,加上5号线的开通,有轨电车在短短的时间里,植入每一个市民心中,成了丘北街头的一道风景。
【作者简介】肖正康,云南省作协会员,先后在《小说林》《文艺报》《陕西文学》《含笑花》《云南日报》等报刊发表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百余篇(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