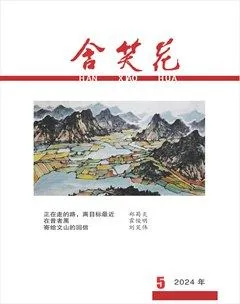小芬姐
小芬姐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在我家帮忙采茶叶的一位姐姐。说来也是缘分,如今我就在她的家乡工作,印象中她生活的村子很贫穷,对比早些年,如今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回想起初次见到她,都是二十一年前的事了。那是赶集日的一个下午,估摸着时间,妈妈应该快回来了。我爬在院子的围墙上,期待着能早一些清点妈妈背箩里东西。果然,很快就看到了村里赶集回来的队伍,过了一会儿,妈妈便踏上家门口的小陡坡,朝着家里走来,身后还跟着一个陌生女孩,十五六岁的样子,皮肤很白皙,个子瘦小,一头乌黑的头发干干净净地,扎着一个高马尾。
我从围墙上嗖地跳下来,小跑着过去:“妈,她是谁?来我们家干吗?”“我买回来的,给你当姐姐。”妈妈一边说,一边笑得合不拢嘴,本来还有些拘束和胆怯的姐姐也跟着笑起来,我皱了皱眉头,假装生气地问道:“妈,你骗人,快告诉我她是谁?”妈妈把背箩放下,扯着腰前的围裙擦了擦汗,又径直走向水缸,舀了一勺水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随即便招呼着这位陌生姐姐坐下。这才慢悠悠地告诉我:“这是小芬,我请来帮我们采茶叶的,估计要在我们家住很长一段时间,你就喊她小芬姐吧。”
后来,小芬姐也确实在我家住了很长的时间,因为家里只有哥哥的缘故,所以对于这位陌生姐姐的到来,我欢喜得很。小芬姐性格很温和,在我的印象里,她从来没有发过脾气,我俩单独去采茶叶的时候,水、午饭她从来不让我背。
唯一不好的就是她会告状,晌午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总会偷偷到地棚里睡觉,才躺下一会就被她发现:“你再不起来,回家我就告诉你妈妈。”她可不是恐吓我,因为她的状告,我没少挨竹条,所以我只能乖乖地回到老位置,顶着烈日,采着垂头丧气的茶尖儿。每次她告状之后,我就赌气,晚上不和她睡,但是由此一来,我就会错过动听的睡前故事,受惩罚的还是我。我最喜欢她讲的灵异故事,她总是描述得很有画面感、让人身临其境,声音时而平淡、时而低沉,到关键的时候她还会提高音量,吓得我大叫,躲进被子,看着我的囧样,她总会咯咯大笑:“胆小鬼,谁让你天天缠着让我讲,看你还敢不敢听。”
“小孩子不小心遇到偷牛的,还会被一起偷走,到了晚上我们要约着一大群小伙伴才敢出门……”听着她的故事,脑海里总是会想象她老家的模样,在一个山窝里头,周围都是高山,道路狭小而又弯曲,边上都是茂密的森林。
每个月,妈妈都会拿着单据到茶厂结算卖茶叶的钱,回家之后又会把小芬姐一个月的工资一起拿给她。那时候小芬姐的工资是每个月一千块钱,记得有一次给小芬姐算工资的时候,爸爸妈妈趁着小芬姐出去拾柴的时候,在火炉旁悄悄商量,要多发给小芬五百块。“你小芬姐家兄弟姐妹比较多,家里很穷,小小年纪就到我们家打工,一年到头都不回去,看着也很心疼。”虽然那时候我很小,妈妈的这句话依然清晰地刻在我心里很多年。
每到茶叶结果的时候,我都要被拽着一起去摘茶果,说是帮小芬姐摘的,她也想在她家那边种茶叶。“拿回去之后要捂一段时间,等到它发芽之后就可以栽种了,打窝窝的时候不要打太深,不然不容易长出来。”妈妈一边说着,一边给家里的小白骡架上驮子,把茶果抬上驮子之后,妈妈领着小芬姐,赶着一边驮着一袋茶果的小白骡,往那个我脑海中神秘的小山村走去……
“姑娘,你在干吗呢?端午回不回家过?”
“妈,我还在下村呢,不知道那时候放不放假,我今天来未哪基了,就是你以前经常拿来吓我的村子,人家现在村子搞得可好看了,群众又团结。”我像往常一样简单和妈妈分享着下村的所见所闻。
“哪有吓你啊,那时候那里是确实穷,以前来我们家采茶叶的小芬姐就是这个村子的,她来我们家帮忙了差不多三年。”就是这样的一通电话,重新唤起了这段我本以为早已尘封的记忆。
记得我刚来单位工作的那段时间,偶然一天听到办公室的前辈在讨论要报哪个村子作为典型材料,“报未哪基啊,美丽乡村。”一个清脆而又响亮的声音,敲碎了记忆时空的玻璃。“不好好读书,以后把你嫁去未哪基那些地方,有你吃不完的苦。”小的时候,家里的长辈就经常用这个村子来恐吓我们,教导我们要听话,好好读书。印象中,这个村子只在我们的耳朵里听过,我从来没想过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村子。所以当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心里是欣喜的,是期待的,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一睹它的“芳容”。
我在这里工作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未哪基属彝族僰人支系,这儿的村容村貌、历史变迁的材料我看过无数遍,日常也提笔撰稿过这个村子的通讯信息,可以说我对它是有感情的,但是当我知道记忆里那位与我感情深厚的小芬姐也是这个村子的时候,我对它的感情如洪水般袭来。
看着这座“神秘”小村庄的巨大变化,我再一次感叹着脱贫攻坚的丰功伟绩,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脱贫之战,给全国贫困地区以及千千万万边疆贫困地区群众带来的福利是多么令人惊叹。
2016年,一个脱贫攻坚项目落在了这里,一场轰轰烈烈的易地扶贫搬迁彻底结束了未哪基这个偏远山区的年代。如今的未哪基,搬离了山沟沟,者太—底圩的公路穿村而过。距离集镇只需要十几分钟的车程,远远望去,一排排红墙碧瓦的小别墅依山坐落。每逢节日,彝族歌声荡漾山间,醇厚的彝族美酒味弥漫着空气,常常让人沉醉在这云雾缭绕的彝家村。置身其中,很难想象,眼前这个红墙碧瓦依山落,人勤茶绿梨花香的美丽村落曾经是什么模样。
岁月不言,唯石能语。带着再见故人的满心欢喜,我再一次走进这个村子,特色彝族文化元素随处可见,村里来来往往的群众身着民族特色服饰,女性服饰以红、蓝为主色调,镶嵌有各式亮丽的配饰,男性服饰多以浅黄色为主色调。路过几户人家门前,常见三五成群的年轻少女,聚在一起制作服饰,在无数个一针一线地来回间,仿佛编织着他们美好的生活。
不一会儿,在村组长的带领下,我如愿地见到了小芬姐。她已然变了模样,年近四十的她褪去了当年的青春,身上多了一份岁月的沉淀。见到我,她很惊奇,脸上的笑容一直没停过。
“小芬姐,是我,你以前在我家住过两三年呢。”经过我的提醒,她很快便记起了我,随后她热情地招呼着我坐下,还端出了瓜子、水果这些,一个劲儿地让我吃。我们聊了很久,多是聊以前的趣事。之后我问起了她这些年的生活状况,得知她现在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由于公婆常年身体不好,独自一人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小孩,管理着六十多亩茶叶,据说她们家现在的茶叶种植面积是全村最多的一户,说到这里她还笑着提起了当年的小白骡。
晚饭过后,我便驱车返回,回来的路上小芬姐的话萦绕耳旁,当初那些故事里摇摇欲坠的叉叉房、泥泞的小路、总是会丢失的牛羊都是真的,而我的小芬姐姐,如今同这里的人民一样过上了幸福生活更是真的,窗外灰蒙蒙的,但也遮不住这夏日的绿意盎然,只愿这里的青山、绿水继续见证着这份的幸福。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今,整齐排列的小洋楼、漫山遍野的茶叶、正在结果的长冲梨、载歌载舞的纯朴民风都在向世人展示“云上彝家”的幸福生活。
【作者简介】韦延梅,女,汉族,广南县底圩乡人,广南县者太乡人民政府一级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