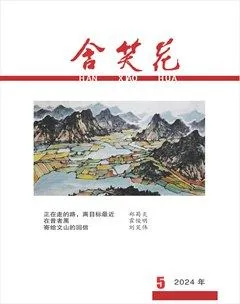温浏往事
今夜不宁。
关掉房灯,小沙发纵容半躺,目光刚好避开小城的一地灯光,任对面山黛青的、黑得不坚定的轮廓涂满窗口。
空间始终有形,时间没有。
时间是世间最温柔而最残忍的存在,每天以日出派生遐想、以黑暗铺陈安详、以鸡毛蒜皮磨损你的警觉,不动声色拿掉你十年八年,让你添皱纹、掉头发,让你的大半生须臾间便被粘入回收站……算算,我上一次在此过夜已是三十多年前,足足三分之一个世纪啊,怎么着也应该下楼走走的。但今夜四肢慵懒的借口十足——我跟丘北县城“不太熟”,我不来则罢,我到了这里,满脑子便只有温浏乡。
手机准确地指出,我的住所离温浏65公里,不远不近,正好就是“山那边”。如果思念针对的是一个人,想来呼吸已经急促、胸口已经狂跳。
一
199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进入省级机关上班,并且在单位的人还没认全的时候,名字被纳入省派“社教工作队”,目的地文山州丘北县温浏乡。
我们坐汽车前往,先到文山接受州情培训。又一天中午,我们午饭后从文山出发直奔温浏。在大巴车上,队友们似乎全都沉沉入梦,我却可劲地东张西望,充分感受颠簸,陪着陌生的滇东南大地延展它绿意不够、顽石充斥的丘陵“卷轴”。不经意间,太阳似乎熬不过我,溜了,疲乏与漆黑同时报到,我的眼帘终成铁闸。不得不说,在那个遥远的夜晚,温浏实在遥远。
“到了。”不知是谁大叫一声。我挺身寻找,见左下方隐约有许多灯光。凭感觉,汽车正在下坡,我们应该是到了温浏坝子后面的半山上。星星点点的灯光纵然不辉煌,那也是温浏在暗夜里头一次伸向我们的臂膀。一时间,清一色二十来个男子汉的欢呼随着汽车的趔趄起伏。我注意到,在一片星星点点的正前方,有栋楼房的灯光形成了规模,就像是领头的大灯塔。我想,那栋楼应该就是我们要入驻的乡政府了。直到汽车熄火,一群人踏进乡政府所在的瓦房四合院,我才知道自己想错了,前方三层楼的砖房属于温浏中学。
奇怪的是,感觉错了,我心中却不曾有半丝失望。相反,“最好的房子属于学校”这个事实让我亢奋。我身在滇东南的温浏,联想到滇东北的老家。那里见不到这么多石头,但山头很高大,比这边要挺拔,闭塞和落后也许都差不多。我离开老家中学也就那么几年,没忘记几排小平房容纳着上千学生,便是我冲刺大学的校园,温浏中学拥有全乡最好的新房子,而且还是三层楼,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在后来的日子,中学的三层楼便成了我们暮色里下乡归来的坐标。
我很快将对温浏的第一印象写在一篇标题含“希望”二字的散文里,寄给了《文山报》。在其中,中学顺理成章被我视为温浏的希望焦点。而在憧憬温浏的未来时,我选择的象征物是红辣椒。
“丘北有中国最好的辣椒,温浏有丘北最好的辣椒”,温浏乡一位领导这样说。话说得或许有些绝对,但出于夸奖自家“孩子”的角度就没有不妥。我们去时正是秋天,听了他的话,长在乡政府周围菜地里、挂在家家户户墙上的辣椒格外夺眼。有一天傍晚散步,我和另一个年龄比我小的工作队员各摘了人家墙上的一个头尖尾圆、暗红纯正的干椒。那不是拿来玩的,我们说好,同时夹进信封,我寄我的“女神”,他寄给一个过去不敢表白、只听说毕业后在某地工作的某女生……记不清多少天后,我先收到回信,得知我的干椒被挂在窗口,她“每天都倾听着无声的红风铃”;他就有些惨烈了,信被从外省退回,信封上写着“地址不详”还“查无此人”,气得他一把撕开,辣椒掉在地上,还是那样红。
既然是约着一起干的事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安慰他。我俩那天散步很远,都到了中学下面的田间。收割早已结束,空旷的土地就要冬眠。一路不知该怎么说的我,伸出手狠狠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想到比我高半个头的大小伙,一拍他就蹲下,哭了。我说:“算了,失联就是缘尽,你翻篇吧。”他可怜巴巴地掏出那枚辣椒:“哥,这个怎么办?扔了吗?”我犹豫了一下,接过辣椒,一扯两半:“吃了吧,我陪你吃……”
我在那篇散文里讴歌温浏辣椒的时候,写的当然不是这件事。我当时的着眼点好像是,温浏辣椒那么红,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壮乡的一位“致富明星”。
二
温浏多壮族,他们说话时似乎都咬字很重,不藏着掩着。
我们工作队将近二十个人,来自好几个单位,有处级、科级,还有我这样的什么也不是。队长高配,由某厅一副厅长担任。队长把大多数人都安排到村里驻扎,只留下我和一起吃干辣椒的小伙子,他负责协调联络,我负责全队所有的文字。拿队长的话说,他是“通讯官”,而我是“史官”。
在老宅里办公的乡政府很拥挤,好不容易腾出一小间房子让队长住,我们俩则分别跟人挤。我挤的是一位乡党委委员的宿舍,位于主办公区的四合院后面,也是老瓦房,二楼,必经的木质楼梯有些响,室内的木地板也是。
我背着随身的行李跟着乡党委委员走进他房间的时候,木床已经被他腾出来,空着。他的蚊帐罩着一床草席,拉开就见草席铺地,铺盖铺在草席上。我也是个执拗的人,坚持要他回到床上。两人争执了好久,万万没想到他会发火:“让省里来的老师睡地铺?你当我是什么人?你不依我就去找书记,让他安排你跟别人去住。”我当然不敢再犟。临窗摆着他的书桌,剩下的空地,刚好够一个人拉开凳子坐下写字。他的主要工作也是面向文字,常常要加夜班。但自从我住进去,他加班便总去办公室,为的是把书桌让给我。
他跟我说母亲身体不好,所以周末不忙的时候便步行回家。再回来时,挎包里一定掏出吃的给我:“你赶紧,莫放坏了,我是吃多了,不喜欢吃。”有一个周末,他问我可不可以陪他回一趟家,我想都没想就点头。一路翻山,走了三个多小时,赶上他妈急急忙忙从地里回来,背上负担很重,根本看不出病的迹象。她招呼我坐下便带着儿子上楼去了,等我想起什么,跟上去,一只显然自家舍不得吃的火腿已被他娘儿俩锯开,取最好那块,准备用新鲜的红辣椒爆炒……
整整数月,除了入住那天,他再也没有过让我不适的言语和表情。记得分别的时候,我搓着双手,理不直气不壮地表示自己的“随身听”和铺盖不想带走了,请他别嫌弃。他不干,我便记仇似的将了他一军:“你不要我就放到书记家,让他转给你。”
我有我的道理:棉絮带走体积大,不如让他的床更软些。下乡前夕专门买的小放音机,之前他也常借过去听,爱不释手。
结果……结果后面再说。乡党委委员虽年轻,年龄其实比我要大几岁,但他一直坚持让我喊他“小某”,说大家都这么喊,亲切。而他称呼我,从头到尾都是“朱老师”。
温浏乡有十个行政村,我们队员常驻的只有一半。没有驻村队员的地方,队长、我和“通讯官”有时间就轮流去走访。
有一次我去一个较远的行政村,说好了没见过面的村支书来半路接,没想到我才走出温浏坝子,刚开始翻山就遇上了一个人。“你是省里来的朱领导吧?”他说话中气很足,“朱领导”三个字被重音。总是这样,每当下村,我的“头衔”就被热情地拔高,让我压力山大。
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我们进入一处山谷。抬头看去,两边山相对较高,难得地长着成片的树林。支书放下干柴说:“我们歇歇再走。”他就地生火,进了树林两次。第一次取出一包翠绿的青苞谷:“我自己家种的,早起从地里掰来,藏在这里。”苞谷去壳,烤上,他让我守着,自己又进了树林,再出来时,手里捧了些菌子。
苞谷已经被我全部烤熟,他让我先吃,忙着烤菌子。我当然不肯先吃,知道那天为了迎接我,他一定是天不亮起床就赶路,而我是在乡政府吃过一碗面条的,最饿的人是他而不是我。
苞谷香甜,是那种产量不高的老品种。菌子快熟的时候,支书又变戏法一般从怀里摸出一小包盐巴,小心翼翼地往菌窝里撒:“盐巴是个宝,缺了盐就没有味道,嘿嘿。”
终生难忘的野炊之后,我们又走了很长的路,晚上到了原定的自然村已天黑。我坚持先开群众大会,支书主持,我宣讲。那个村还没通电,屋子里只有一盏煤油汽灯,挂在柱子上,光线很暗。我讲的时候,行政村支书和自然村村长不时用壮语嘀咕,语调时低时高,似乎有所争执。待我宣讲完毕,村长猛然起身:“省里的领导难得来,我有个问题要反映。”他讲汉话不太流利,讲话同时还要对抗支书的阻止。我听下来,他是在说村里有条水沟,雨季的时候老人孩子路过不安全,想砌两个水泥墩,搭座木桥,“请省里来的领导拨点钱买水泥”。
依我的实际身份是无权“拨钱”的,这一点支书大致了解,所以他才会阻止村长不让说。而村长满怀希望,我又岂能装聋作哑?弄清楚他的“胃口”只是五百块钱,我说:“大家凑吧,我个人出二百块。”那两百块钱是我揣到钱包里的大半,相当于我当时一个半月的工资。我这样说,社员堆里有个年轻人立刻站起来说他也出一百,坐在我身边的支书也当场掏出了他仅有的二十块。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支书搂紧我的肩膀耳语:“谢谢你啊朱领导,村长为这件事都找过我好几回麻烦了。”
会后到村长家吃饭,火炉上小火炖着一锅鸡肉,吃起来已经烂熟,很香。也没别的菜,村长先给我的饭碗盖满鸡肉,然后提着勺子候着我吃,不时添加,自己却不吃,说吃过了。支书自己找个大碗,苞谷饭加两勺鸡汤,很快就吃完。一起去的还有主动捐一百块钱的小伙,没动筷,也说吃过了。我吃了个大饱,支书指着小伙子说:“今晚你跟他去睡,新盖的瓦房,条件好些。”小伙子拥有一辆二手货车,经常在外面跑运输,放在当时的整个温浏乡也少见,他是村中“首富”。
打着手电筒,小伙子直接将我带到他家楼上的房间,被子新,蚊帐洁白。我很累,倒头便睡,迷糊中隐约感觉到楼下有孩子反复哼哼。第二天一早下楼,只有支书等候。我才看见,小伙子家一楼屋角,还未经打理、凹凸不平的泥巴地上打着地铺,难怪孩子一夜不宁呢,我占用了他家唯一的床。
想找主人道声谢,支书说小伙子出门了,女主人带着孩子下地去了。支书陪我翻过山梁,嘱咐我沿着来路返回,我才想起头天晚上没给队长交伙食费。支书连忙摆手,一急就说漏了嘴:“不能不能,他死活不会要,那是他的一点心意啊。听说你要来,家里有两只下蛋的老母鸡舍不得杀,他就杀了两只半大的小鸡……”
藏在树林的青苞谷,捂在怀中的盐巴,睡在泥地上的一家人,未成年就被我吞掉的小鸡仔……无论过去多少年,想起这些,我的胸腔就会刮大风掀大浪。
三
从秋天到冬天,温浏少见落雨。
基本靠双脚,穿越一处又一处丘陵地,走进一个又一个自然村。半年不到的时间,我在温浏走过上千里路,倒也不觉得苦。只是,温浏的人个个让我感动,温浏的自然条件却没“感动”我。
少雨,干旱,稀松的绿意,无处不在的石头,贫瘠而不成型的“鸡窝地”,单调且产出低的农作物……据说,已有专家断言过,滇东南有些地方根本不适宜人类居住,温浏在内吗?
说说我着眼最多的学校。那时温浏的学校不多,除了一所中学,就只剩下些屈指可数的小学,大多利用土木结构的瓦房甚至草房办学,校舍简陋,老师清贫,孩子艰苦,家长无奈。在上哪哈小学,我看到教室正中贯通一条小沟,那是师生们雨季对付屋顶漏雨的“绝招”;在葫芦田小学,全校只有四套桌椅轮流用,轮空的孩子自带小凳,课本放在膝盖上听课;在盐井小学,我巧遇一个特别的聚会,为了促使辍学的孩子返校,一个年轻老师从紧巴巴的工资里抠出钱来买糖买烟款待家长……其实,就是在我所谓条件最好的温浏中学,看到的也是教室挤得只容孩子侧身通过,十多个老师头对头、身挨身挤在一个小房间备课改作业。温浏办学苦,苦在自然环境差,苦在贫困。
不得不说的还有饮水。那时温浏各村,常年吃得上井水和泉水的地方我认为就是天堂。可惜“天堂”太少,大部分村庄挖一个大塘,雨季蓄积雨水,旱季供人畜共同解渴。村民可以挑回家烧开再喝,牲畜则直接走进水塘“直饮”。水质可想而知,在此不忍回味、形容。
哪怕是我居住的乡政府,我记得也是很多人从一口井里取水,只能维持饮用、简单洗漱,想洗个澡那是做梦。所以那些日子,我和“通讯官”每隔几个星期就不得不去一次干石洞村,那里有一股山泉,从山巅的绝壁下冒出来,形成一汪清冽的井。我们每次等到太阳落山、天欲黑未黑、几乎没有村民去取水之际,带上毛巾、香皂和两只水桶,登山,提水到二米外的一块大石头后面,一人脱衣,一人服务。时令由秋至冬,净身犹如受刑:脱衣者须先“咬牙”,毛巾泡水湿身,迅速满涂香皂;再“切齿”,让另一位以一桶水淋你头,以另一桶淋你身;最后一道程序称“暴跳如雷”,那是已经冷到极限,不得不又跳又叫,以最快速度擦身穿衣,再提水换下一位……那时真是年轻啊,反复“自虐”,疾病却无一次染身。
再说说吃吧。记得刚到那天吃猪脚,队长夹起一块猪蹄提醒我们:“同志们,这只‘小皮鞋’实在珍贵,体现了乡领导对我们的深情厚谊。不瞒大家,来到温浏,每个人今后都得有‘三月不识肉味’的思想准备。”果然,后来我们在乡政府吃食堂,日常的菜谱基本就是两样:盐巴炒花生、素煮南瓜叶。温浏的花生很好吃,南瓜叶也不错,但顿顿、天天吃,也让人受不了。
在温浏,肉果然是绝对的奢侈品。且不说钱,就是卖肉的人也只在街天出现,只有一位,杀一头猪,刚开张就卖光,收摊走人。
大约是一月,新一年的元旦刚过,我在温浏收到两张额度很小的汇款单,一张出于《文山报》的那篇“希望”,另一张来自昆明。以两笔稿费预定一只猪脚,好像我还往里加了点钱。猪脚交给食堂大姐打理,她叮嘱我一定在下午四点前连锅抬走。
那是个周日,队长和“通讯官”下乡,同住的伙伴回家了。一只猪脚,我设想自己享用三分之一,留三分之二给他们三人。不料下午,静悄悄的大院迎来一人,是丘北新到的科技副县长,也来自昆明,说是临时决定到温浏看看。我义不容辞,像个“老温浏”般接待他,给他介绍情况,还带他到最近的村子转了一圈。不知不觉六点已过,想起猪脚,我邀副县长吃口饭再走。走进食堂,大姐见面就怪我晚到,猪脚早被抢光,连花生都没有了。
尴尬之际,科技副县长爽朗大笑:“给你们队长留个字条,上车,到县城我请你吃火锅。”两个多小时后,在丘北县城的一家餐馆,副县长要了好几盘肉。我也不客气,只管埋头吃,吃到他早已停筷,吃到餐馆再无食客、服务员捂着嘴瞅着一个人在战斗的我笑的时候,我似乎还不饱……副县长安排我住招待所,那便是我第一次在丘北县城过夜。
那夜我觉得特别幸福,因为吃了火锅。但温浏村里那些乡亲呢?莫说吃,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连“火锅”这个词都没听说过。温浏的生活,我待久了,看多了,也亲身体验了,越是喜欢这里的人便越是心疼他们,越是心疼便越发有爱莫能助的痛苦。
贫困是那个年代中国大地的最顽固的阴影,在温浏,在许许多多农村,特别是闭塞的山里。
四
所幸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不用打听我也相信,温浏一定今非昔比——毕竟,此处虽无地利,却满是顽强、善良的人。
此次来丘北,我本打算顺便到温浏看看。但听说通往那个方向的高速正在加紧修筑,我便改了主意——且忍忍吧,都几十年过去了,何必匆忙了事?待高速通车,我欲从昆明自驾而来,从容而去。我想找找故人,想再回干石洞、石葵、坝稿、花交,想去听说有猴子出没、当年很想去却没去成的“猴爬崖”……
三十多年前,我这个履职将近半年的工作队员究竟为温浏做了点什么?这个问题想起,就会反问自己。开会?宣讲?走村串寨?入户调查?写过一些材料?发表过几篇短文?所有这些都不足支撑自信。倒不如说,在许多方面,包括心态,包括做人,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人给我的教育反而刻骨铭心,诸多方面悄然影响了我这一生。
这已足够,我与温浏便是这样的“君子之交”,我于温浏,有愧而无悔。
丑时已过,这篇文章必须收尾,但没触及的细节还有很多。时光冷酷,记忆温热,温浏在我脑海依然有它近五百平方公里般的广阔,再输入十万字未尝不可。
比如临走那天,乡政府为我们践行。我清楚记得,猪脚肉再一次上桌,书记和乡长亲自执勺在大菜盆里打捞,硬生生为每个工作队员配了一只贵客才能享用的“小皮鞋”。他们还敬酒,喝的是我们故意读错的“贰角酒”,真名“腻脚酒”,温浏临近的另一个乡的特产,那时入口只觉得烈。
那天队长特别打了招呼,说肉可以多吃,酒不准多喝。可是,吃饱肚子走出乡政府大门,我们所有人刹那间便又醉了。那天,接我们的大巴只能停在两公里外,原因是街道两边挤满送行的百姓,他们是自发来的。那么多的人,比街天还多,有的拍手,有的唱壮语歌,有的不停怂恿孩子挥小手、喊叔伯,场景有点像影视作品里,苏区人民送红军。
你猜,就那个日子,就那一步一步被温浏百姓宠爱的两公里路,若让我展开,我能不能鼓捣出一万字?
此处不啰嗦啦。那天坐上大巴,个个泪眼,连年过半百的队长都泣不成声。我将背包放在腿上,想摸镜帕擦眼镜,却摸出了不知何时偷藏进去的“随身听”和一张纸条,见容我同住一百多天的兄长在纸上说:“铺盖留念,随身听不夺。兄弟顺风。”
他改了口。
【作者简介】朱兴友,高级编辑,出版有《斧声与寂静》《朱兴友的“近视眼”》《那时赵钱孙》《大时代微墨》《咬定青山》等多部个人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