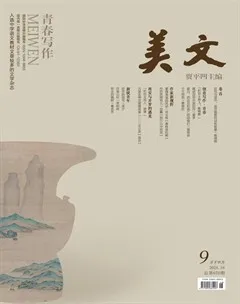时节的羽毛
很冷的夜晚,我在暖气房读一些零碎文字,脖子因为落枕而不时疼痛,在一不小心抬头的时候,疼痛不那么严重,却充满潜在的不确定性,以至于我不时调整着姿态来保证舒适。
已经十二月了,是冬天最安静的时候,所有事物都慢下了自身脚步,冬天也许是从这里开始,然后散向时间各处。今天傍晚开始落雪,薄薄的,有着轻盈质感的雪花片慢悠悠飘下来。这是这个冬天的第二场雪,还带着几分对大地的好奇与慢条斯理。下午站在院子里看雪,天空中洋洋洒洒的白,美得很纯粹,院子里的花凋谢了,月季细长的枝干显得更加孤单,仅有的几片叶子顶着薄薄的雪,甚是好看。我走过去,站在月季和冬青旁,想象自己也是它们其中的一棵,被某片雪花选中,在风里摇曳着白色的薄纱。
在冬日,雪花的耀眼无可替代,每一片都轻盈得异常珍贵。我喜欢兔爪留在雪地上的图案,带着弧度的小小的印记,恰到好处地呈现出优雅、柔和的姿态,那印记小巧玲珑,精致得可爱。我时常猜测,这大抵是一位出色的雕刻大师,一点点凿出来的,手法娴熟而巧妙,仿佛在裁剪最轻盈的丝绸。我也曾在老家的院子里养过兔子,父亲在靠院墙的地方,用砖块垒起一个小窝,再用木头做了小栅栏门,看起来小巧方便,我和弟弟给里面铺上麦草和一块母亲用旧棉絮做的垫子,一整个冬日,兔子就与这些暖融融之物相处得特别默契,在落雪后天气放晴之日,我们打开闸门,看两只兔子在雪地上跑来跑去,轻快灵动地越过了彼此间的警戒。我们喜欢跟在它们身后细数脚印,或者用树枝在脚印四周画上更大的轮廓。对于孩子来说,有兔子的童年是完整的,欢快的时光在这些温暖的画面里透着缕缕温馨。
另一个雪夜,我在书里读到“雪的沉寂”,在那辆开往伊斯坦布尔的车里,诗人说“一生中终有那么一次,雪会飘落在我们的梦中”。想起儿时看雪的情景,鹅毛般的雪下了一夜,第二天推开门,到处是白茫茫一片,由远及近,由高到低,一片纯白纯白的模样,干净得让人心醉,也让人不忍心踩上去,以至于时常忘了寒冷。我们戴着围巾和手套在场院上玩,打雪仗或者滑雪,大人们站在屋檐下一边喊着冷,一边被我们玩耍的身影所吸引。是的,谁不喜欢雪呢,“瑞雪兆丰年”嘛,更何况它如此这般安静地美着,干净地明亮着,仿佛从不曾有别的事物掺杂进来。那些便是我生命深处的雪,从童年至今,被头顶的风微微聚拢,又微微吹散,起起伏伏的过程像极了一个人的思绪,在某个点上被记忆牵绊和惦念,任思绪无边际地在脑海中蔓延,构思,带着夜晚空阔的安宁。
雪落在这个夜晚的窗外,真实又虚晃,像孤独,像思绪深处明亮的黑,反复递给你,又反复收回,不带一点点别的企图。这个夜晚,我在暖气房内感受不到屋外的冷和寂寥,20度的温度和郁郁开着的各色花朵,让屋内像是一片小小的春天。长寿花从入冬开始就举着自己玫红色的火焰,紫色的蝴蝶兰充满幽雅的贵气,而珊瑚蕨安静的模样和绿萝、吊兰相得益彰。茶花也在开,层层叠叠的端庄感让人爱不释手,我喜欢用手指轻触茶花花瓣,温润的质地像涂着薄薄的釉,以至于它每掉一朵,我就赶紧捡起来夹在书里,想让这份美更久地存在着。窗外小阳台上,是一截细长的褐色枯枝,紧紧缠绕在防盗网上。那是前年初春,路过小区围栏时,对许多缠绕在围栏上的枯枝产生了好奇心,它们还没有发芽,露出地面的部分有一小截红褐色的细芽,稚嫩的模样让人满满地好奇,我折了一小截带回家,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当我把它插在窗台花盆里的时候,我对它产生了莫名的期待,接下来的日子,给它按时浇水,施肥,看着它由一截细细的芽长成一根小枝,再长成细长的藤蔓,长出芽孢和叶片,这过程像极了探索,像极了从婴儿成长为大姑娘的过程。现在,它已经绕着防盗网缠了好几圈,巴掌大的叶片在春天和夏季鲜活地绿着,秋天开始,就会慢慢变红,一颗颗小铃铛般地挂在窗外,我喜欢这成长,成熟和衰落的过程,仿佛生命在我眼前延续出另一番风景。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只种一棵爬山虎的人,能有多大心思?”极简而缓慢的生活是我所钟爱的,时间在它的秩序中无边际地辽阔着,我始终站在小小的一角,养花,看书,再将心爱的文字搬到纸上,这种安静,带给生活许多片刻欢愉,人到中年,我对自己和世界已没有过多索求。
我曾在另一个雪夜,读到诗人莫温的《十二月之夜》,相同的时间点上,读喜欢的文字,内心深处有一种晴明的欢喜,仿佛来自天空深处的雪,安然而恒久地落在我周围,在我仰望的时候,漫天星空和雪片一起闯入视野,带来深深震撼与感动。他写道:沉重的翅膀爬进有羽毛的月光里/我来看这些/白色的植物苍老于夜/那最老的/最先走向灭绝。古老的夜,因为月光的羽毛而流露出浓浓的诗意,月光洒落自身的羽毛,像季节散落的种子,在同样古老的土地上自顾自生长,流淌,没有穷尽。想起上中学时,我每天和堂哥赶几里路去另一个镇子上学,路上要经过一大片原野,在冬日,原野没有庄稼也没有果蔬,近似透明的安静映衬在视野每一处,在我们上学和放学之际,时间因为过早或过晚,流淌出静止的安宁,月亮在天上孤独地白着,原野在脚下辽阔地白着,我们站在其中,仿佛天地辽阔,而我们从来不曾存在。虚无的空茫中,只有风偶尔吹过,带来丝丝寒凉和茅草丛沙沙的声响。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时间还没有给我们过多展示它折扇般的卷轴,我们沿着小路自顾自地走着,有时也会走在田地和小土坡上,厚厚的雪地里,没有路的过多概念,我们走在哪里,那里就是我们的必经之路,直到下一场雪覆盖了脚印,太阳融化了积雪。
冬日的林间是最为幽静的,像一片明晃晃的镜子倒映着天空的影子,偶尔有雪落下来,伴随着短暂而轻快的声音,舒心中充满了无限惬意,充满平和之感。我喜欢踩在雪上的感觉,脚底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不嘈杂喧嚣,也不会太寂寥,让人觉得不是在走路,而是在弹奏一曲轻柔的旋律。这时刻走得太快是极浪费的,慢悠悠走在雪上,听脚底下高高低低参差错落的声音何尝不是一种享受。
冬天走过河边,河水睡着了,或薄或厚的冰层上泛着丝丝寒光,像一条玉带完美地镶嵌在堤岸间,好奇心驱使你试探性伸出脚,或者只是用手轻轻触碰过冰层,寒意使你后退,又带着几分紧张和小确幸。小时候觉得冬日的小河有一整年的故事,要等春暖花开之际,讲给我们这些路过的人听。
这是适合冬眠的季节,动物睡着了,植物也睡着了。这时候一定要看看芦苇顶端的雪,薄薄的一层,晶莹剔透,像谁刻意涂抹上去的。我时常觉得冬日的芦苇才是最美的,虽然失去了春日的勃勃生机,但依然倔强地站在风口上仰视着河面,任雪花在身上,在周围,一点点地洒落,灰蒙蒙的天空在雪落之时有着让人沉迷的白,浩渺而深邃,仿佛天地间一场独特的约定,芦苇保持着原有的姿态,肆意地接住雪片像戴着轻悠的头纱。
记得上小学时,我们会经过一条细长的小河,我们喜欢冬天在河边捞几块薄冰,用芦苇秆在中间吹一个圆形的洞,再用茅草叶子穿起来拎在手里,冰块在雪后的阳光下闪着淡蓝色的光亮,仿佛我们拎着一块干净的玻璃,尽管小手冻得红彤彤的,但我们依然开心地笑着,在小路上拎着自己的冰块跑,那时候我们不关心时节变迁,一小块薄冰就让我们开心无比,那时童年的纯净和无忧虑,让我至今怀念,长大后再也没有找到几块属于自己的冰块和孩童时的心境。
冬天的缓慢,让人心里踏实。雪慢悠悠地落着,在树梢和屋顶勾勒出清晰的白色轮廓,层层叠叠的美,在某一瞬抖落下来,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悠长的音符在黑白键盘上滚动。屋顶上的炊烟袅袅地升起,为下落的雪撑起了青色薄纱,偶尔有人从小巷经过,有几声狗吠,宁静的小巷显得更为沉寂。我的母亲喜欢在落雪的午后做烩菜,豆腐、白菜、粉条在大铁锅里炖着,柴火在灶膛发出嘶嘶的声音,一切安宁有序,我们围着灶台等饭菜出锅,母亲做的烩菜极适合在冬日吃,喷香的热乎饭菜和屋外洋洋洒洒的雪相得益彰,我们吃我们的,雪下着雪的,看似毫无关联的两种事物,却有着点点滴滴的联系。
我曾在冬日夜晚,和一枚红月亮相遇,它高高地挂在远处的楼顶上,像一枚硬币,孤零零地看着我,我知道这还是我小时候见过的那枚月亮,而我已步入中年,它却一点没变,孤冷,高远,有着不食人间烟火的种种迹象。我在红月亮下走着,抱着刚买的蓝色梅花,是的,蓝色,绝美妖娆中又带着丝丝宁静,符合我对喜欢颜色的种种期许。我想象它们插在白瓷瓶里的样子,像极了我头顶此刻同样清冷的月色。我和红月亮的相遇,仿佛一场久别重逢的叙事,在冬日夜晚相互穿过自身隧道不期而遇,这一刻,我们都是没有故事的人,只带着自身的步伐和四周落下的薄雪。
我以为,大自然的手笔是从冬天开始着墨的,在山水和星空之间,澄明的白可以容纳一切万紫千红,从最细微之处落笔,再将璀璨和浩渺一一描绘,浓淡相宜,还时节以动人之处。我想过一个人最谦卑的样子,便是在雪夜,安静地看一轮明月,明晃晃的白衬托起碎银般的光亮,纯粹的干净让人感动,不必记挂远方的惦念,也不用想起眼前的琐碎,就那样简单地明亮着,仿佛月光找到了归宿,我也找到了归宿。
朋友说下雨天适合读《枕草子》,我觉得下雪天更适合。一个人清清静静地坐着,在火炉旁,猫儿卧猫儿的,我读我的,雪落着雪的,我们三个互不打扰,仿佛彼此孤立,又彼此依存。纤弱细腻的文字像一片片雪,慢慢落在我的脑海里,清寂又高远,纯净得不需要其他色彩,此刻我的思绪只属于雪,书里的,屋外的和心中的,它们相互交汇,融合,起起伏伏之间,让我想起春日碧绿的麦浪,在风中自由地舞着身姿,在无序和有序中构建起自身的舞台,此刻的雪也是这样,它们只在属于自己的舞台尽情展示,一起一落满是婆娑之姿。
这个冬日有几天阳光特别好,走过雪后的单位院子,异常的安静中,看见一只猫,眯着眼蹲在台阶上晒太阳,安静的姿态像一尊坦然的雕塑,我们笑着说,这是只有文艺气息的猫,这会在这暖阳下思考文学,也许是小说,也许是诗歌或者散文。我们没有靠近,但还是有意识地停住了脚步,猫只是微微地转了转头,继续眯着眼,这只花狸猫,黄黑相间的条纹,白白的肚皮,传统的乡间土猫,但因为在这个院子里,又让它看起来和别的猫略有不同,可能是精神上的不同吧,毕竟作协大院的树都是文艺气息的,更何况一只有灵性的活物。其实我更喜欢它春日躺在花荫里的姿态,深深浅浅的阳光照在它身上,小野花随意开着,路过的蝴蝶或蜜蜂在周围嘤嘤地歌唱着,仿佛一幅形态可掬的春日动态图。它偶尔会翻下身子,伸长的姿态露出毛茸茸的平静,让你觉得梦境也带着淡淡的花香。
在冬日,麻雀是颇为活跃的,这些冬日的精灵在灰色树枝间,忽上忽下地飞着,灵活而轻快,看不出忧虑与悲喜,我曾深深地羡慕过一只鸟的身影,像月夜中的一枚星子,动荡,旋转却异常活跃,在高远的天空下,有属于自己的小小枝丫。我的母亲在秋日采摘果实时,会将高处的果实留在树梢上,不论是柿子还是苹果,她说留给鸟儿吧,它们也需要这一口食粮。
前几日阳光很好的午后,我时常坐在紫红色的菊花旁边,大橘猫卧在另一边。菊花在暖气房肆意开着,任性而夺目,让冬日有了几丝俏皮感,橘猫圆滚滚地躺在我身边,发出呼呼的声响,母亲说这是猫儿在念经,我说这也许是猫在说梦话,我们都笑了,愈发对一只猫的梦境充满好奇。毛茸茸的东西让人在平静中多了一些惊奇,而此刻这份平静来自酣睡的猫和绽放的花儿,我喝茶,看书,从一本书的字里行间想象作者独特的视角和思绪,有那么一瞬,我在猫的鼾声里出神,起起伏伏的声响,仿佛一个人无忧虑地躺在棉花堆里,四周满是柔软的平静。
此刻是深夜,我喜欢的书里也正在下雪,伊斯坦布尔的雪以一种雪的沉积方式落在作者的脑海里,而昏暗如同一层薄纱压迫着周围的一切。我努力回想雪的沉寂,而窗外宁静般的昏暗在夜晚失去了原本面目。橘色的路灯下,星星点点的白沉郁地落着,有一种似懂非懂的朦胧与缥缈笼罩着周围,偶尔的人声和汽笛声是这份朦胧带着变幻与不确定,想起作者说过的,“一生中终有那么一次,雪会飘落在我们的梦中”。此刻,这夜晚的雪是我真实世界的雪,而儿时的冬天,那些雪才真正落在我的梦里,十几年如一日,摇摇曳曳地落着,像我梦中的童话世界,满是可爱,简单的模样。不经意间,雪便成了冬日的另一种寄托。我甚至觉得雪是人间的另一种思想,一粒水滴变换成雪的模样像极了人漫长而短暂的一生,液化和汽化的过程凝聚了一生的气力,只为这珍馐般的白轻轻落下,我曾在诗里写道:落雪后,可以踩着雪,缓缓走/可以在心里,低低地喊一个人的名字/想到他就想到/这薄薄的冬天/鹅黄色的温暖。此刻想到喊一个遥远处,模糊记忆中的名字,也是件有趣的事情,不必等着应答,也不必时刻惦记,就这样慢条斯理中夹着几分随性就好,他可以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可以是雪,是花朵,或者晴朗之夜的一轮明月。
放晴之后,闪烁的白从山头、树梢和山野之间茫茫然地铺展出去,靠墙角晒暖的老人,拴在木桩的牛羊和挤在墙角挤暖暖的孩童,都洋洋洒洒着饱满的精神头,他们谈论雪和来年的庄稼,谈论村口的路人和早饭的咸淡,仿佛雪后,一切慢下来的事物,都有显而易见的边沿,可以随时被他们归纳到某个话题中央。牛羊在扫过雪的木桩旁悠闲地晒着太阳,偶尔长叫几声,唤来跑远的幼崽们,这也是来年丰收的另一部分,被雪后的阳光轻轻抚慰。
《雪国》中写道的:“晨曦泼洒在曝晒于厚雪上的白麻绉纱上,不知是雪还是绉纱,染上了绮丽的红色。”我极力想象被晨曦渲染后的绮丽的颜色,想象自己也曾在雪后的清晨站立,周围满是星星点点的光亮,从山峦直到屋檐之下,而屋檐上,母亲做饭的炊烟轻轻升起,麻雀忙着翻飞,小伙伴们扬起手里的雪团,红围巾在脖子上露出暖融融的明艳,那种入眼入心的美,让人心情舒畅,那时刻天空深蓝,日子新鲜,仿佛尘间没有遗憾。
雪夜已经很深了,雪落的声音已有了明显的快节奏,沙沙的声音像细沙落下,又有几缕柔和之气,颇有柔中带刚的侠者风范。
伊斯坦布尔的雪还在落下,川端康成的雪国,列车在长长的铁轨上驶向远方,像一部没有来得及结尾的爱情剧,从朦胧之际走向朦胧之境。我的思绪在这两种画面之间穿插,我是他们中的一分子,被情节带动着穿梭在每一片雪片之下,而我,又不是他们中的一分子,站在局外的人,有长久的观望和叹息,但生活又不止这些,夜晚也远不止这些,我们从一场雪景里逃离,又在另一场雪景里重逢,这逃离和重逢的过程像极了我们所谓的宿命,如果真的有宿命。
我忍不住伸手抓起窗台的雪,这场景和我童年抓起窗台的雪在一瞬间相互重叠,我恍惚母亲还在我身后,在灯下做鞋子,父亲端着水杯,将泡着橘子皮的水放在木桌上。
记忆深处的雪永远温暖而宁静,仿佛不曾接受过岁月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