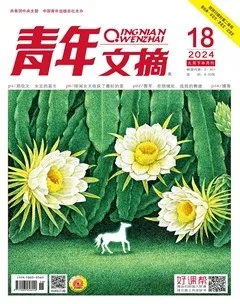海天之间

多年来,我痴迷于一个空间:海天之间。
去海边游逛,坐轮船涉海,乘飞机越洋,我都注意观察,浮想联翩。
海天一色。什么色?蓝。其实,海天并非一色。蓝,只是笼统的判定,它其实分为天空蓝与海洋蓝。天空蓝,一碧如洗时才为正宗;海洋蓝则复杂多变,深蓝、浅蓝,有多个层次,过渡时让人难以觉察。只有在适度的光照之下,才有标准的海洋蓝。
用色彩学解释,天空蓝是高调蓝调子,传递平静、纯净、安详;海洋蓝是低调蓝调子,传递沉静、深邃、幽远。两种蓝,各有千秋,我都喜欢。
海与天的分界是海平线。世界上的几何线条有无数种,那是最长最直的。但你无法靠近,即使乘船去寻,它也永远距你四点四公里左右。看着它,你耳边可能会响起塞壬的歌声,被吸引,被诱惑,一心趋前,不计风险。
海平线是一根漂在海上的纤细魔杖,会显示种种奇迹。日月、云雾、船只、飞鸟,均从那条线上诞生,生生不息,无休无止。
关注海天之间,可以开阔心胸。“乾坤浮一气,今古浸双丸”,充沛在海天之间的浩然之气,恒久不变的日月升落,能让你明白何为天行健,你是否要自强不息。
关注海天之间,可以调节心情。向后看,人事如麻,烦恼如烟。往前看,天宽海阔,一片澄明。
有一种看不见的力,在海天之间拉扯,于是有了潮汐现象。
潮汐可见,惊心动魄。一些礁石,看着看着就没了,等着等着又有了。沙滩上,潮舌伸伸缩缩,似在表达对陆地的情意;潮间带干了湿了,无数小生灵在此觅食、求爱,繁衍生息。
我曾在夜晚来大潮时,立于海崖边看惊涛拍岸。轰然激溅,震耳欲聋。浪花飞起时反映着月光,像满天珍珠,晶莹剔透。我对着月亮双手合十,默默感佩它的神奇之力。
海天之间,还有一种力,我们称之为风,这也由太阳传递的热量引起。
风在陆地,有许多羁绊,到了海上便畅行无阻。我们看不见它的真身,它就推动云朵给我们看,推动船帆给我们看,推动海水给我们看。
对海水的推动,最能显示风的手段。滚滚波涛,巍巍浪山,都由它造就。它甚至能制造渔民所说的“鬼潮”:潮水该来不来,让船只无法出海。
那是来了特别猛烈的强风,让大片海水整体移动,拉开了与陆地的距离。
风险,风险,因风而险。这个词,也因海而生。“天下之险莫如海”,信然。
台风,是海天之间的巨无霸。每当一个台风生成,我都从天气预报上看它的位置,从卫星云图上看它的形状。它独眼向天,极其狰狞;它旋转着移动,强悍无比。
我曾多次观察台风将至时的天象,只见远处海云如山,气势汹汹,近处有碎云飞跑,似野马奔腾。海鸟们懂得风险,纷纷从洋面上飞回来躲避,叫声中带着惊慌。
台风呼啸而至,所向披靡。天知道它怎么能有那么大的风力,在海上有十几级,到了陆地上有所减弱,却还能摧枯拉朽。天知道它怎么会带来那么多的水,从太平洋深处一路泼洒,泼了几千公里之后还是大雨如注。
鸟儿,是海天之间的精灵。如果没有鸟,这个空间便会死气沉沉。
我经常在海边看鸟。那儿有留鸟,有候鸟,种类繁多。最常见的海鸥,红嘴、白身、黑翅尖,在碧海蓝天的背景上引人瞩目。
那年夏天去汕头,北回归线上的太阳当空直射,潺热难耐。忽见海岛模糊,灯塔摇晃。细察之,原来是海中蒸汽升腾,袅袅而上,将我的视线扭曲。
有多少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升华,到了天上成为云朵,积为云山,铺作云层。
云,忘不了它的出处,在天上飘悠一段时间便回归大海,回归方式或温柔或粗暴。我见过海上的和风细雨,雨星儿微小,似有似无;见过风狂雨暴,雨区像巨大帷幕一样急促移动;我见过海上大雪纷飞,无声无息飘入浪波;见过冰雹大如乒乓球,落到海上砸起高高的水花。
云飞出海洋,雨雪冰雹便落于大地。即便如此,水滴还是汇成细流,汇成江河,奔赴汪洋大海。之后,一些水还要飞走,要升华。
海天之间的大循环,暗藏玄机,鬼斧神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