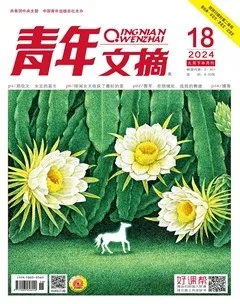明亮而温暖的卡夫卡时刻

编者注:弗兰茨·卡夫卡1883年出生于捷克,18岁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律,1904年开始写作,同时在保险机构担任文员。其作品数量不多却举世闻名,如小说《变形记》《城堡》和《审判》,其中运用了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开一代先河,被誉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宗师。
从前我常常感叹,弗兰茨·卡夫卡一辈子困在保险局的文件堆里,没有婚姻和子嗣,寿命又短,一脸苦相,真是个“苦命人”!当我读到自媒体称呼卡夫卡为“互联网嘴替”或“格子间幽灵”,也跟着会心一笑。但事实上,弗兰茨·卡夫卡是一个丰富多面的生命,他的喜剧天赋是不容小觑的。
假如我们有意寻觅,并且足够耐心,会撞见一个个诗意的,陡然明亮的“卡夫卡时刻”。第一个指出卡夫卡身上那些不为人知的幽默感和明亮色彩的人,是他的挚友马克斯·布罗德。布罗德在《卡夫卡传》中写道:“我认为他的关键词是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留恋尘世,以及一种恰当的充实生活意义上的虔诚,而不是自暴自弃、厌倦生活、灰心丧气等‘悲剧性姿态’。”
他曾回忆,“有一次卡夫卡来我家玩,正好我父亲在客厅沙发上打瞌睡,在半睡半醒中身体动了一下,卡夫卡以为把我父亲吵醒了,连忙举起双手,对我父亲说:‘您就把我当作一个梦吧’,然后蹑手蹑脚溜进了我的房间。卡夫卡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创作和生活混在了一起,两者没有明确的界限。可以说:他创作地生活,生动地创作。”
卡夫卡和布罗德初识的夜晚,布罗德在文学俱乐部做完一场关于叔本华的报告,卡夫卡带着严肃而羞涩的神情穿过人群,走至矮他一头、又比他年轻一岁的布罗德面前,问道:“我可以陪您走回家吗?”布罗德欣然应允。10月底的布拉格夜色微寒,两个不到20岁的青年边走边聊,一会儿忘我激辩,一会儿又欣悦于共鸣,一直走到午夜才依依不舍地道别。
即使到了一百年后的今天,谁不想拥有卡夫卡这样的同事或朋友呢?卡夫卡在单位里从不嚼舌头、扯八卦,从不参与派系斗争。他永远彬彬有礼,优雅整洁;他追逐时尚、关注新技术新发明,崇尚自然生活和自然疗法,热衷户外运动和旅行。卡夫卡虽然很少主动约人,但从来不败坏大伙的兴致,总是有求必应。
但每个和卡夫卡有所交往的人都会注意到,在他不善交际、疏淡羞涩的表象下,藏着巨大而神秘的能量。可以说,卡夫卡的“社恐”只针对不熟悉的人,在最好的朋友圈里,卡夫卡常常充当“显眼包”,将表现欲和表演天赋体现在主持和朗诵上。
1912年,卡夫卡为他的穷朋友、演员勒维四处张罗:安排演出场地,招募观众,印制入场券,甚至自告奋勇担纲开场白演讲,为朋友的登台做了出色的铺垫。
假如换一种角度,我们会发现,卡夫卡的文字处处具有幽默滑稽剧的效果。比如,当他某天开始写一篇新的小说,内心已经雀跃,却还不够自信去谈论它,他就会说:“昨天我开始写一个小故事,它还那么短小,几乎连脑袋都还没伸出来。”他对自己的身体极其敏感,他会说:“我的耳廓自我感觉清新,粗糙,凉爽,多汁,犹如一片叶子。”他的自嘲总是极度夸张,让读者忍俊不禁:“看上去我像是彻底完蛋了——去年我清醒的时间每天不超过五分钟。”他天真热烈的心会因为自己坚持写日记而幸福地冒泡:“我真想解释心中这种幸福感,它偶尔出现一次,现在就正充满我的心中。这确实是冒着气泡的东西,带着轻微的、舒适的颤动充满我的内心,它告诉我,我是有能力的。”
至于那个著名的句子:“一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卡夫卡也许参透了“笼子”的意义。所以,他有多讨厌枯坐办公室的时光,就有多发狠工作。他把分内事做得尽善尽美,年度报告写得漂亮挺括;他深入工厂实地勘察调研,搜集大量资料,撰写安全生产指南,为事故报告配插图;他发明了一款便捷安全帽,大大降低了工人的工伤死亡率;“一战”期间,保险局的一半同事都应召入伍,导致人手紧缺,卡夫卡经常需要加班。在这样的工作强度下,卡夫卡仍然见缝插针地写作,只有极度自律和坚韧的人才能胜任如此强度的工作。
固然,卡夫卡在信件和日记中不止一次地写下“绝望”和“崩溃”这样的字眼,但是他总能“绝处逢生”,从未真正躺平。在与自我的长期较量中,卡夫卡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生存策略——精神分身术和自我解嘲术!看似柔弱的人孕育出惊人的坚忍品质。
当然,卡夫卡并非天性快乐之人,那些明亮诗意的时刻只是生命的间奏。但凡具有强烈使命感的人都是幸福并痛苦着的,卡夫卡30岁不到就已写下豪迈的誓言:“我对文学不感兴趣,因为我就是文学本身。”写作的使命感让这个布拉格公务员的生命充满西西弗斯和普罗米修斯式的悲情诗意,那短暂的岁月不再是随风飘荡的枯枝碎叶,而是一个明暗交错、主题鲜明、富有活力的有机整体。
对于弗兰茨·卡夫卡而言,写作不是业余操持的游戏,不是为了赚取稿费,甚至不是获得社会声望的途径,而是一团照亮生命的火焰,抵抗周围世界的寒冷:“我看到了我们世界的寒冷空间,我必须用火焰去温暖它,而我先要去寻找火焰。”卡夫卡用他的整个生命点燃了一团清冷火焰,它执拗地燃烧了一个世纪,还将继续燃烧下去。
(大浪淘沙摘自2024年6月3日《文汇报》,本刊有删节,黄鸡蛋壳图)